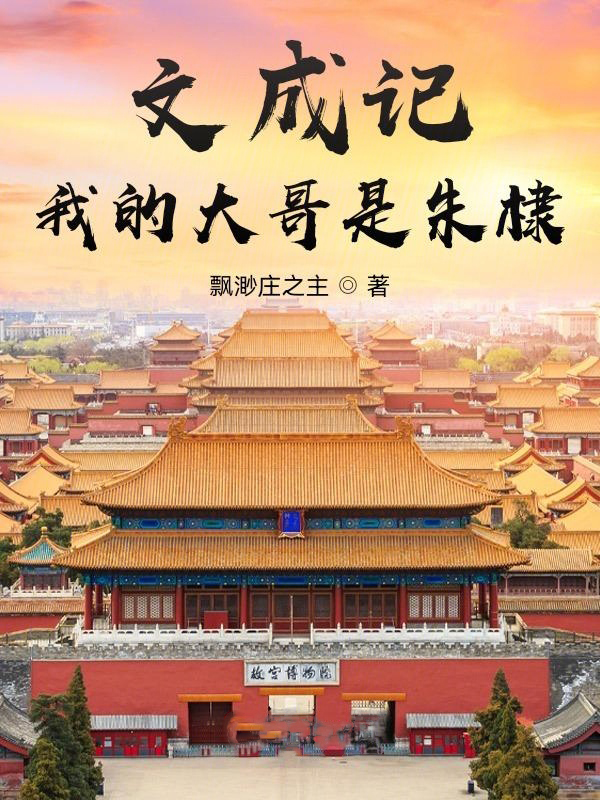天边已露出一丝灰白,楼天宇带着疲惫走上二楼。
卧室苍白透明的窗帘透出远远零星的灯光。刘珍妮缩在床边,像一个天使一般睡得沉静,微卷的长发披落在床头,睫毛轻轻地抖动着。
楼天宇不忍叫醒她——她爱他,爱的如此单纯直接,十年了,他怎会不为所动。他的心底无数次地想象着:这就是他的爱人了吧?美丽大方、温柔似水、家世显赫、才干非凡。这难道不是一个男人能想象到的另一半最好的样子了么?
可是他的心里,为什么总有一份对归宿不能甘愿的保留?
楼天宇站在窗前,廖一凡低沉稳健的声音,像挥之不去一般,在他的耳边萦绕:
“你是说……你想投资KC Capital?”
“不,我想投资的是……你”,廖一凡深黑的双眸盯着楼天宇,“组建一支人民币基金,你,和我,还有我们的团队”。
“你是想带着资金加入?”
“是。计划里面,对我曾经投资的项目和回报率有充分的介绍”。
“我对你的能力没有任何怀疑。但你为什么要投资我呢?”
“你有完美的履历和强大的美金渠道,加上KC Capital的业界声誉,是一个完美的境外平台。我的第一期人民币大约20亿,虽然不多,但联合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可以做的事却有很多。”
楼天宇沉默了几秒,这个廖一凡说的一点都没错。短短数语,他就感觉到面前这个人:专业、激进,野心和头脑一样都不缺。他一直和最优秀的投资团队共事,很清楚:这一个行业,血液里不自带着贪婪因子的人根本做不出成就。可是,廖一凡看上去,似乎又并不像一个贪婪的人。
“廖先生,我好奇地问一下,是什么驱动着你做投资行业?”
“楼先生,你觉得二十一世纪什么最重要?”
“你是想说……人才?”
“不,我是想说:资本。”廖一凡顿了一下说道,“这个世界上,毒品和资本是最直接可以驾驭人的东西。如你所说,浅尝辄止。我想驾驭我的人生,而不是被任何其他人所驾驭。”
“毒品和资本……”从廖一凡这样的城市金领嘴里说出这样的话,让楼天宇有些意外。
不知道为什么,廖一凡这个人,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莫名熟悉的感觉。他想起第一眼见到他时,对面那双眼睛中无法掩饰的错愕。
但,怎么可能呢?茫茫世间。他虽是华裔,却是第一次来申城。楼天宇嘴角露出一丝无奈的浅笑。
要想捕获好的项目,最完美的方案的确是通过廖一凡建议搭建的那个联动平台。他们的战场,衡泰系的战场,就将迎来血雨腥风。
血雨腥风……他的脑中涌现出这个词。
突然,毫无预料的,右半边大脑涌上一阵涟漪,一波连一波的痛楚袭来。一张又一张断续的影像画面不可控制地占据了他的大脑,一个女人的哭喊和嘶叫、扫射的机枪、林地、带着面具的几排荷枪实弹的……军人。眼前林立的大楼仿似海市蜃楼般地崩塌,他抓不住坠落的那份无望,也无法思考这些不知何来的片断画面。他打开床头抽屉拿出一瓶止痛药,抓过桌上的一杯水,飞快地吞下。
熟悉的窒息感,强迫他低下头,双手支撑在床沿。
深夜的动静惊醒了刘珍妮。
“天宇?“她惊叫一声,”你怎么了?刚回来吗?“她一个翻身挪到他的身边。
楼天宇像是还未从混沌和痛楚中彻底清醒过来,扶着头直直地望着她。
那双深陷的眼睛,带着疲倦透出摄人心魄的魅力。一片潮红和温热荡漾在她的周身。
“Jenny,“他看着她,她如此美好。
一整天的疲累,抵不过迈进房间看到她静静躺在身边的感觉——他突然感到一种安定踏实。像十年前他刚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那些时光。混沌的人生抵不过面前一张灿烂开心的笑脸,心在游离与彷徨的漩涡中,抓住了这跟救命稻草。
可是那崩塌一般的画面,在最近的几年里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让他怀疑迷茫。但他无论怎样努力,都想不起究竟是哪里看到过——是幻想?是记忆?不会,这些镜头都毫无可能与他的生活轨迹有关。
像是要摆脱一天的困倦和疲乏,和那些混沌的乱象,他一个翻身迎向刘珍妮鲜艳的双唇,透出一声长长的喘息,世界仿佛陷入无边的黑暗。
慕尼黑的英国花园,温暖和煦的风吹在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身上。老人一身银灰色的运动装,身材匀称。他饶有兴趣地看着一座小桥下,德国人自制的冲浪设备——河流的水湍急而起伏,一个个自带着滑板的人轮流上去尝试。每当一个人失误掉落进河水里的时候,周围人会惋惜地发出“噢”的叫声。
一个健硕的男人,看上去有三十五六了的样子,浑身的肌肤呈现焦糖色,肌肉紧实,散发着坚毅而誓不罢休的劲头。他在冲浪板上滑了有将近5分钟的样子,各种姿势、翻滚旋转,引起周围人一片喝彩。老人慢慢微笑着走近些看。滑板上的人余光似乎扫到了他,一个刹车的动作过后,他顺势往河水中一趟,以示完结。有几个还未尽兴的,还在嚷着,像“继续”的意思。老人适时地往后退。两人从嘈杂的人群中退了出来,走向林间深处。
“陈总,好久不见了!”健硕的男人开口,一听就不是纯粹中国人的样子,有点东南亚口音。
“是啊,达邦,你这么些年,一切都好吧?”陈克盾笑眯眯地问。
作为海天金融的老总,陈克盾这么多年来,仍然不是很清楚达邦背后的基金OPG Investment的掌门人究竟是谁,据说这是一家KC Capital的下属基金,专为亚洲而设的,达邦是泰国人,已经是Head of Asia (亚洲区总裁),但仍然没见过KC Capital欧洲区的老大,一个据说叫Morris的人。
尽管一开始在项目上的相遇纯属偶然,合作也充满着不确定与怀疑,但几次大项目的交手过后,双方都感到了配合默契的和谐——海天金融攒项目,出名做背书,OPG给钱收劣后回报。一个越来越有名,一个越来越有钱,再加上两人各自的腰包都迅速地鼓了起来,慢慢的大家都形成了默契,只谈项目,不谈其他。
“这次,劳动陈总亲自出马……说吧,又看上了什么好东西?”达邦一手提着滑板,顺手用毛巾全身上下地擦拭着自己。
“不是项目,是家公司。”陈克盾轻松地说道。
“陈总还有拿不下来的公司么?”
“衡泰控股……”
达邦惊异地看了他一眼,道:“衡泰,这不是你们自家的公司么?”
“哪来的自家哦,你知道的,我只是一个小创始人而已。衡泰系的苏棉衡,在海外最信任的还是Susan,我追了她那么多年,最终还是收不到啊。”陈克盾悠悠地表示着沮丧。
“哈哈,那你是追不到他的女人,恼羞成怒要抢他的公司吗?”达邦哈哈地笑了起来。
陈克盾没有笑,也没有说话,看上去便像认可了一般。
达邦饶有兴趣地看了他一眼,一把将滑板扛到了头上,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走,请你喝啤酒。”
陈克盾轻笑一声——没有拒绝,还表示可以坐下来畅饮,这便是可以详谈共谋的态度了。
公园里的啤酒屋,永远有仿佛不需要工作的欧洲人肆意地在里面闲坐。一杯啤酒,可以消磨一下午。而在陈克盾看来:这种生活纯粹是浪费时间。时间如此宝贵,不用来换取一些什么,哪怕是利益、哪怕是地位、哪怕是一些影响力,都是好的。好过无甚建树,过了一个完全没有收获除了一杯啤酒的下午。
“陈总,你别看不上这些欧洲人,呵呵,在他们的世界里,真的没有什么需要去追逐和征服。能够平平安安地喝喝啤酒就很好了!”达邦仿佛看出了陈克盾内心对他们的鄙夷。
“总觉得,你应该和他们不一样,对吧?否则你大老远地跑到欧洲来干什么?”陈克盾没看他,盯着一个胖子,看他狼吞虎咽地吃着一大盆的薯条,别说书或者电脑了,手边连张报纸都没有。
“你知道的,我是没办法。”达邦满不在乎地摇摇头说:“一个被凌氏家族扫地出门的女婿,你觉得我还能在东南亚有未来吗?”
陈克盾不是不知道,他口中的凌氏家族,就是当年称霸东南亚的大毒枭凌岳,鼎盛时期几乎垄断了金三角70%的毒品生意,规矩严到他的雇佣军都闻风丧胆,但最后还是没有逃过美国人的追捕,他最受器重的儿子去世后,他就再也没有缓过来,在缅甸军政府的软禁中郁郁而亡。他的长女凌清红,在泰国重起炉灶,现在拥有泰国最大的酒店连锁集团和最丰富的畜牧产业链。由于她一直怀疑当年是达邦和美国人勾结发起的突袭,两人最终分道扬镳,并放出话来:不许达邦粘手任何凌氏产业。达邦于是远赴欧洲,在德国和瑞士之间求得生存,慢慢地,竟然也算借着海外的平台在东南亚的金融领域里称霸一方。
此时,两人啤酒下肚,有了些酒精的刺激和兴奋。达邦举起啤酒杯示意,陈克盾适时地“cheers”稳稳地接住:“老规矩”,他说。
达邦会意地笑了笑。隔壁的德国胖子吃完了薯条,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拍拍大腿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