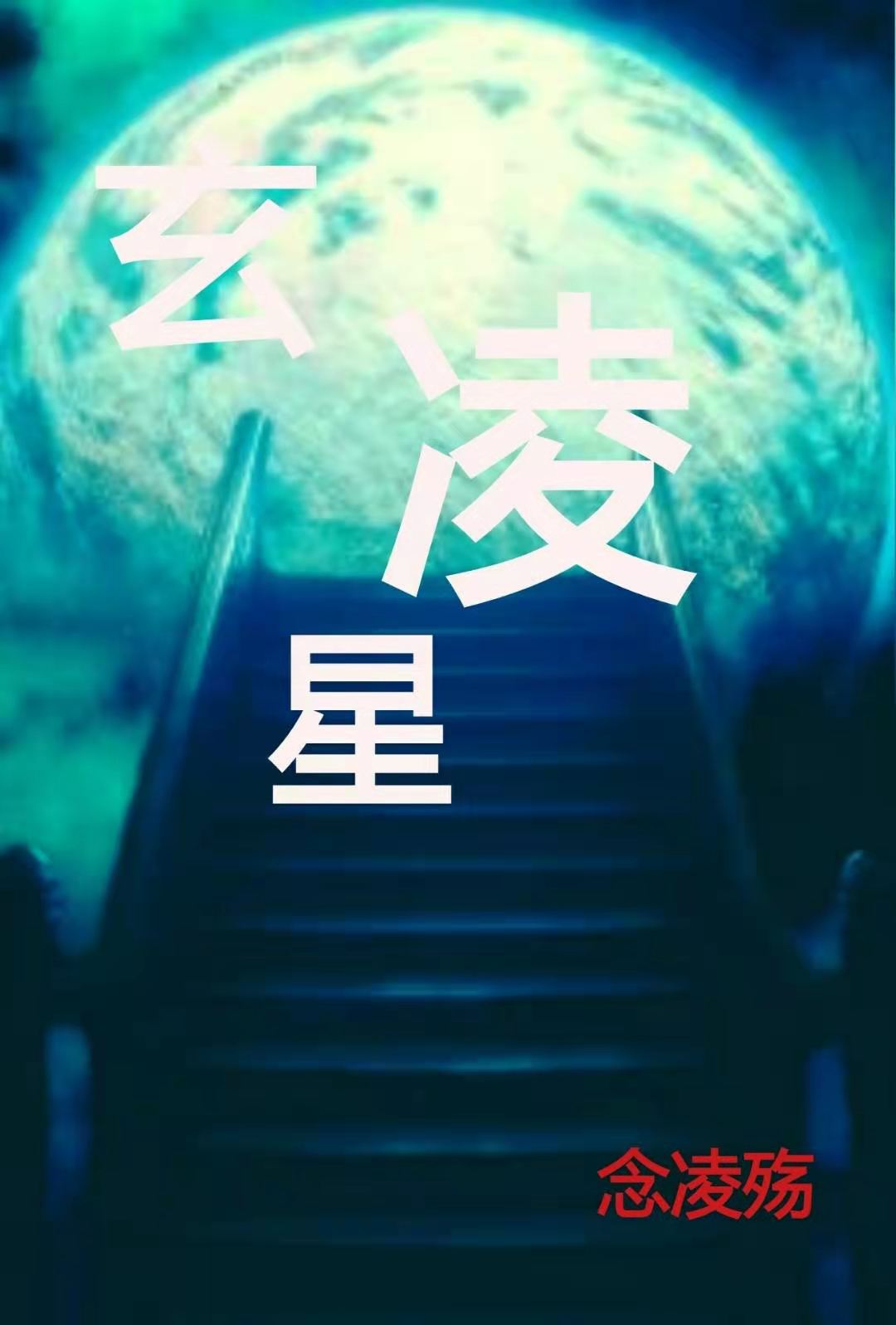两人匆匆出了剧社,上了车。
薛起发来视频请求。
摇晃的镜头内出现了花白的医院病房,最后对焦在薛起一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球上。
薛起已经熬了好几夜没有睡,睁眼闭眼都是视频中的画面,还有小时候,爷爷坐在老院的藤椅上给他讲故事,故事讲着讲着他就长大了,他现在满脑子都是爷爷看着他的脸,一双老眼浑浊的模样。
他还能记得爷爷睡梦中总呓语报应报应啊。
“爷爷。”他将镜头靠近薛春年,凑到薛春年的耳边说,“是尤小姐和徐先生。”
薛春年明显在听到后者的时候,身子颤抖了下,他骨节嶙峋的手去抓手机,每一寸的肌肤都是皮包骨,肤色黯淡发黑。
他紧紧的握住手机,手抖的厉害,看着视频那端男人英俊的脸,薛春年忽的笑了:“真像,像啊。”
他笑着笑着开始咳嗽了起来,胡言乱语的说:“角啊,我的角儿……”
薛春年话说的断断续续,视线痴痴地看着屏幕画面中徐放的脸,浑浊的眼中迸发出精光,像是濒死之人前的回光返照。
空气中蔓延着死一样的沉寂,薛春年扯着嗓子:“佳人绝代,天妒英才。”
他的眼睛一眨不眨,看的人不寒而栗:“徐放,你父亲是他杀不是……不是自杀,那晚,出事那晚……李任意曾……曾去见你父亲……”
薛春年似乎用尽了所有的力气,说完这段话开始用力的喘息,上气出下气不进,有去无回。
老人闭上了眼睛,一行眼泪顺着眼角无力的滑下。
画面一阵凌乱,随后归于花白占黑,徐放只能听见画面那端,薛起撕心裂肺的哭声和很多人手忙脚乱的声音。
徐放很久都维持着一个姿势一动也不动,薛春年的话不住的在耳边回响。
出事那晚,李任意曾见过他的父亲。
尤礼心里咯噔一下,她看向徐放,范宜淮跟她说过,徐放最敬重的便是他这个师傅,李任意了。
尤礼和徐放赶往了禺子岭镇。
高河商店还是那样,但是门头落了锁,尤礼在出租车上匆匆的瞥过一眼。
转过头来,身旁的男人侧脸被外面连街婆娑的树影划出深浅不一的阴影,光从他的眼中过,最后消失在急速飞驰的速度之中。
薛起等在门外,一身黑色的衣衫,头顶上披着白色的麻帽,一直长长的勾到后膝。
远处,尤礼和徐放急匆匆的从出租车上下来,吴亮早就到了。
“节哀。”
听闻徐放的话,薛起鼻子抽动两下,眼中莹莹泪光。
记得车中他说过,爷爷是他唯一的亲人了。
“请进吧。”薛起擦了把眼睛,青年仿佛一夜间彻底长大了。
薛家住的还是老式的院子,院内绿叶盈盈,却在那深绿中列着一具棺材,沉红的漆木,棺盖严丝合缝。
谁都知道,那里眠于一个藏了一辈子心事的老人,这心事成了心病,带入了棺中,即将长眠于土里。
黄土白骨,终年不见天日。
来薛家送薛春年最后一程的人很多,徐放走入人群,屈膝而跪,给老人磕了三个头。
尤礼站在他身后几米远处,目光飘落在那冰冷的长棺上。
徐放不远万里的来到禺子岭,来见这个老人,而这老人,知道很多秘密。
薛春年是徐放的恩人,是那宗疑点颇多却早早定棺盖论案子的揭发者。
第二日,薛春年出殡,埋于镇内一座矮山薛家的祖坟里。
一切结束后,薛起将徐放一行人留了下来。
薛起动手给三人沏了茶之后,便进了主卧。
片刻,他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盒子,他将盒子递给徐放:“这是爷爷让我交给你的。”
红色的长方盒,上面雕花画蝶,是那种老式的款,盒子开盖时发出轻微的咔声,而里面,放着台录像机。
还有一封亲笔书信,落款薛春年,印泥红色的指印就摁在名字上面。
书信的下面是薛起发给徐放邮件中,那页父亲在出事那天亲笔书写的日记。
这个老人把一切都想的周全。
薛起说:“这是沈叔02年送给我爷爷的,里面有你们想要的东西。”
沈叔,沈尔京。
薛起又颇有意味的说:“这里面的卡带是原件。”
徐放问:“薛老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薛起双手交握,似乎陷入了回忆:“爷爷以前是个很开朗的人,但是自从一年半前听说禺子岭要划出一个汉源景区来之后整个人就变得不太对劲儿,后来我才听他说,是因为一个荒废已久的戏台子。”
徐放:“清河灵庙。”
薛起语气顿了一下:“对,一开始我不懂他为什么这样,哪怕别人稍微提起来一句也会暴跳如雷,直到,一年前,爷爷的身体突然变差,整夜梦呓,甚至有时候会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薛起看着徐放:“他最常说的一句,就是他有些害怕,报应,这是报应什么的。”
薛起看了眼徐放已经放回原位的录像机:“这视频是我爷爷拍的,爷爷当年倾慕名伶风采,借着两家的情面求沈叔要他进去帮忙,沈叔知道爷爷好看戏,而且国海剧团的演出并非有钱就能请到的,这次机会无比的珍贵,所以给他一台录像机,可能是希望他能和偶像合个影,或者是记录现场,但是谁也没想到,最后这带子里记录的却是……”
除了尤礼之外,两人均看过带子播放的画面。
将两人送出门之前,薛起终于再度开口:“一年前,我父母曾自驾游去,半途遇车祸双双身亡,而那日,刚好是您父亲的忌日。”
儿子儿媳在那样一个日子双双去世,终于击溃了老人心中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筑起来的城墙,坍塌后袒露出里面肮脏恐怖的现实。
“邮件,是你发的。”徐放的视线落在薛起苍白的脸上,他的头发几天没打理,有些乱。
“快递也是你送的。”
薛起终于不再沉默,道:“是。”
但是他好奇:“你是怎么猜出来的?”
徐放:“薛老年事已高,那个年代的人对电子设备都不怎么在行,就算有例外,能写出隐藏ip地址代码的人也绝不可能是他。”
徐放走近薛起,抬手撩起他近乎遮住右边半只眼的头发,尤礼看过去,薛起的右眼皮上有块浅长的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