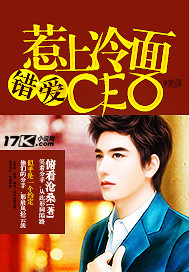“打听出来了,他们明天上午十点四十五的飞机。”
陈词说这话的时候,尤礼正在擦杯子,闻言,她将酒杯倒挂在架子上,玻璃与铁碰撞,发出叮的一声脆响。
她掀起眼皮:“消息准确?”
尤礼记得他们是开车来的,这会怎么又改坐飞机了?
“准着呢,我加了他们其中一人的微信,说来时的一辆大车不知道怎么就坏掉了,余下的那两辆是小车,载不了几个人,所有干脆将车都留在了北京,搁领头一个朋友那了,他们订了飞机票,说是忙着回去呢。”
陈词笑:“小老板,你打听这事做什么啊,难不成你还想再请他们一回?”
尤礼将布递给陈词,推开小门出来。她就算想请,也请不到了,她应该是将徐放得罪透了。
尤礼思量半瞬,道:“陈词,我明天要去上海,以后店你来看。”
飞机降落在虹桥机场,徐放取下背包向机舱口走,林逢昌跟在他的身后:“少爷,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反观犯了事的人,跟没事人一样。
他们去北京这一回,打的是给范宜淮母亲过生日的名头,徐放道:“叔你放心吧。”
国内到达口外停了辆银灰色别克,车牌沪A打头,66收尾,而李任意是66年生的。
林逢昌看到后,脑袋里冒出四个大字,放心个屁。
开车的人是梁吴,他一眼就看到了要接的人。
徐放生的高,五官又过硬,走到哪里也是让人回头瞧那么两眼的主,想不注意到都难。
梁吴下了车,走到徐放面前,道:“少爷,上车吧。”
见到梁吴,徐放就知道事情败露了。
“梁哥,我们这刚给我妈过完生日回来,飞机不早不午的,饭还没吃呢,不着急回去吧。”范宜淮慌了。
梁吴伸手推了下金丝框眼镜,道:“别编了,我查过了,这趟飞机由北京飞的,你老家安徽。”
梁吴又扫了一眼几人手里拖着的挺大的皮箱,冷笑了声:“林叔和少爷上我的车,至于你们……”
他扫视一眼:“自己解决。”
他回身去拉车门,想起了什么,语气很淡:“还有,半个小时之内必须到堂子,团长在等。”
团长在等,范宜淮听到后腿都软了。
要说林逢昌主管越剧团的剧目安排、活动以及账目清算,梁吴管的就是设备、现场以及演员们的日常生活。
说白了,林逢昌和梁吴都是团里的管家,只不过梁吴跟着团长,林叔跟着他们罢了。
国海越剧团在普陀区。
由机场出发,车程不过二十分钟,穿过繁华的街区,开进短巷,最后视线开阔,别克停在一个大院前。
大院有些年头了,青灰色的砖墙上爬了不少爬山虎,建筑风格挺像四合院的。
现任越剧团团长李任意的母亲也是越剧演员,而团长的位子是李任意从他师父手里接过来的。
一进院子,迎面窜过来一条黑背,哈着嘴巴扑到了徐放的身上,徐放顺手揉了两把它毛茸茸的脑袋和大耳朵。
梁吴沉默着躲开了些,这条黑背是徐放养的,是院里的霸王,除了徐放谁都不让摸,凶狠无比。
都说谁养狗,狗就像谁,梁吴抬起眼看了徐放一眼,就见他握住大狗的爪子,将它推开了些:“恶霸,乖。”
没错,恶霸就是这狗的名,起的那是相当有先见之明。
未走两步,徐放回头对林逢昌说道:“林叔,我去见师父,你先回去休息吧。”
林逢昌脸色犹豫,徐放笑了下:“叔,你放心吧。”
李任意就在前堂,徐放去的时候,气氛凝重。梁吴跟着徐放站在他身后一步远,徐放道:“师父。”
李任意手里握着拐杖,缓缓起身,绷着脸走过来:“跪下!”
男人声音中气十足,凌厉严肃。
徐放向后退了半步,双膝曲起,膝盖磕在地上发出闷响。李任意握着拐杖的手骨节泛白,低头看着徐放的脸,咬紧牙关,眼中不知是失望更多还是愤怒更多。
“我问你,你来国海几年了!”
“十五年。”
“那团里的规矩你可清楚。”
“倒背如流。”
李任意被气笑了:“倒背如流?那你倒是说说,不可以出私这条你记到哪里去了?”
李任意下颌骨紧绷:“人家都是躲着枪眼走,你偏偏往枪口上撞!知道尤国章是什么人吗?”
这徐放还真不知道,他平时除了唱戏就是唱戏,团里的业务问题他一概不管的。
李任意的声音就在头顶,听起来万分的气恼:“尤老板连续十年给咱们团捐款捐乐器,你知道这次你惹了什么大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