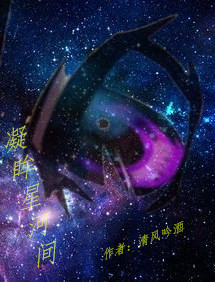四名亲兵答应一声,掳着袖子就要上前,一直满脸谦和的景监忽然脸色一沉,沉声说道:“且慢,廷尉大人鲁莽了吧?”
“什么?景大将军想抗诏吗?”张栋勃然大怒,手指景监喝道。心中却在冷笑:果然狗急了是要跳墙的。
景监面色如常,对着张栋一拱手:“廷尉大人言重了,景监如何敢抗诏?”
“既不敢抗诏,那为何不让我的亲兵扒下这几名贱奴的衣服?”
景监打开手中的诏书,沉着脸说道:“大王诏书上只说让廷尉大人来查实景监征用军奴,可没说这四人就是军奴。”
“什么?你说什么....我看你是想包庇这几个军奴!”景监变脸本就让张栋甚为不快,一听他强词夺理,更是让他气得七窍生烟,语无伦次地大声暴喝。
中军帐中,两位最高主官针尖对麦芒。景监一改先前谦恭神色,满脸都是傲气。手下的心腹军官心中大声叫好,早已看不惯那廷尉老气横秋的作派,管他妈的特史不特史,只要大将军一声令下,咱们立马上去尸解了他们。
“本大将军从来赏罚分明,既不包庇手下也不冤了手下。廷尉大人自己既说他四人是军奴,请问有何凭证?”景监两眼斜瞟着张栋,眼中尽是鄙夷之色。
“反了,反了,老子既说他们是军奴,当然有凭证。”被激得暴跳如雷的张栋口不择言,移目四顾,直盯着将参王平。王平此时鼻尖上冒出了汗珠,心中大骂张栋草包,两眼极力闪避着张栋。
“请廷尉大人请出凭证,景监若有庇护军奴之事,任凭处置。”景监脸如严霜,步步紧逼。
“王平?都这时候了还做缩头乌龟吗?”张栋一声大喝,其声如雷,两眼怒视着王平,象是要喷出火来。王平再也躲不住了,低着头躲避着景监的目光出列两手一拱:“标下可作证,这四人确为军奴。”
“看到了吧?听到了吧?”张栋立即变得神气活现,摇头晃脑地说道:“景监,这可是你营中的将参说的,算不算得凭证啊?”反正已经撕破了脸皮,再无顾忌,直呼景监大名。
景监不理会他,两眼盯着王平问道:“请问将参大人,如何得知他四人是军奴?”景监向来在军中威信极高,平时虽从来不摆大将军的谱,却是不怒自威,瞪起两眼时大营中无人不怕。王平是他手下,却呼其为大人,自是讥讽之意。王平此时被景监利剑一般的目光逼视得局促不安,手足无措,结结巴巴地答道:“标下..标下..曾看到..过他们..肩头上的奴隶..印记。”
“哈哈哈”一旁的张栋昂着身子一阵狂笑,“听到了吧,你们都听到了吧?”后面一句是问帐中众军官的。众人无不恨得牙关紧咬,两眼怒盯着王平。
景将军突然变得和颜悦色,叹了一口气说道:“王将参,自甘臣相荐你到我军中,景监一向待你不薄,你既知他们几个是军奴,为何不先告诉我呢?”
这可是诛心之问,王平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得不出声,四下都是怒视着他的目光,躲无可躲,只得两眼望地。
景将军的脸色今天好象是六月的天,说变就变,“不过那都是你一面之辞,诬陷大鑫在职军官可也是要杀头的。”话是对王平说的,两眼却瞟着张栋。
“不要再罗嗦了,如是诬陷,本廷尉自会治他之罪。景大将军,现在可以让亲兵扒下这几个人的衣服验证验证吧?”
“且慢,本大将军要王将参自己说,如是诬陷该当如何?”景监毫不让步,历声喝道,身后站着的心腹蠢蠢欲动。
“王平?”张栋又一次被气昏了头,发抖的手指指着王平。王平如骑在虎背,面如死灰,他心里知道,今天就是整倒了景监,他手下的心腹也决不会让他活着回到咸城。长叹一声,拱手说道:“标下愿以人头担保,这四人确实是军奴。”
王平话刚落音,大帐中忽然一道红光闪过,王平的脑袋连着头顶上的平帽一起滚落下来,颈腔中冲起的血箭在空中散开落下,散落血雨中正是景大将军手执滴血的铜剑,威风凛凛傲然而立。
“啊!你..你..你要起反吗?”被眼前突然出现的景象惊呆了吓软了的张栋,手指景监话不成声,他虽然和王平站得远,嘴角边却也溅了几点王平的鲜血,惊慌之下忍不住伸出舌头舔了一下,浓重的血腥味道,让他更加惊惶失措。
张栋的亲兵见势想要拨剑,却立即被军官们紧紧围住,动弹不得。只听得景监冷笑了一声,扬声说道:“景监世代望族,永远都是大鑫忠心之臣。南宫,脱下你们的上衣,让廷尉大人查验。”
四人得令,昂头脱去了上衣,坦然将右肩伸向张栋。刚刚心下稍安的张栋定睛一看不禁傻了,眼前四人的肩头上除了一个军奴的印记外,赫然还烙着一个火红太阳的标记。惊怒交加的张栋,陡然间只觉心口处遭了一记闷棍,嗓子口一甜,一口鲜血喷出,跌坐在地。
*************************************************************************************************************************************
花儿坡营中,孙旭东正在操场和王剪一同试射经他改制后的弩,一百五十步的距离,王剪一连试射了三次,支支都中了插在前面的木头小人,不由兴奋之极,大赞校尉大人的弩既省力,又准又好用。
孙旭东第一次看到弩就觉得太原始了,虽然已经具备了现代弩的雏形,射程也比弓箭要远,但它的准确性太低了。而准确性正是弩最大的长处啊。他拿了一副弩在自己营房里琢磨一个时辰,发现影响准确的主要是三个地方,一个是弩的扳机直接去推动钩牙,要用很大的劲才行,这肯定会大大影响射击的精确性。二是弩的望山是固定不动的,不管射程多远都在一个地方,完全没有考虑到箭镞的飞行是一个抛物线的过程。三是箭镞呈扁平的三角形,既不是很符合空气动力学的流线原理,影响射程,遇有风时也会影响精准。
虽然找到了问题的症结,问题并不好解决,主要是扳机,想法是加上一个联动机构,利用杠杆原理去推动钩牙,这样省力的同时可以保证弩身的稳定性,大大提高弩的精准性。可要实现时却让孙旭东费了不少脑细胞,想画张图吧还没纸,没铅笔,没直尺,没三角板,没圆规,真是让他费尽了心思才弄妥了。望山的问题倒是好解决,只要参照现代****的标尺原理就可搞定。将原先为一个整体的望山拆成两部分,底座锉成台阶状,随着距离的远近调整望山的高度就行了。第三个问题在花儿坡营却没有办法解决,因为这里的军中器匠最主要的任务是修补损坏的兵器,根本打制不出孙旭东要求的,三个棱面相同大小的三棱型箭镞。
两人来到距木头小人二百步的地方,孙旭东让王剪再试射一次,王剪用脚蹬开弩弦,放入弩箭后瞄准,轻扣扳机,孙旭东设计的联动杠杆机构极轻巧地就推开了钩牙,一阵疾风掠过,弩箭射出,两人张目细望确好象没有射中前面的木头小人。
趴在木头人那边的小山跳起身,飞也似地跑过来,喘着气禀报道弩箭射到了木头小人的脚下了。孙旭东微微一笑,接过王剪手中的弩,将望山调高了一格后蹬弦上箭,略作瞄准,嗖地一声射出,稍后就见那边的兵士们欢呼雀跃不止。王剪匪夷所思地看着这猛然间威力大增的弩说道:“校尉大人,这支弩能否赏给标下?”孙旭东哈哈大笑:“别急,待本校尉再稍作改动后,即送到齐田大营,请景将军命军中器匠以后就照着这样子做,鑫国大军的弩兵都能用得着。”
孙旭东回到营中,仔细琢磨着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动,只可惜弩臂的制作工艺太过复杂,和制作长弓一样需要的时间很长,不过眼下可以在原有的弩上进行改制,就可节省不少时间。
正在细细思量,帐处蔡轮走了进来,躬身禀道:“孙先生来了。”
“快请。”孙旭东急忙起身,对这位大才,他一直保持着足够的尊敬。两天之前由他导演,景监主演的大戏确实是太精彩了。
孙先生坐在二人抬上,伸手接过蔡轮递给的陶碗,喝了一口水道:“校尉大人,咱们从白国到这儿时日已是不短了,也不知那边的情形到底如何,总是有些放心不下。”
孙旭东点头道:“先生说的是,我也有些不放心,咱们弄的动静弄得实在太大了。景将军派去的细作一个都没回来,想来济城看守很严,估计三国还在跟白军接仗吧。”
“是啊,所谓知已知彼,百战不殆。这消息不通,咱们就好像是瞎子,眼前的事也只能是估摸了。”
孙旭东听着孙子的名言,心中叹了一口气,只可惜此孙子非彼孙子,要不这样的现场直播世上有几人能听到啊。忽然心中一动,大声令蔡轮:“你速速带着人,不拘到哪里,去替我逮些活鸽子来。”
看着孙先生瞪大双眼,孙旭东故作神秘地一笑:“等他们捕来了,先生就知用处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