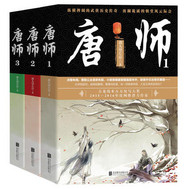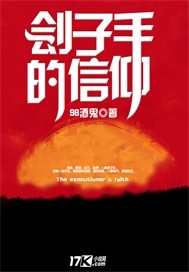花儿坡营中军帐里灯火通明,帐外南宫手按腰中铜剑亲自守候,大帐内孙旭东等三人已和景监见面寒喧已毕,围坐在他身边听他说话:“景监夤夜至此,实有三事与诸位相商。”说罢先将大鑫朝堂的政争和盘托出。
孙旭东一直边听边玩味景监叙说中的大鑫朝堂里纷繁的政治格局,他不停地在头脑中检索,大鑫类似于哪个朝代呢?翻开中国历史,无论哪一朝哪一代都是派系林立,相互间明争暗斗,景将军嘴里的大鑫好象是一个综合体。但不管哪种情势,也只需用利益二字来概括足矣。借用来的世界里的一句话就是:没有永远的合作,只有永远的利益。
景将军说完三人都在思忖,孙先生默然良久抬头说道:“久闻鑫国太子伯齐干练旷达之贤名,历次上书鑫王要求变法刻意求新,发奋图强之心令人敬服。臣相甘虹豪门望族,老辣祢坚,虽非相国,实有相国之权。其身后还站着一大帮豪门望族。不知大将军想过没有,太子的变法一经施行,表面上看能让鑫国国富兵强,但得害最大者为谁?正是这些鑫国赖以为基石的豪门望族哇。”
变法?孙旭东脑子里急速地回忆历史教科书,中国古代战国时期有很多诸侯国都曾经变过法,好象大多是都半途而废,只有商秧在秦国的变法最为彻底和成功,为后来的秦始皇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商秧变法的具体做法在他脑子里已经有些模糊了。
“太子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实为憾事。老鑫王为政一向默守陈规,怎会为镜中花般的新法去开罪那些豪族呢?太子虽得太叔公所助,但过早暴露实行新法意图实为一步错棋,其实只要想一想,变法之说并非太子最先,其他六国都有说者,为何都只是听打雷而不见雨下呢?是以太子上书不但说服不了老鑫王,还会为自己处处树敌而埋下危机啊,从大将军目下的处境足可突窥一斑了。”孙先生说完目视着景监。
景监连连点着头,鼻梁上微微有些汗珠,当初太子上书老鑫王要求变法图强,自己兄弟着实在后面怂恿了一把,虽然当时也曾想到了会有人反对,但没能想得甘虹他们反应会这么激烈。总觉得对国家有大利的事,作为大臣吃些亏是应当的。他盯着孙先生问道:“景监受教了,还请先生教我,太子当何以处之?”
孙先生微微一笑:“无他,六个字足矣:当其位谋其政。”
景监低头略一思忖,哈哈大笑道:“先生所言令景监有茅塞顿开之感。这第二事却和大鑫西北之向的胡人有关了。”
胡人入侵在中国历史上犹多,特别是在汉朝时期的匈奴,这一点孙旭东是了解的,武帝以前大都是以纳贡,甚至以公主和亲来换取边境的和平,直到汉武帝时期,倾全国之力经几十年,最终将匈奴打得一厥不振,从此不再为患。从景将军的叙述中好像他说的胡人远没有当年的匈奴强大。他整理了一下思路说道:“大将军,胡人之患,并非一日之功便可清除。但对付胡人以军**防之策标下以为甚为不妥。”
“哦” 景将军目视着孙旭东,“那你说说看。”
“此次胡人聚拢攻城,大将军尽可不必担心。蒙大将军只是一时不能适应胡人战法的改变而已,得太子援兵相助后定可大获全胜。”
“这是为何?”景将军见他说得如此肯定,问道。
“胡人何以能为患?就是仗着人数分散,行踪飘忽不定,骑射功夫好而已,而这些东西对于攻城掠地来说用处不大。他们此次将人数聚拢,攻取城池正是以已之短攻敌之所长,必败。标下所虑的是,将后对付胡人的方法不能再是军**防了。”
景将军大以为然,欣然问道:“那以君武之见呢?”
这条经验汉朝大将霍去病早已总结出来了,此时不妨照搬就是:“以飘忽对飘忽,以骑射对骑射,丢弃被动的防守,改为主动进攻。只要统兵之将谋划得当,当可永禁边陲。”
“好!”景将军拍案叫绝。这是一种全新对胡作战思路,不管是否有效,都值得作些尝试。景将军很是兴奋,呵呵笑道:“今晚真是不虚此行,再说第三事。”
这次等景将军说完,三人都笑了。旷都尉说道:“想必是校尉大人见大将军时,有些事忘了说了,徒让大将军烦恼。”景监望着三人神情轻松的模样,很是有些疑惑:“莫非君武还有事瞒了我?”
孙旭东笑道:“不敢,标下觉得不是什么大事,也就没提了。”说罢即将在白国太子府中缴获籍嫡之事禀告了景监。
景监听完大喜过望,哈哈大笑过后说道:“你这家伙,如此重要国器竟然还不是什么大事?”孙旭东确实不知道那籍嫡有什么来头,便问道:“那请大将军告诉标下。”
景将军心中高兴,看了一眼孙旭东呵呵笑道:“真不知道?好,本将军告诉你。当年大忌国强盛之时,每次分封诸侯国即看国之大小铸配籍嫡,由诸侯王自行掌管,以便分管治下奴隶,像咱们鑫国这么大的诸侯国也只配了两根呢,有些小诸侯国则一根都没有。白国灭了几个诸侯国,想必也抢夺了他们的籍嫡,是以太子府中也有一根,不想竟被你们所得,实是天意呀。”
“既是这样,那这根籍嫡就由将军上交鑫王吧。”孙旭东听罢也很高兴,不过在他眼中看来,那东西也没什么特别的,如果放在来的那个世界里,随便在哪个小县城里大约也能仿造个十根、八根来。
“不可。”孙先生说道:“白国失了籍嫡,可能正在四下查找。大将军将此物上交,万一走露了风声,又会带来麻烦。”
景监点点头说道:“孙先生所虑甚是,还是用此物替南宫他们除去奴籍后即原物奉还。”
孙先生听罢微笑道:“难道大将军只用它来除去南宫护卫的奴籍,不想用它来除去心腹大患吗?”
*********************************************************************************************************************************
朴阳城令躬身目送着远去的轺车队,心中不住暗骂:入你奶奶的,一晚上就挥霍了老子五十金。
轺车队最前的骑甲高举着几面大旗,表明了轺车队主人的身份就是鑫王派往护边大营,查实大将军征用军奴的廷尉府廷尉张栋大人。此刻他正坐在宽大的轺车里,一双小眼不时看看两边车窗外并不美的景色。轺车前面是几十名步兵护卫,拉大轺车和头前骑甲的距离,用以防止马匹扬起的灰尘呛着了廷尉大人。
快到田齐时,张栋就见前面大道旁,景监已经带着营中的副将、将参、校尉等在路边恭候了。这让他心里很舒服,看来这次真的是抓着这家伙的把柄了,记得以前每次到他营中,他最多只是接到大营辕门。张栋靠背用力地伸了个懒腰,冷笑了一声。
轺车队停下,张栋是鑫王特使,景监按规矩带着手下行了参见礼后,神色间甚为谦恭地亲自扶着廷尉大人上了轺车。张栋心里那个舒坦,和将参王平会了一下眼色后,高昂着头登上了轺车。
景监中军大帐里已经摆下了接风的酒宴,空气中充满浓烈的酒肉香味。两排小几上盛食之物竟然使用的是铜鼎,装酒的器具也是使用的铜爵,这在军中可是奢侈之物,一般情况下都只是会使用精致些的陶碗。鑫军中生活清苦,如此规格接待是极少有的事。
酒宴伊始,景监斟了满满一爵酒举起说道:“廷尉大人远道而来,一路甚是辛苦。军中原本不许饮酒,但今日既为廷尉大人接风,也只得破破例了。来来来,廷尉大人,景监先干为敬。”
张栋皮笑肉不笑地听着,见景监举爵干了双手一亮爵底,咧着嘴笑道:“本廷尉可不止一次到过景大将军营中了,先前可都是白水煮青菜,今儿是怎么了?又有酒又有肉,倒真叫本廷尉有些难以置信哪,啊?”说罢阴着眼笑看景监。
眼见张栋满脸神色傲慢,说话中尽是骨头,大帐中景监的心腹们无不心中暗怒,他们真不知景大将军为何会一反以前的作派,对这鸟廷尉如此客气。只有将参王平和他身后的两个心腹,满眼幸灾乐祸地看着景监。
景监眼中的怒火稍纵即逝,仍是双手举爵呵呵笑道:“头几次廷尉大人到我营中运气不好。昨日本营兵士外出打猎,收获颇丰,是以今日得以酒肉款待廷尉大人和一众弟兄们,请各位放量尝尝这边城的野味。”
“哈哈,看来本廷尉这次运气不坏,好,本廷尉陪大将军干了这一爵。不过过会儿还有公务,酒嘛,点到即止。待公务一了,再陪大将军一醉方休。”说罢仰脖将爵中酒一饮而尽,对着景监亮了亮爵底。
再有人向张栋敬酒,均被他以公务为由推辞。尽管大帐中酒肉飘香,一顿饭众人却吃得索然无味,不到一刻,张栋即推席起身,景监一见,便也下令让人撤去酒席。
张栋站在正中,冷眼看着兵士们把用饭的小几搬了出去。大帐中除了几名他的亲兵只留下了校尉以上的军官静静站立在两侧。他撇了撇嘴,手入怀中咳嗽一声道:“大王有诏,景监跪接。”
景监急步走到张栋身前跪下,大帐中两侧的人也都跪倒在地。张栋扁平的脸上露出一丝冷峻,看着跪伏在脚下的景监,心中怎一个爽字了得?
“大鑫国平王诏令:今有人报鑫国护边大将军景监,目无国法,擅征军奴从军。着廷尉张栋,即日赶赴护边大营查实回报。景大将军,请接诏令吧。”
景监高举双手过头,接下张栋递过来的诏令。张栋嘿嘿一笑后板着脸说道:“这就烦请大将军派人将中军护卫都尉南宫措、中军护卫亲兵赵刚、虎翼军队率赵猛、还有前卫军队率其食带来吧。”说罢冷笑紧盯着站起身的景监。
大帐之中景监的心腹们暗暗心惊,他们并不知道南宫他们曾被打为军奴。难怪大将军今日对这鸟廷尉如此迁就,可是迁就了那廷尉也未必领情啊。
景监叫了帐外的亲兵,吩咐他们立刻将廷尉大人要的人带来。看着景监面容上略带无奈的神情,张栋用心品味着猫捉老鼠的快感。
一时南宫等四人被带到中军大帐,景监令四人参见廷尉。四人行礼后便直挺挺地站起身,让张栋心里很是不爽。他冷笑一声:“也不知四位到底是大鑫国的军官呢还是白国的军奴?如果是大鑫的军官,那不妨就这样站着,如果是军奴那最好还是跪下。”
四人冷眼看着张栋,一声不吭。张栋压住了怒火,冷眼看了一边的景监,就见他焦急已见于颜色。便围着四人慢慢转圈,像是自言自语道:“还是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好,是什么样的人便在你肩头上按那么一小下,就算你扒了那块皮也还能留下疤。”一圈过后停下脚步,突然对着等候在帐门口自己的亲兵暴声吼道:“来人,扒下这几个贱奴的上衣,现出他们的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