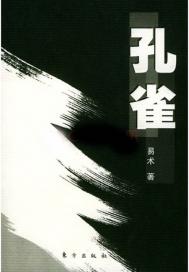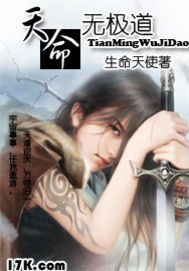不知道沉睡了多久,醒来,苏娅心里空空荡荡,一时不知身在何处,窗外的阳光与树叶被热风翻动着,像谁的心灵:暴露无疑,又不被洞悉。
广州的8月,热得人浑浑噩噩,分体式空调似乎也有点招架不住,发出不正常的微茫的蜂音。市声迢遥,仿佛被暑气的棉被盖住,变成了异国他乡的风俗。
她从宽大的床上,慵倦坐起,瞧着阳台上一只精致的白色花篮里,吊兰的茎须与她深有同感似的缱绻地蜷曲。光着脚丫,披着丝质睡袍,从这一个房间走到那一个房间,又从那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她仿佛要找一份心事,也找一份失落。找来找去,找到厨房,打开冰箱,才想到自己饿极了,正要找什么东西填肚子。
儿子跟保姆到楼下花圃玩去了,客厅地毯上放着她前天从深圳回来,送给他的一条袖珍剑齿龙。在过去做总经理的日子,每次她回家都送给他一件不同类别不同形状的恐龙玩具。关东与大多数孩子一样,也酷爱谁都没有见过,但好像谁都见过的侏罗纪恐龙。苏娅针对儿子的嗜好,便有意花钱请人到处去搜罗高档的恐龙玩具,满足他的奢望,这里不排除她心中有自私的一面:让不在身边的儿子对她产生某种程度上的盼望和期待。她时不时问他:
“想妈妈吗?”
“想。”他认真地说。
“小伙子,你真是妈妈的乖孩子。”她伸手摩娑他柔软的头发,幸福地赞扬儿子。
“我也想恐龙。”他更认真地补充道。
她摇摇头,笑微微又问:“假如妈妈没给你买恐龙,你还会想我吗?”
他考虑了一下,如实回答:“想!”
她大笑,大笑之后,心中不免又有些空空荡荡。
空空荡荡,就像一幢曾经住满人,现在大伙都搬出去,等待被拆毁的房子,问题并不在于拆毁这事实本身,而在于拆毁前难耐的凄凉和孤寂。苏娅不知道一个人怎样在突然迷惘与突然明了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闲来的愁绪,于滚滚红尘中一个成熟的女人,如此真实,又那样虚无缥缈!
室内有暗香浮动。
嗅觉上仔细分辨出空气中的蛛丝马迹,原来是自己身上散发出的女人特有的体香。她无意间走到穿衣镜前,似乎想从镜中找到那氤氲的“体香”,仿佛它真的是一种具象的物质。
吃东西可以填饱肚子,但四肢无力的缱绻反而更无可救药。她无意间又解开睡衣的腰带,对襟敞开,在银色丝绸之间,露出一片黑白分明的地带,其中赫然入目的“爱情最黑的部分”,让她无端地**了一下,腰肢一扭,睡衣从滚圆的双肩滑落下去,赤裸的胴体,哀怨地凸现几何学中最柔情四起的线条。记忆中,在与聂小刚即将结婚的前一天,她也这样对镜审视过自己,并产生了少女的强烈的献身欲望,只是由于他手中的一只该死的脸盆,像一道铁幕,遮断了彼此的青山绿水:铁幕这边是自己与关山海的“冷战”世界;铁幕那边是一道无解的一元二次方程。既然骰子一掷永远战胜不了偶然,你顺从了命运的安排,又遵照了心灵的规律:你是否一直在寻求某种对称,就像你此时的对镜自鉴?白与黑,情与欲,聪明与糊涂,纯洁与瑕疵,骄傲与虚荣……等等等等,从来就不曾泾渭分明。在更为开放的时候,一个女人的幽闭可能更深。你因此孤芳自赏,充满对自我的怜悯。
“这是你的悲哀,也是一切真女人的悲哀,苏娅。”她想。
她这么想着时,便已释然。
她重新披上睡衣。
然而,一双丰乳在丝绸后面微微震颤,一种咄咄逼人的东西逼迫她拿起了手机,打通丈夫的手机:“山海。我想**。”
“你……你说什么啊?”他问。
“我要你,现在就要!”
“……我正忙着呢。”他好像愣了愣,似乎有点喘不过气来,“你发什么神经?”
“谁啊?”电话里隐约传来女人的嘀咕声,“讨厌。”
“我真的很忙。”关山海掩饰说,“对不起,老婆。我……”
“你忙得好事!”苏娅猜到了他在做什么,没收线,就把手机扔到床上,仿佛它蜇手似的。
她萎坐在地毯上。此时,她多么渴望有个男人破窗而入,把她糟蹋,而且他最好是一个肮脏的白痴!当你把一件高贵的瓷器,送给某人,而他不仅不屑一顾,反而去玩弄一些质地粗糙的碗碟时,你愤而想掷碎那精美之物,无论它多么价值不菲。
但女人在室内的冲动,一出门八成就会烟消云散。她换上一身极富性感的衣裙,涂脂抹粉,遍洒巴黎香水,走下楼梯,准备到什么地方去破天荒体验一回做“鸡”的感觉。这时,儿子和保姆回来了。
“妈妈,您要回深圳上班吗?”关东脆脆的童音,让她顿觉无地自容。
苏娅的脸像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艰难一笑:“噢,不。孩子。”
“您为什么不去上班?”
“瞧你,小伙子……妈妈不好……”她语无伦次地说,“你为什么希望妈妈去上班呢?”
“因为……”他似乎也有点不好意思,说,“因为妈妈去上班,回来时就会送一个恐龙给我。我爱您,妈妈!”
她赶紧抱起儿子,把自己的面孔掩埋在他弱小的肩膀上,蹭来蹭去,直到她感觉夺眶而出的眼泪,被他的衣襟擦去,才抬头,说:“傻孩子,别老想玩具啦。下个月,你就要上一年级啰,正式成为一名骄傲的小学生!”
没想到关东的入学,竟颇费周折,让她体验到办孩子入学手续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一点也不比申办出国护照容易。
不声不响,好朋友黎曼就办好了一切手续,万事俱备,只差买一张直飞悉尼的机票了。
投资移民澳大利亚,不日将背井离乡,黎曼不免有些伤感,与苏娅在花园酒店荔湾亭喝下午茶,觉得这个下午格外阒静,也格外漫长。走来走去的侍者手中的托盘、瓷器和玻璃杯一尘不染的悄然的碰撞声,如同两人的思想,怎样会意,又漫不经心?
“你知道,”黎曼说,“父母很爱我。但他们不愿看到我自溺于某种情感,就忍痛割爱,叫前几年就已经去了澳洲的我哥,给我搞掂了这个投资移民。而我自己,也觉得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了,需要换一种新鲜空气,换一种呼吸的方式。”
“对。”苏娅说,“你不能老是听蟋蟀在弹奏着什么,或把一支老掉牙的歌唱一百零一遍。”
“可是,”黎曼说,“其实我不想走……”
“其实你也不想留。”苏娅补上她的话。品茗一品,既品味黎曼,也品味自己。
“你与关山海的关系,”黎曼停了停,问,“近来怎么样?”
“就那么回事呗。”
“就那么回事,就意味着有事。”
“可我都差不多麻木了。”苏娅又想起那天手机里响起的女声:“讨厌!”这是汉语中目前最让她恶心的词儿。
“你这么说,说明你并没有麻木。恰恰相反,你很清醒。一个人太清醒,与一个人太傻一样可怕,尤其当这个人是女人时。”
黎曼的话,使苏娅蓦地想到“太傻”的李修玲,便问:“你去看阿玲了吗?”
“最后一次见到她,已是一个月前的事了。”
“我也是。好像有三个星期,她没给我打电话了。”苏娅说,“不对。自从春节过后,她每个星期都打电话告诉我,她收到了情人寄来的‘勿忘我’是多么幸福,那个奶油蛋是多么爱她,阳光是多么灿烂,雨声是多么动听。她还准备写一部叫‘勿忘我’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献给那个‘天字第一号情人’。莫非她整天忙于闭门造车,把我们都忘了?”
“我正想与她道个别。我们一块去她家看看吧。”黎曼说,“听你这么一讲,我担心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不会吧。”苏娅嘴里说,与黎曼走出酒店,坐上了她在深圳与一个外商做生意时赚得的白色跑车,心里也有点不踏实。
到了文昌北路,泊了车,步入一条小巷,踢踢踏踏上了楼,敲门。
李修玲的丈夫黄爱军个子瘦高,戴一副小眼镜,剃了个小分头,极像在天津张园做寓公时的末代皇帝溥仪。苏娅因与他久不见面,礼节性地叫了声:“黄科长,你好。”
他立即纠正道:“我不是科长,只是个副科长。”
“几年前,你不就做了副科长吗?”黎曼说,“怎么还没扶正?”
他从冰箱里拿出两罐饮料,一个一罐,放到她们面前的茶几上,还一丝不苟地插上吸管,然后打开一把折叠椅,在一边陪坐着,双手放在膝头上,说:“我们机关比我能干的人多的是。”
“你太谦虚了。”苏娅说,“我们来看看阿玲。她人呢?”
“在睡觉。”他抬头瞧瞧墙上的石英钟,说,“睡了47分钟。”
苏娅与黎曼对视一眼,似乎有点惊奇,又有点感动,为老婆睡觉计时的男人,好像是一个新生事物。前者说:“你对阿玲太好了。你常这样守着她吗?”
“我不守着,谁守?”
“阿玲怎么啦?”黎曼问。
“她还能怎么啦,神经病嘛?”
“她又犯了?”
“唉……我差不多已习惯了她的神经病。说句并不可笑的笑话,当你跟一个神经病配偶生活一定时期后,一旦哪天她不神经病了,你自己就会重蹈她的覆辙,变成神经病。所以,我心甘情愿侍候她,有时甚至暗暗祈愿她永远……永远……”说着说着,他低泣起来。
“你怎么啦,黄爱军?”苏娅和黎曼不约而同站直身子,惴惴不安。
“你们请坐。”他拿下眼镜,抹一把泪花,说,“对不起,我有点激动。”
“你刚才说,你暗暗祈愿她永远……”黎曼问。
“永远疯下去。”他平静地说。
“什么?”黎曼又虎地站起。苏娅拉了拉她的手,说:
“黄爱军。我知道,你太爱阿玲了。”
“是的,我爱她;但她,并不爱我。”他摇摇眼镜,说,“她被一个小白脸弄成了神经病,活该!”
“这不是你的心里话。”苏娅说。
“你错了。现在,她是一个疯子,我是一个疯子的监护人,面对她,我具有了一种她疯时我从来就不曾有过的优越感。这比我做一个小小的副科长有滋味得多。”
“我不相信。这不是你的肺腑之言!”苏娅说,“你一定是已经忍受不了她的疯狂。你被她的病折磨得绝望了。这个家还像个家吗?孩子被送到了姐姐那里寄养。你是多么希望阿玲能成为正常人啊!你骨子里其实最疼爱她……你是一个好人,黄爱军……”
苏娅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黄爱军吃了一惊,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从面巾纸盒里抓出一把纸,递给苏娅。苏娅接过,从那把面巾纸中拎出一张,轻轻揩了揩湿润的眼眶。当她恢复常态,再看黄爱军时,后者捧着脸,指缝间的泪水,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一瓣瓣,砸在尘埃落定的地毯上,浸洇,然后消失。
黎曼又拿起那把面巾纸,塞给他。他紧紧握住它,像紧紧握住她的问候和安慰,却并不使用。两个女人,都从未见过一个男人如此坚强如此安静的哭,如此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以至于他们内心由衷赞叹:这个不起眼的前司务长,才是一条真正的男子汉!
黄爱军告诉她们:春节过后,不知为什么,李修玲每星期收到上海方面寄来的“勿忘我”,署的是那个‘奶油蛋’的名,她因此一度精神稳定,面貌一新;一个月前,她终于感到了其中的蹊跷,为什么他只署名而不留地址呢?恰好,一个从前跟她一块搞广告的朋友,从美国回来看她,告诉她在旧金山碰见过那个奶油蛋,并同他吃了一顿饭,后者年前就到美国去混了。显然,那些“勿忘我”不是他寄的。她明白事实真相后,马上又疯了,而且比以前疯得更完全彻底!
苏娅和黎曼目瞪口呆!
“真该死!”苏娅随之捏住饮料罐,使之变形,说,“那些花,正是我叫一个朋友从上海假冒那个混蛋之名寄来的……”
“不,”黎曼仿佛为了承担责任,忙说,“不是苏娅,是我……”
黄爱军苦笑道:“你们心里不必有什么不安。其实,我早已猜到是你们的所作所为。你们是阿玲最好的朋友,一切都是为她好。在此我代表她向你们表示最真挚的谢意!阿玲,作为一个人,只存在一个肉体了,进疯人院是她最后的归宿。我之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把她留在家里折腾,是因为想尽量多争取一点时间同她在一块,尽管这对我来说是多么地痛苦和困难。你们来这里之前,精神病院还打电话催我把她送去。”
说到这里,他再次抬头瞧瞧墙上的石英钟,接着喃喃自语:“她已睡了2时13分钟,她睡得挺安详,她的睡姿很美,不是吗?我想至少等她睡完这一觉,睡完这一觉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