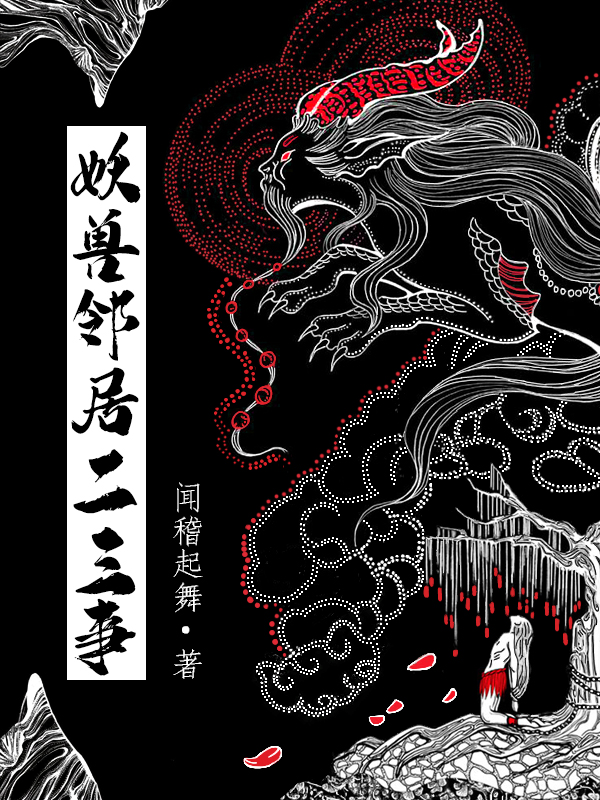护训队两年很快过去了,苏娅被分配在空军A医院。又过了两年。春天。她被选拔到湘东医学院进修高难度静脉注射。
无事的时候,她常到湘江边漫步。湘江边一排排倒扣的小舟无事地趴在懒洋洋的春阳下,像一个个睡得正香的无人照管的孩子,令人感动。
江水湍急,混浊而又金黄,向东流去。与江水的流向相反,她在沙滩上走走停停,有一种无形的被洗涤的感觉。
不知为什么,这种感觉很舒服。
湘东有座回雁峰,去年南飞的大雁今年又北飞了。尽管北方对她来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她仍有一丝莫名的惆怅。
18岁,正是少女多愁善感的年龄啊。
远远见一人在湘江大桥下挥毫作画,戴一顶凡高式的草帽,大红的衬衣扎在牛仔裤的裤腰里。她慢慢走近,觉得他像某个人,又弄不清楚他到底像谁。
一阵大风吹过,把他的草帽吹到她的脚下。草帽如此破旧,让她有点不屑。她下意识抬脚,踢了草帽一下。他回头与她对视了一会儿,转身走过来,问:“我的草帽惹你了吗?”
“你首先,”她自己给自己做个鬼脸,敏捷地回避了他的问题,说:“你首先应该去问这风,你的草帽惹它了吗?”
他摊了摊手,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风是没答案的。”
“我也是。”她倔强地说,好像需要抵挡着什么。他的目光明澈而又深湛,有一种不可言传的东西,使她觉得这比他的话语更显得意味深长。她问他在画什么。他把她引领到画架前。一副未完成的油画:一座大桥。
“你画得很棒。”也许是为了掩藏心中的不安,她脱口而出。
“除了你,我记不起有第二个人给我诸如此类的评价。”
“你喜欢表扬?”她镇定了自己。
“为什么不呢?”
“那么,听着。”她捋捋头发,说:“我的表扬是:除了画画,你可以干任何其他的事。”
两人爽朗地笑。他告诉她:他其实学的是桥梁建筑专业,对桥情有独钟。画桥,消遣而已。大学快毕业了,日后的职业肯定与油画无关。
“是这有缘的风,让咱们认识了。”他挥毫往空中画了几笔,说,“我姓聂,三只耳朵,叫聂小刚。”
她一惊,一愣,一叫:“天!咱们不是早就相识了,在信上!”
这得从苏娅发表处女作说起。
她发表处女作,源自一个夜班。当时,她睡思昏沉,右手的钢笔还在掌握中,左手的日记本已悄然滑落在地板上。日记本上有她的抒情习作。正巧,在苏娅所属的内科疗养的著名老作家汪健,夜不能寐,披衣来到护士值班室,想找人聊天,见苏娅在蜂窝炉边打盹,也不惊动,弯腰拣起那本子,粗粗一读,若有所得,细细再读,就颇有点爱不释手的意味,当即叫醒苏娅:
“小家伙,你写的,这东西?”
她睡眼惺忪,点点头。
“回头你摘抄几首小诗。我拿去给你发表。”
“发……表?”
“也就是说,让更多的人了解你丰富的内心世界。”
“那多残酷!”她本来想说“那多不好意思啊”,说出来时,竟变成了这样一句无端的话。老作家点点头,还认为“残酷”二字用得好。她真的不好意思了,面孔骤然飞上两团红云。
三个星期后,她的诗“残酷”地发表了。
对新生事物怀有浓厚兴趣的护士长,举着报纸,从病房走廊那头向这头跑来,一路快乐地嚷嚷:“快来看,快来看,咱们苏娅的诗刊出来了!”
她还大声朗诵苏娅的作品,在医生和病人的包围圈中。
朗诵完毕,一片寂静。护士长正要不解地说句什么话,掌声突然四起。
远远地站在一边的苏娅,浑然不觉已泪眼模糊。
之后,她陆续收到诗爱者的来信,其中就有聂小刚的。她与他相互通信达半年之久,才得以意外相逢。
湘江边的邂逅,玉成了一段情缘。
他第一封情书,差点使她酿成一起严重的医疗事故。
苏娅下楼去血库取血时,通讯员来了,递给她一封信。一见那熟悉的字迹,她怦然心动,竟有点不知所措,一会儿把信塞进口袋,一会儿把它拿出来,不敢贸然拆开。有人路过身边,她赶忙又藏住信,好像它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东西。
茫茫然取了血,她回到治疗室依旧茫茫然,心里老记挂那封未拆开的信。上“治疗班”的护士唐红从病房门边探头喊:
“苏娅,24床的输血交叉反应做完了,已挂上生理盐水,准备接血了。”
问题是,刚才苏娅下楼拿的是8床的O型血,现在要挂上24床的B型血。茫茫然的苏娅把O型血瓶套上输血网兜,出了治疗室,便往24床走去。那天,她上的是“临床班”,临时输血、输液、医疗处理,以及长期医嘱的输血、输液的中途换瓶,都属于“临床班”的工作。幸好,唐红清楚24床要的是B型血,当时,她正给26床打针,无意间瞟了一眼苏娅提着的血瓶,大吃一惊,喊道:“你疯啦!”
这一喊,使苏娅如梦初醒。一向工作严谨的她,吓出浑身冷汗。
聂小刚的信并不长,也没有多少想象中的甜言蜜语,只转弯抹角地从谈论如今留长辫子的姑娘越来越少这个事实开始,隐喻真正的爱也越来越少这个问题,并提到了流行在同学们中间的一个笑话:一个女孩,刚才还柔肠寸断地吻过你,可等你上了一趟厕所,出来时,发现她已变心。他希望能同苏娅建立一份真挚的情感。最后,仿佛不好意思,用英文写了一句:“I LOVE YOU!”当然,任何初中生都会写的短句,已足以使苏娅下决心为聂小刚蓄两条美丽的长辫子。
不久,聂小刚毕业分配到长吉。苏娅第一次去看他。他住在六楼的集体宿舍。单身汉乱糟糟的天地不会让一个爱整洁的女孩——尤其当这个女孩又是女军人时——看了顺眼。她请门卫老头打电话通知他下楼相见。收发室摆着一条饱经沧桑的长板凳。她端坐如仪。他也端坐如仪。两人都望着那老头。后者穿着一件奇怪的花花绿绿的百慕大短裤,也笑微微地望着他们,幽了一默:“怎么,还要我给你们照个合影吗?”
这才打破僵局。苏娅俏皮地向门卫行个军礼,拉着聂小刚跑到街上去了。
去了烈士公园,去了鹿头山,去了天心湖。日落西山,街上行人如织,车辆如梭。两人突然感到心里像一面晾晒了一天的床单那样空空荡荡,总觉得有一件什么事还没有去做。
长吉的风味小吃臭豆腐闻名遐迩,天心湖的臭豆腐排档更是名不虚传。两人津津有味地吃到第三块时,不约而同地问对方在想什么,又不约而同地提议把想法写在手心里。
一亮,手心里都是个醒目的“吻”字。
聂小刚正要把思想付诸行动,苏娅伸手挡住他,说:“满嘴的臭豆腐,咱们的第一吻不就变成了臭吻了吗?”
“闻着臭,吃着香嘛。”
“臭吻”一吻就吻了个轰轰烈烈,直吻得其他吃排挡的人都变得坐立不安为止。
这纯洁的一吻,直吻了四年又三个月,它的力量却又居然不及一个瞬间的电话。
信不信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