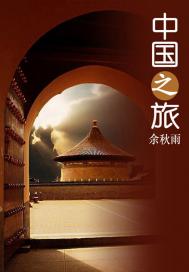春节前,关山海把一批氧化铕卖到香港,赚了数目可观的一笔钱。春节后,关山海就搬出单位的宿舍,住进了在天河新村租赁的两层小楼。
这时苏娅怀孕了。
这时苏娅也学会了做菜。
初八这天,关山海的几位商界朋友带了鞭炮(那时广州还没有禁止燃放爆竹),前来天河新村拜年并恭贺乔迁。关山海在客厅里陪着客人说说笑笑,苏娅则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弄饭菜,把每一道菜都弄得像她的诗歌一样精致。
客人们吃得有情有绪,称赞苏娅多才多艺多漂亮,苏娅不过浅浅一笑,倒把关山海听得心满意足。
吃过晚饭,关山海对苏娅说:“我们要谈点事情,你回避一下吧。”
苏娅就回避到天台上去看街景,望星空。站累了,苏娅回到卧室,想看看书或写点东西,但客厅里的交谈很激烈,让苏娅心慌意乱,烦躁至极,干脆开了门,上街溜达。
眼前无非是些一动不动的房子,和动来动去的人。
广州越来越繁华,可苏娅突然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独。过来了一辆公共汽车,也不知是哪一路,苏娅下意识地踏了上去,在车厢尽头的座位坐下。售票员问:“去哪?”苏娅也不知道去哪,递过一张零钞:“到终点站吧。”
车到终点站,苏娅又上了另一路公共汽车,坐的还是尽头角落里的位置,还是终点站。
一路上,苏娅入痴入迷地看,入痴入迷地想,却并不在乎看明白什么,想清楚什么?什么都是,又似乎什么都不是。
这大约就是佛家所谓的超脱。
当然苏娅不可能超脱。晚上十一点半,苏娅换乘过五辆公共汽车以后,又回到了天河新村。十二点她值夜班。
关山海与朋友都没有觉察苏娅出去了四个半小时又回来了。
换好上班穿的衣服,苏娅用卧室的电话拨通了关山海新购的手机,说:“我要上班了。”这是苏娅搬到天河新村后第一次上夜班,从这儿到B医院,一路上好多人家养着动不动草木皆兵胡乱吠叫的狗。苏娅惟恐哪一条冲撞出来。她好希望今晚丈夫能送送她,可关山海一点也没有要送她的意思,只说了句:“那你去吧。”就收了线。
在院子里推单车时,苏娅磨磨蹭蹭,仍希望丈夫能跟出来,结果,没有。
好在那些狗只是在看不见的地方虚张声势,并没有真的扑上前来。
正好在医院门口碰到刚下班的黎曼,黎曼也在年前嫁人了,嫁的是本市一位大人物的公子。那公子早已在外面泊了一辆“奥迪”,此刻,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啵啵”按响喇叭。
黎曼见苏娅独自一人,好生奇怪:“怎么,深更半夜的,‘倒霉鬼’也不送送你?”
苏娅笑一笑,说:“他不在家。”
早晨下班回家,关山海已经出门。空荡荡的房子里犹如台湾诗人郑愁予“小小寂寞的城”,只是门外没有过客,也没有马蹄声“得得”踏响。
一个人没滋没味,苏娅中饭也懒得做,也不想吃,只把一颗话梅、一点落寞和几缕伤感,含在口里细细品味。
睡了一觉,忘却了诸多不快,苏娅收拾好散乱的心情,晚饭做了几道关山海爱吃的菜。但左等右等,拨通了他的手机,他说忙,不回来吃了。
“不回来吃怎么也不来个电话?让我白做了许多菜。”
“我这正商量事咧。好啦,就这样吧,你吃完饭早点睡。”
苏娅哪里能睡得着?新住进来的房子她一时还不太习惯,入夜后益发显得冷寂,风吹动窗帘或者厨房里漫步的一只蟑螂,也叫她心惊肉跳。就算睡着了,万一一个恶梦惊醒过来,身边无依无靠,又怎么是好呢?
不敢睡也不敢在屋里久坐,苏娅就搬了一把折椅坐到二楼阳台,阳台上能看到一些人和一些人的欢乐,还可盼望晚归的丈夫。这样,心里踏实了许多。
闲闲地看几页张爱玲有檀香缭绕的小说,又信手握住几行飘游而来的诗句。不觉已是午夜。
这时才见到关山海的“千里马”悄没声息地驶到楼下。
苏娅赶紧回到卧室,换上睡衣躺下,她怕被关山海知道她在等他,怪她太儿女情长。
苏娅清清楚楚听见关山海开门,进屋,换上拖鞋,喝了一杯开水,踢踏踢踏上楼,她心里算计着在关山海推开卧室门时,她应该不应该睁开眼睛。卧室门却迟迟不开。
客厅里响亮地传来电视的喧闹,一听就知道本港台放送的深夜电影,曾志伟阴阳怪气地搅笑让关山海呵呵直乐。
苏娅最受不了曾志伟,终于忍无可忍,冲出卧室。冲出卧室看着关山海脸上难得一见的笑容,终不忍坏了他的兴致,便一言不发,改变主意进了洗手间,但返回卧室时,她还是忿忿地摔了一下门。
这一摔,摔出了大男人的脾气。关山海闯进卧室,把被子一掀掀在地板上。
“你在我的家里凶什么凶?”
苏娅“呼”地弹坐起来,哭喊:“我凶什么凶?你还算人吗?对怀孕的妻子不管不顾。你以为你能赚几个钱就不得了啦?你除了钱还有什么东西?”
关山海“啪”地给了苏娅一个耳光。
苏娅以关山海当年教导的敏捷,也迅即还了他一个耳光。
关山海恼羞交加,大吼:“你给我滚出去!”
一把攥住苏娅的胸襟,拎起来就往外走,拎到客厅里,才想起妻子不是说丢就丢,说滚就滚的,便只是扔在沙发上。
苏娅一开始动怒,就意识到很糟,只怕要害了肚子里的胎儿。果然这时肚子里有些隐隐作痛,苏娅立刻像突然停电的工厂车间一样,不哭也不闹了,静静地趴在沙发上,双手轻轻抚摩肚皮,额头上沁出一层虚汗。
过了半个小时,情绪才稳定,肚子也不疼了,只是春寒让她哆嗦不止。此时关山海已洗完了澡,钻进被窝对外面说:“睡不睡?你不睡我睡啦。”
何必跟自己和胎儿过不去呢,毕竟是自己的丈夫。这么想着,苏娅爬起身来,整了整凌乱的沙发巾,关了电视关了灯,回到床上,躺在关山海身边。
第二天去医院上班,苏娅抽空到妇产科作了检查,说是伤了胎气,有可能会影响到胚胎发育。苏娅惶惶不安,给关山海打电话,告知检查结果,说:“如果你担心有事,要不要做了?”
“做就做了吧。”关山海说。
苏娅心中一寒,想:“那么做掉吧,做完就离婚。”
苏娅知道,流产自然痛苦,但又有什么痛苦比心痛更难堪呢?
手术约定上午10时做,关山海没来,只有好朋友黎曼请了假陪在身边。黎曼一到就大骂关山海,拨通他的电话:“倒霉鬼,你有没有一点良心?苏娅要死了。你知道不知道?”
这一次关山海听到“倒霉鬼”,一点也没笑,一声不吭,挂了电话。
躺上手术台,苏娅突然感到自己再熟悉不过的手术室变得异常陌生,手术灯的光束、器械盘里的手术用具,散发一种银质的寒冷,医生和护士已戴上大口罩,俯视着她,现在她们不再是她亲密无间的同事,而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可怕的“职业杀手”,这更使手术室显得危机四伏。冷汗不停地渗出,她觉得自己仿佛漂浮在水面上,水面下是无底的深渊,器械悄然而清晰的碰撞声,就像打碎的玻璃一般尖锐。当她痛苦地闭上双眼,任凭那漂流的感觉裹挟时,黑暗的穹顶有一颗惨白的星星闪烁着……与此同时,隔壁产房传来一声声新生儿的啼哭,给她的震动不亚于一场雪崩。
她猛然坐起来,使一个护士惊愕得翻掉了手中的器械盘!
“对不起。我不做了。”
她逃离了手术室。
跑到街上。下雨了。苏娅扬手截住一辆的士,心中说:“孩子,妈妈一定要把你生下来。”
轻飘飘回到家里。正在书房用电子计算机计算公司利润的关山海问:“做了吗?”
苏娅冲了一杯冻奶喝下,说:“我的孩子,我为什么要做掉?我要好好地把他生下来。”
“生就生吧。”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