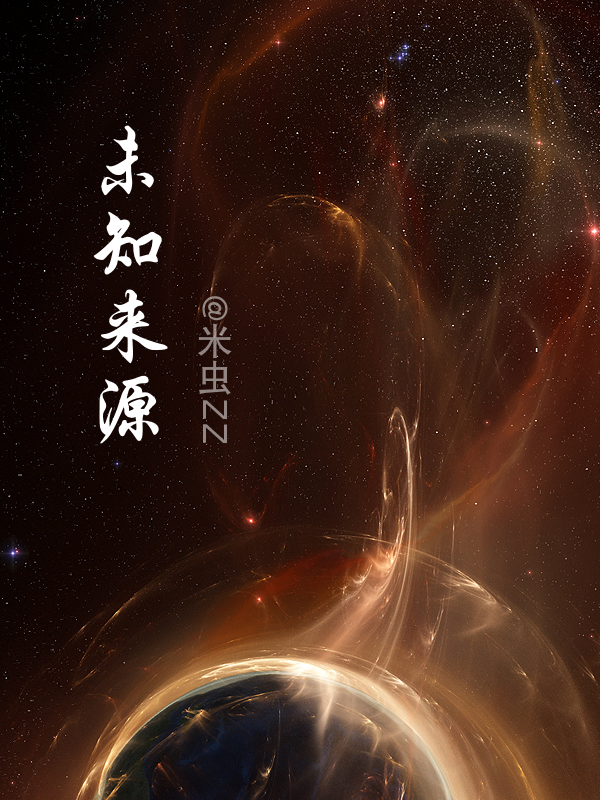与关山海结婚不到一个月,苏娅就从团卫生队,调到了B医院。以常理论,苏娅应该高兴才是,可她更感到茫然。尤其当她看到关山海那副沾沾自得、非他不能的样子,心里就不是滋味。调动是他跑的,跑得水落石出了,便拍着胸脯说:
“怎么样,我想搞掂什么事就能搞掂什么事!”
苏娅的嘴角不易察觉地撇了一撇,丢给关山海一句似是而非的话:“你真有本事。”
关山海吐出一个骄傲自满的烟圈,说:“我真的本事你还没见到呢!”
进B医院的商调函来了,苏娅心想:“算了,反正你苏娅已变成了关太了。”搬家时,关山海从广州开来了他的“千里马”。苏娅要去弄一辆货车装什物,被他制止了,说:“把这些玩意都扔了,值几个钱?”
苏娅也不与他争辩,便只整理一些书籍和一个小皮箱。站在一边的关山海踢踢皮箱,问:“这里面装着什么宝贝?”
“一些旧信件。”
“聂小刚的?”
“是的。”
“有什么用吗?”
“没什么用。”
“也带走?”他又踢踢那皮箱。
“你的意思是让我烧掉它。是吗?”她看着他的眼睛。
“你可以不烧,”他拖着腔调说,“我不介意的。”
638封信以及聂小刚的结婚证明并照片,足足在洗手间里烧了一个小时,四年又三个月的激情至此烟消云散。
关山海见苏娅烧得灰头灰脑,说:“你不是爱流泪吗?今天怎么倒没有?”
苏娅一边洗脸一边说:“嫁得你这等好先生,还流什么泪呢?”
“只怕你未必真这么想吧。要不,这些信也不会等到今天才烧了。”
“这不正是时候吗?我要到一个新家去了。”
开车前,正当班的李修玲穿着白大褂跑出来,与苏娅缠绵一阵,趴在车窗口对关山海左看右看,说:“你一泡上苏娅,一点也不像个‘倒霉鬼’了。”
车出西鹅,关山海忍不住问道:“李修玲干吗叫我‘倒霉鬼’?”
苏娅笑了那么一笑,说出了新兵连的这个掌故,把关山海听得大笑不止,勾起无数往事,说:“苏娅,有时我可能不讲理,但其实我还是LOVE你的。”
“多谢。”苏娅说,把头扭向窗外。
不日就是元旦,这是关山海选定举行婚礼的日期。
苏娅在B医院有几位护训队的战友,其中包括“死党”黎曼。苏娅本想请黎曼做她婚礼上的伴娘,但黎曼听说苏娅嫁的是“倒霉鬼”关山海,尖叫声与李修玲一样响亮,惟恐她对着关山海说出难听的话,就放弃了这个打算。最后干脆决定,自己所有的亲戚和朋友谁都不通知。
婚礼在花园酒店举行。人到得不多,只坐了四桌,但全都有头有脸,乘坐的小车一辆比一辆豪华,蝗虫般包围了花园。
来的多是领导,以及关山海生意场上的关键人物。新郎关山海忙得喜气洋洋。有身份的客人们倒不觉得怎么喜气洋洋,他们过惯了一丝不苟的生活,看报纸看头版,11点准时睡觉,在人前从不高声喧哗,笑不露齿,醉不失态,措词恰当,尊卑分明,更像是在参加一个常委扩大会议。
主婚人为出席本次婚礼者中地位不高不低的“老团长”。“老团长”在东北搞土改发动群众斗地主时练就一副宏亮的嗓门,至今宝刀不老,喊一声:“现在婚礼开始!”四座皆惊。苏娅与关山海恭恭敬敬并排站在“老团长”面前,心中暗笑:“这不是又在开斗争大会吗?”
当“老团长”高喊:“新郎新娘相互鞠躬!”新郎新娘忙左转右转,一弯腰,“咣”地碰了个响头。
事情很好笑,客人们也很想笑,但谁都不想先笑,结果谁都没有笑,就像碰响头是婚礼中不可或缺的仪式一样。
苏娅心中一惊:“糟糕,这辈子只怕是注定要打架了。”
真正有板有眼,有笑有闹的婚礼,是在关山海的老家关江进行的。
花园酒店的婚礼结束后,关山海偕新娘苏娅回到了关江。
到关江的路,遥遥远远,破破烂烂,就像路边一闪而过的一个乞丐身上穿着的肮脏长裤。离家大约还有10公里,“千里马”又犯老病了,闹一个别扭,横竖不动了。关山海鼓捣一阵,“千里马”只是干咳,电瓶总打不着火。关山海只好在路上拦车,好不容易拦得一辆比道路更破烂的农用运输车。进入小镇时,街道两旁的人都伸长脖子看一对身穿新装、胸前佩着小红花的新人,站在那越看越不像话的拖斗里,倍感稀奇。而苏娅看他们,就觉得有点夹道欢迎的意思,便十分开心。
不开心的关山海,满以为“千里马”在这贫穷落后的山区,会为自己挣足一回面子,殊不料它在即将到达目的地时,成为可耻的叛徒。
噼噼啪啪的鞭炮响过之后,关玉龙上前迎接苏娅,说:“妹仔,你跋山涉水,一路行军,辛苦了。”
苏娅向公公婆婆行过见面礼,被一群人簇拥,到房间里坐定,要不是关山海他娘止住,关玉龙又想掀开衣襟让苏娅看他腰间的弹洞,以证明他的确是个老兵。结果,只是取出那支老枪让苏娅摸了摸,心痒痒地要唱《我是一个兵》,终于忍住没唱。
当夜,关玉龙指挥众人,宰猪三头,杀鸡无数,为次日的“会师宴”(关玉龙语)“备战”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早饭过后,关氏家族几百号人马开始一拨接一拨地赶来喝“新娘酒”。如果只是喝酒、饮茶,也并不太麻烦。事情远非这么简单。吃喝者往桌边一坐,新郎新娘即趋上前,新郎介绍这是“23叔”、“48公”或“59婆”,新娘立马满脸堆笑,尊称“某公某婆”,斟酒、沏茶。“某公某婆”绝不端起杯子就喝,平时窝囊如阿Q的人,此时都变成赵老太爷,他们架子十足,偏要出些歪题让新娘难堪,让众人哄堂大笑,才皆大欢喜作罢。这是关江一带的“考新娘”风俗,过了这一关,新娘才算被族人正式接受。新娘应答不妥会被小看,喝“新娘酒”的人出不了歪题一样会被人小看,所以双方无不尽心尽力。
苏娅一向口齿伶俐、反应敏捷,大部分时候能对答如流,令喝酒者满意而去,不时赢得阵阵喝彩和笑声。
但也有别扭的时候。到“48公”时,就僵持了好一阵,无论是普通话还是广州话,“48公”听起来都像是广东的骂人话:“死巴公”,苏娅含含糊糊叫了声:“斯基伐莱公”,叫得“48公”小眼睛一鼓一鼓的。苏娅连忙子虚乌有地解释说英语中的“48”读起来便是“四季发财”,才将老想四季发财的“48公”半信半疑地蒙混过去。
“新娘酒”真是喝得久,一直喝到夜幕降临。苏娅持壶把盏的手软得像一条绳子,但脸上仍幸福洋溢。在这群像收割后的田野一样坦荡而纯朴的乡亲们中间,她感觉自己真正做了一回新娘。
晚上,按关江的传统习俗,又举行了一次婚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关山海今日也陀螺似的旋转了一天,使“千里马”带来的不快早一扫而空,他扳扳苏娅的肩膀,说:“老婆,好多人都说,你是关江最美丽最聪明的新娘。”
苏娅笑了那么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