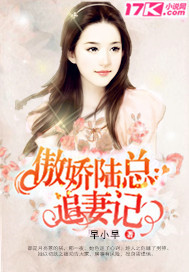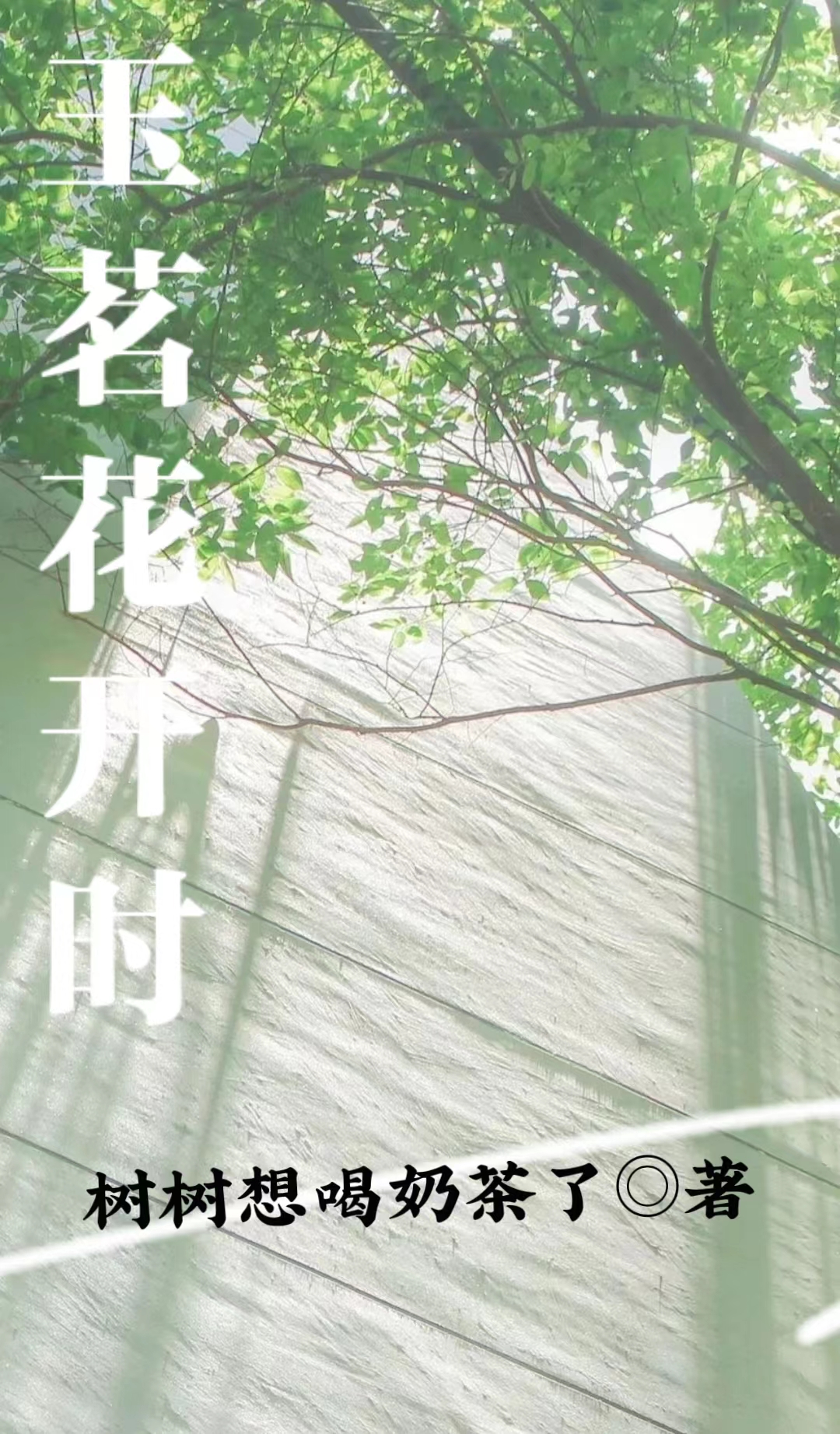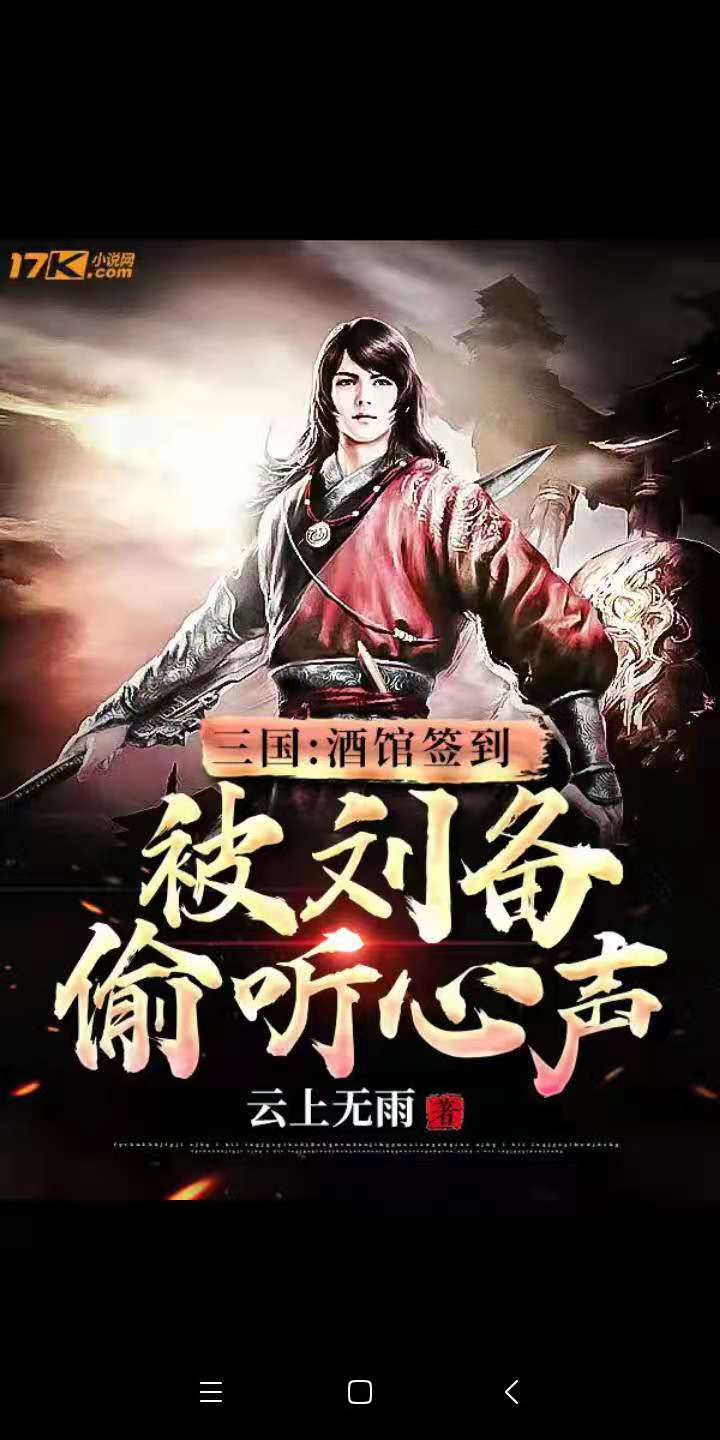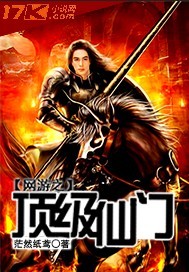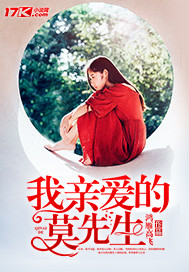第十四章 磨练
难忘的一年过去了,又迎来了艰难的漫长的另一年。
这年,中国不管是在国际关系上还是在国内经济上都发生了困难。国际关系上首先和一个大国发生了分歧;东南亚的某些国家和台湾掀起“反华大合唱”;国内由于预算失调,粮食发生了短缺;又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去年大丰收,而今年却大减产。中国的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
春天刚刚开始,格针岭的刺槐树发绿了,格针帐发绿了,桃杏花将要含苞待放,这会的格针岭应该是一个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可今年,此地已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去年冬天至今年春天,雨雪很少,土地干裂,溪水断流,就连那脱蘑山下的“鬼翻锅”的大泉子也翻不出水来了,加上公共食堂为解决烧草大量的砍伐,村边、山下的刺槐树林和格针帐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眼看这小小的像世外桃源的格针岭,将要变成光秃秃的一个小山寨了,鸟儿不来了,野兽也躲走了,代替它们的将要是干风和沙尘,干旱和风热,气候的干湿调节和防风的屏障活活地被公共食堂烧掉了。这会儿格针岭的风光真是显得有些萧条冷落了。
八里屯的大街小巷里都闲谈议论着公共食堂将要停火的烦心的消息。
上级下达指示:要求社员要勒紧腰带、渡过难关,让公共食堂坚持下去!
格针岭的社员们在老队长的带动下,真是响应了上级的指示,公共食堂里依然能吃上饭,烟囱里天天还正常地往外冒着浓烟。社员们的意志并不消沉。
仓库的保管员告诉社员们,老队长真是“老谋深算”,叫俺不轻易开那两间大仓给外人看,说它是格针岭人春季的“救命丹”,这会儿该让大家知道了:去年秋季大部分劳力都去参加各种“大会战”了,老队长在家中带领老少、妇女等“剩余劳力”,除了进行正常秋收外,还动员他们摘山芋秧嫩头嫩叶、在菜园子里拣嫩萝卜樱子等等,晒成干菜,藏入队部大仓,并瞒着余赤红,又把那些大田里头遍地收拉下的烂山芋、霉山干复收了起来;又暗暗告诉饲养员把精猪料适当地减少,省些豆饼、花生饼暗暗藏进仓库;刚开春又把上级拔来的说是作为土地追肥用的橡子饼也没沤进大粪塘,“偷藏”进了仓库;还又把秋季上级从外地调来的几千斤的胡萝卜被余赤红弄掉进南沙溪扔了的说是本地社员吃不惯的东西,发动老年人从沟底捞出来,又切成了胡萝卜干子晒干,也“偷藏”进了队部大仓。这会儿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将霉山干沤泡几遍,把霉汁倒掉,加点玉米推成煎饼,人们吃得美味香甜;干菜泡开,搭粮配菜;胡萝卜干放些红辣椒,炒成稀罕的素菜;橡子饼、花生饼、豆饼放在了大锅的稀饭里,人们愈嚼愈香。
公共食堂的生活还能坚持下去,大家都暗暗称赞这个老队长有远见。食堂里除了烧一部分上级调拨来的煤炭,仍然是烧从山上山下砍筏来的林木和格针帐,再过几天,就得烧社员的园边和家前屋后的刺槐树和格针帐了。社员们在这方面和老队长一样,都暗暗发愁,这些东西烧完怎么办?
就在这同时,洪宜章的三个女儿家的生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大女儿文英的丈夫韦亮在公社里犯了错误,被罢了官,没收了财产;大儿子惠惠的供销社工作也被解除了,他只有到粮管所里当了装卸工。韦亮忍受不了这种尴尬,带着最小的孩子下了江南。二女儿凤英那村的食堂已散了伙,一家四口生活十分贫困,吃这顿没那顿。枣花跟婆婆商量,送些山玉芋和干煎饼给印才家解决临时困难。最困难的是兰英家,她的那个村子刚一过春节食堂就散伙了,到现在她那儿的绿树已看不到绿叶,只要能吃的树叶一露头就被社员掐了吃,野外的沟堤埂上岸边的野菜也被挖吃完了,甚至有些能吃的嫩草也都被社员用刀子挖起,割掉根放到少量的粮食里加工成煎饼充饥了。兰英一家几口饿得面黄肌瘦,皮包骨头。枣花知道后,经过婆婆的允许赶快把这几口接过来,在家过了一阶段,临回家时又送给她家一口袋熟山芋干,来解决燃眉之急。
这一年,洪如刚已在八里屯的中心小学校读五年级。在入学时,五年级是二个班,每班五十多名学生。刚到学期过半,一个班只有三十名学生了。班主任看着饿得面黄肌瘦的学生,心里实在难受,他跟体育老师讲,叫上体育课时,让学生少做剧烈运动。接着上级又下来政策把超龄学生和一部分老师下放农村,以减轻学校和社会困难。洪如刚的班主任老师,十分佩服洪如刚的学习和品德,他经常告诫洪如刚,一定要克服眼前的暂时困难,坚持把学习搞好。他是雎宁人,他的家乡更是生活困难,一想到家庭,实在没法在此地工作了,他只有主动申请回家,得到上级批准后,他在临离校时,语重心长地嘱咐洪如刚,说:“你没有被下放,很幸运,一定要克服眼前的困难,努力学习,以后有时间,我会写信经常鼓励你的。”临行时,还赠给洪如刚一个笔记本和几张风景照片,洪如刚确实没有钱买东西给他的班主任,心里十分难受,他恋恋不舍地目送他的班主任老师走出校门。那个老师向和他一起工作的老师和学生招手致意,洪如刚看着远去的班主任,低下头,偷偷地留下了眼泪。
不知不觉,格针岭又迎来了麦收时节,过去老百姓叫“麦口”,“麦口”真谓是道“关口”,长长的“春脖子”渡过了,人人都指望着小麦黄了熟了能吃上顿饱饭。可今年,使社员们太失望了,由于春旱,那不到半米高的小麦棵一割下来,拿到手里轻飘飘的,打下的麦粒儿都是瘦长干瘪的。老队长让社员们割下近二亩的麦子,赶快打下来,一半推成煎饼,一半打成麦糊子,做了一顿小麦稀糊饭,让社员们吃上一天的“好饭”。
最后的一顿饭刚吃完,老队长就语重心长地对还没走散的社员们讲了话,他说,“你们都记住这个特殊时期的公共食堂吧!吃了这顿饭只能是留作历史纪念了,现在的困难我实在的抗不住了,公共食堂再也不能坚持了,散伙吧!可这人心不能散,我一定和大伙共同抗拒这临时的困难!明天起,你们还得各支锅另打火,自己想个法儿做饭吃。大家挺一挺,困难一定会过去的!”
第二天,格针岭的公共食堂宣布解散,社员们又重新支起锅灶,开始了各家各户的自己做饭吃的生活。这时,不少的家庭既买不起锅灶,也没有粮食做饭,最后只有偷偷地到外地去逃荒要饭。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由于上级政策的变化,社员们自己可以开荒、拾边地,队里又分给社员们一些自留地和菜园。这样社员们有了一些小自由,他们不但可以自己调剂自家的生活,还可以把剩余的粮食和蔬菜拿到市场上去卖,换回些自家生活的必需品,农村又逐渐偿到了新的政策的温暖,可这政策不久就被否定了,连那些执行新政策的某些领导人也受到了批判。
洪宜章和枣花辛勤地劳作,陈氏在生活上精打细算,终究渡过了生活的难关。
洪如刚自觉地克服生活和学习上的一切困难,每天从格针岭到八里屯小学校步行往返十公里,在走读两年的高小的时间里,除去节假日、星期天,他大约步行走过八千多里的路程。洪如刚在读高小的这段时间里,经常利用午休时间和下午上完课放学回家之前的空隙,到大街的新华书店里去看书,如四大名著,古诗词和百家姓,字词典等等,他喜欢看但是无钱买,老辈给他的零花钱他舍不得花,中午饭带的煎饼他舍不得吃而又不让同学看见,却偷偷地拿到街上卖了,这些钱他一分也舍不得乱花,全部用来买书看了。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不断地吸取书中的精华,学习书中优秀的字词句,学习古今的文学知识,楷模书中古今英雄人物的品质。从而造就了他今后的人生,造就了他个人的修养。在这二年的四个学期中,他每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每学期的“操行等第”都被评为一个“甲”字,而不是“乙”、“丙”、“丁”。
不平凡的年代,艰苦的生活,使洪如刚不但增强了克服困难的决心,也磨练出了他那坚强的钢铁般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