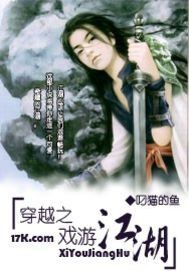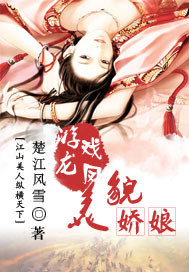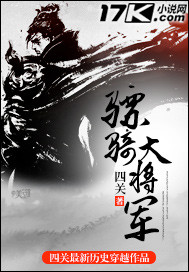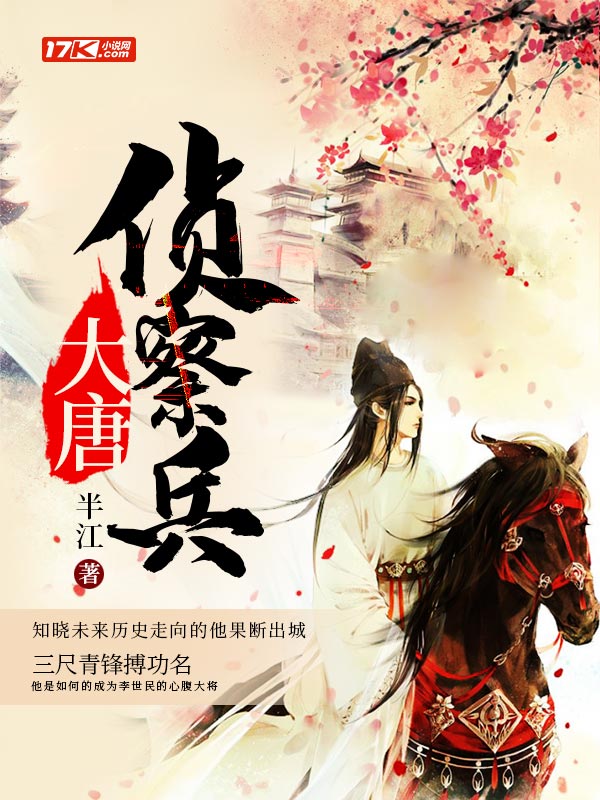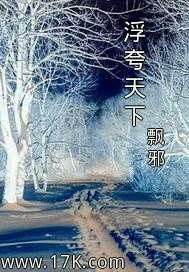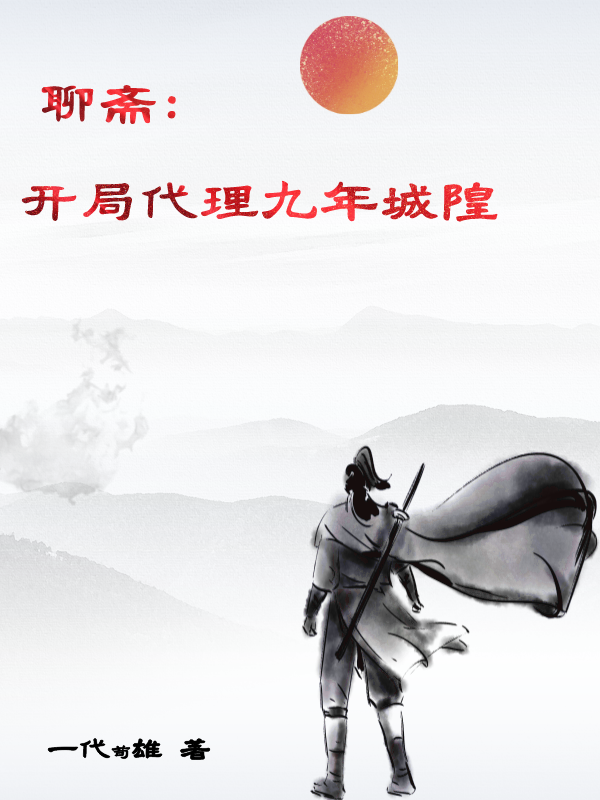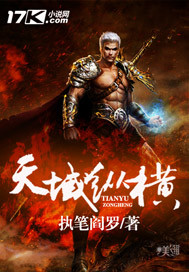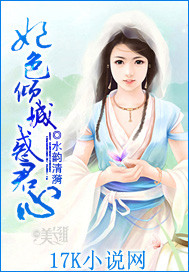何府,何焕正在给他爹何栗分析当前的形势。
“爹,你怎么还不去迎接来宣旨的钦差梁公公呢?这会儿正该是你露脸的机会啊,在梁公公面前混个脸熟也好啊,多认识一个对你有用的人,以后就多一条出路不是。”
何栗毕竟是个读书人出身,还是讲究那些阶层的差距,于是不屑道:“你爹我也是个有原则的人,并不是什么人都要去阿谀奉迎的。”
何焕知道他爹还没想透这其中的厉害关系:“爹,请问,那梁师成是何许人也?”
何栗不无鄙夷道:“一阉竖而已,何足挂齿?”
何焕也不立即反驳,只是拿起手中的折扇扇了扇,又来到那张紫檀茶几边上,将茶碗端起呡了口茶,清了清嗓子才道:“那梁师成本人确为一宦官而已,但是梁师成是官家的近臣,背后站的就是皇上,此番为何让梁师成来宣旨呢?你有没有想过这里边的那些弯弯绕绕?而且,众所周知他明里、暗里是支持大皇子赵桓的。”
“听你这么说,这里边还大有文章?你爹我走的是王丞相的路子,王丞相背后支持的是三皇子郓王赵揩,这些你都是知道的。”
何焕笑了笑,又继续品着西湖而来的明前龙井茶,看着茶碗中汤色绿、明、亮,品一品香气馥郁持久,滋味鲜醇,喝下几口不禁让他诗兴大发——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
何栗不明所以,用疑惑的眼神望着何焕,不知他又要做什么妖?
何焕却娓娓道来:“这世间只有两种人,一位名来二为利。俗话说的好,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诚然是三皇子帐下听用,但现在梁师成带来的圣旨是符合现如今我们的利益的,现如今为什么不能交好与他呢?多个朋友总归比多个敌人要好,况且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作为荆湖北路转运使,最高行政长官,由您亲自去迎接他梁师成,给足了他面子,届时他要是高兴向圣上美言几句,爹您指不定又要升官了!”
何栗听完儿子的分析,细思却有几分道理,思想上又随机松动了,其实在站队上,何栗向来没有什么远见,多半是听从他儿子何焕的意见。
一如当初何栗这个一甲进士,初入官场十来年不见起色,直到在儿子何焕十五岁那年,听从儿子的建议,投在当时正处于急速上升期的王黼门下,一路从下县从七品的小县知县一路升迁至现在的正五品的荆湖北路转运使,这才十年的时间不到,基本上这后十年每两年升上一级,不仅官职升迁了,而且还都是肥差,不仅荷包鼓了,而且是几辈子都花销不完的金银珠宝。
有的时候,何栗每每夜里想起来的时候,刚开始还会整夜整夜的睡不着,就怕有东窗事发的那一天。
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边升边腐,越腐越升的日子里,都没有出现任何的意外,到现在早已经习惯了,再也没有了当初贪腐时的那种胆战心惊。
听从何焕的建议,何栗赶忙利用手中的职权,调配了三艘顶级豪华的漕运船只,亲自前往江陵府远郊的龙安镇迎接梁师成去了。
何栗前脚刚走,盐铁司副使李甫的公子李昌宁,后脚就进入了何府后院,为的就是避免正面与何栗相见,何栗一向看不惯李昌宁放浪形骸之人,在何栗看来,这李昌宁简直有辱家门,还妄称出自书香门第之家,不过他老爹也确实是二甲进士出身。
李昌宁进入到何府后院之后,才发现这后院简直是太美了,真个是——
俯水枕石游鱼出听,临流枕石化蝶忘机。
当李昌宁沿着蜿蜒的廊道,信步闲游的观察着这一路的景色,廊桥两边翠竹倚阁,苍松青翠,碧草连芳,假山、流水、虫鸣鸟叫、鱼游,目及之处,处处皆为景。
李昌宁行至何府后院廊桥的尽头,又见石拱桥横跨在池塘之中,池中心两佳人正兴高采烈的泛舟采莲,玩耍嬉戏的不亦乐乎,一主一仆二人谁也不曾发现,不远处有一登徒子痴痴的远眺着,连步伐都迈不开了,要不是此时何府官家前来接应李昌宁,估计李昌宁都舍不得走。
赵构的江陵府衙内,作为在江陵为官多年的余邦光,还是有不少的官员买账的,往日余邦光对待下属也并不苛刻,所以辖区内地面上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下头那些官员还是会在第一时间向其通报。
余邦光刚刚收到消息,京城来传旨的钦差已经到了江陵府境内了,想劝劝赵构也去迎接迎接,现在是形势比人强,该地头的时候还是要低头,虽说余邦光确实是在为赵构着想,但赵构委实不敢苟同他的想法,赵构也是看在余去非的面子上,才让余邦光在这里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着,换做别的人早就轰出大门去了。
让一个堂堂皇子去迎合一个宦官,绝无这个可能,他赵构丢不起这个人,也绝无讨好梁师成心思的可能,这个余邦光的脑袋也不知脑洞是有多大?赵构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打断余邦光:“余大人,请勿在多言,你的好意呢,在下心领了,可绝不敢苟同,这就是我的态度。”
赵构端起茶杯,意思是要送客了。
小奴只好来到余邦光身边:“余大人,请吧,国公爷他自有他的打算。”
余邦光只能失望的摇摇头,形影单只的走出江陵府衙,却见府衙门前甚是吵闹,两衙役拦着一主一仆不让进。
其中一衙役不耐烦道:“你二人再不离开的话,胆敢擅闯衙门,小心让你们屁股开花,让你们知道我们的厉害。”
那主人模样的还没有开口说话,身旁的小厮倒是犯起了浑:“你们这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怎生瞎了你们的狗眼,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人是谁吗?就是蜀国公出来了也得笑脸相迎的请进去,你们倒好,还死命拦着不让进,有你们好果子吃的时候。”
一年轻点的衙役走到小厮面前:“哟嗬,你是癞蛤蟆哈气,好大的口气啊,你倒说说看有多大的老头,今天你要是不说个子丑寅卯来,看不把你投入牢房,吃几天牢饭,好让你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
那主人怕小厮泄露了身份,忙劝阻住小厮:“住嘴,这里哪里有你说话的份儿。”
余邦光刚好从内院里出来,在衙门口撞见了主仆二人,这主仆二人各骑一匹瘦马,身上除了一身包袱外,别无他物,又仔细端详着那主人,一身黑衣也掩饰不住他卓尔不群的英姿,只是可能因为连日赶路,头发略显得凌乱,但是可能又因为久居上位者,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子贵气,于是余邦光摒退他曾经的下属衙役:“你们暂且先退下,我来与他们聊几句。了解了解情况,这个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两个衙役拱手向余邦光施礼道:“余大人,这二人来历不明,硬是要进府衙,又无身份证明,万一是来行刺国公爷的,小的们可担待不起。”
余邦光摆出上官的身份:“怎么,本官的话你们也信不过。无妨的,本官以人格及项上乌纱作保还不行吗?”余邦光凭借着多年在官场上浸淫的识人经验,感觉这二人来头不小,尤其是那主人。
其实这二人真是乔装打扮南下的汪伯彦与其仆人汪从甲。
汪伯彦心想:方才听那衙役称呼其为余大人,再看模样,确实与余去非有几分相似,莫非、、、、、、
汪伯彦赶紧整了整衣衫,然后上前轻声询问:“这位大人,请问余去非是你何人?”
余邦光听闻他直呼出自己儿子的,更加坚定先前其判断的正确性,眼前这两位很有可能来自汴京城的,而且还认识自己儿子。
“正是犬子,你们认识他?”一脸疑惑的问道。
汪伯彦喜出望外:“岂止是认识那么简单,从前经常在康王府邸相见。”
余邦光心说,果然不出我所料。
“既然从前同系康王府旧人,请随本官进来,本官带你进去面见蜀国公。”
汪伯彦感激道:“那就有劳余大人了,今天幸亏是碰见了你,要不然近在咫尺都进不去这座府门了。还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正好快要到赵构书房的时候,小奴刚好从书房里边端完茶出来,碰见了余邦光,还纳闷呢,刚刚不是被自己送出府门外了吗,怎么这会儿功夫又折回来了。
小奴赶紧上前拉住余邦光:“余大人,这会儿你可千万不要进去,里头那位还在气头上呢,可不敢再去火上浇油了,咱家这也可是为了你好啊,谁叫咱家和余去非大人那是过命的交情呢。这要是旁人,我都懒得搭理。”
余邦光半开玩笑半戏谑:“我也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岂是那般不知轻重缓急之人。”
小奴没有注意到余邦光身后还站着两个人,一是因为二人连日来马不停蹄的赶路,要抢先圣旨到达前先期抵达江陵,也就顾不得外在的形象了;二是此刻小奴将注意力都放在了防范余邦光再次闯进书房去,没有来得及去关注其他的人。
还是汪伯彦主动自报家门,装作略带生气的口吻:“小奴总管,好大的官威,怎么连老夫我的声音你也听不出来了吗?”
说完将自己略显凌乱肮脏的头发向后捋了捋,才稍稍让小奴回过神来,小奴眼神跃过余邦光,这才仔细端详起那主仆二人,定睛一看后便大声的呼喊了起来,兴奋之情不溢言表:“国公爷,国公爷,汪大人来了,汪大人来了。”
小奴一面边叫着,边推开了书房的门将二人迎到了赵构的跟前。
赵构怎么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在这贬谪之地,还能见到自己的恩师,真是犹如黑夜里的星光,照亮了赵构前行的道路。余邦光为了给师生二人留下单独的空间,示意小奴与汪从甲退出书房,二人也是心领神会。
进来行事举步维艰,赵构一回想,自从京师一别已三月有余。
“先生为何打扮成这副模样,莫非受学生所牵连?”
赵构想来,如果是正常公干或者途经,断然不至于落魄成眼前这副脏兮兮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乞丐,定是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变故。
汪伯彦倒是丝毫不介意:“非也,非也,是为师主动私下来的,就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为师这次就是特意来劝阻你不可太过任性,私自处决王闳孚的。为师知道你的性格,从小就嫉恶如仇,爱憎分明,怕你铸成大错,才马不停蹄,星夜兼程而来。”
赵构哪曾料得到,这汪伯彦从汴京城千里迢迢的赶来,就是为了劝阻他不要斩杀王闳孚呢?
汪伯彦见赵构并没有当着自己的面松口,又继续好言相劝:“那王黼圣眷正隆,又与内侍杨戬,太尉高俅等人狼狈为奸,此时非但不能轻易得罪与他,还应该反过来讨好与他才是明智之举。为什么呢?俗话说得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那王黼这些年一直深受官家宠幸,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远的不说,近在你这荆湖北路转运使何栗就是王黼一手提拔起来的。”
赵构听罢只是冷冷的吐出几个字:“那又如何,难道就因为他王黼圣眷正隆,他的儿子犯法,罪证确凿也杀不得?不见得吧,恩师不要忘记了,这大宋的江山姓赵,不是姓王。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王闳孚只是一个权臣的儿子而已,莫非本国公秉公执法处斩他王闳孚后,那王黼还敢叫本国公爷给他儿子偿命不成?”
二人唇枪舌剑一番,谁也说服不了谁,谈话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
赵构最为一个千年之后的穿越者,在那个时代,穿越前身为国防生的他,从来也不会轻易的屈从于别人的意志。说话办事做人只遵从自己的内心的那杆秤。
况且赵构还想让宋徽宗赵佶这个便宜老爹将他贬谪到更远的南边去,以便远离朝堂,远离那段很快就会到来的耻辱岁月。
以退为进,才是最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