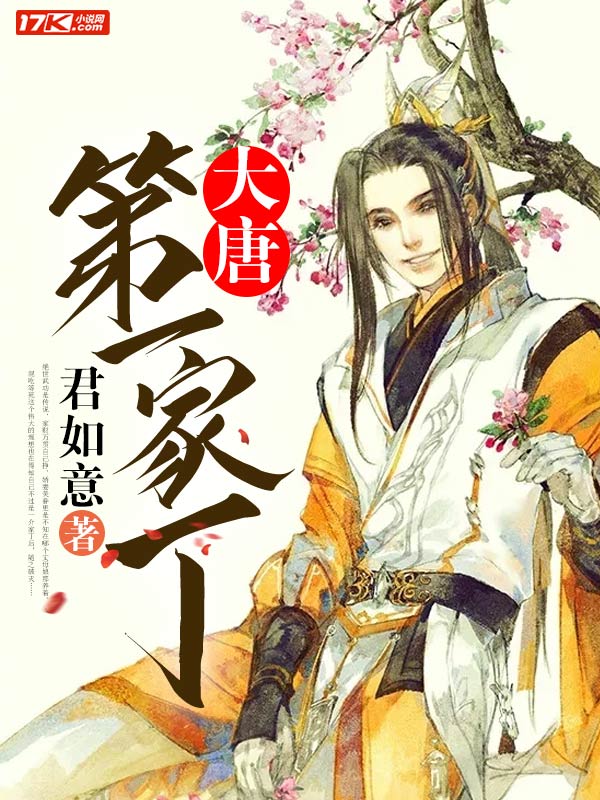人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赵构的第一把火还就准备拿王闳孚开刀,给他烧起来。
赵构可不是这么容易妥协之人,权臣、奸相之子那又当如何?试问,如果现在连一个权臣贪赃枉法的儿子都收拾不了,今后还怎么吊打金国、西夏和辽国,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却说何栗听从了他的儿子何焕的建议,带领着一众心腹下属,浩浩荡荡的分乘三条征调来的豪华漕运船只,要说这漕运船只是如何的豪华,且待细细说来——
船高约二十米,单从船体表面你看不出这船与其它的商船或者官船有什么特别之处,看上去与其它的漕运船只也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但是当你走进了看的时候,就会瞧出些端倪,那些真正用于运送粮食的漕船,窗户极少,一艘船只有一些押运人员及驾船的船工的少数住舱,会开几扇窗户,乘坐的舒适性极差,也为漕船中的粮食安全着想,避免因漕船窗户开的过多,而导致船舱内粮食湿气过重而受潮发霉。
何栗就任荆湖北路转运使之后,特意命人打造了三艘这样掩人耳目的船只,为的就是好用于接待上官,所以船舱里的内饰装饰材料考究的很,不仅船舱内的布局按照客舱建造,而且为了应付上头工部验收核查,还在布局上做了调整,即船内分成三大段六大块,右斜对称三段为粮仓,而左斜三段即为豪华客舱,不过平日里这三艘漕船一般不会用于运粮运物,只有京里头的上官来考核工作时会拉出来做做样子而已。
要说那客舱内,四壁施窗户,如同陆地上的房屋制式一样,上施栏循,彩绘华焕,采用帘幕增饰。船舱内里有桌椅床铺、茶水饮食,甚至僻有专门用于健身的舱室,以增加客人乘坐的舒适性,累了可以去健身,也可以随时打开窗户浏览沿河美丽的风光,好不惬意。
要说有宋一朝,出了军事力量不行,不抗揍以外,在经济、文化、科技以及生活上真真是封建王朝最美好的时代。
何栗乘坐的船头上,悬挂着“漕”字旗,旁边稍小的一面旗子上立着一面“何”字旗,三艘船依次一字排开前后行进着。
梁师成已经准备好动身前往江陵城了,一行人正在收拾行李,大家伙骂骂咧咧的,怨气甚重,嫌弃这里的地方官太不懂事了。
梁师成从汴京城这一路下来,各州各府各县哪个不是上赶着巴结他,心说:是,你赵构是天潢贵胄,你去亲自来拍个手下人来也行啊,竟然让咱家在此等候了一整天也见不着个人影,枉费邢尚书的一番好意了,哼,走着瞧,咱家今晚连夜进城。
就在梁师成腹诽之际,门外有一小黄门飞奔而来:“启禀梁公公,江边有三艘漕船向这边驶来。”
梁师成不以为然,以为只是普通的押运粮食的漕船而已。
梁师成斥责那小黄门:“大惊小怪,即是漕船,那肯定是运往京城的官粮了,快入夜了,他们估计也是来靠岸歇息的。”
那小黄门又说道:“可小的看你旗子上竖着一面‘何’字旗。”
梁师成这才在脑海中搜刮了一遍:是了,是了,此处已经是荆湖北路的地界了,转运使可不就是何栗。但这何栗乃是王黼的得意门生,咱家可是大皇子系的人,大皇子与三皇子那向来都是死对头。
就在梁师成陷入自我的思索之际,何栗已经派人递上了名帖,门外的小黄门王和荣领着来到了梁师成的面前。
“下官何栗拜见梁公公,近日有批粮食启运汴京城,这办皇差下官不敢怠慢半分,这才来的晚了些,实在是罪该万死,本应早些来迎接公公的,江陵府已经在府衙略备薄酒,还望梁公公赏脸。”
好一个一箭双雕之计,何栗之计要拍马屁,竟让赵构给他买单,这招不仅损而且毒辣,答应了他,这人情让何栗赚取了;不答应他,岂不是再次得罪了梁师成。
梁师成稍稍用他的那双犀利的眼神看了看何栗,竟然是两手空空而来,心忖:感情也是一个光说不练的假把式,好话软话说了一箩筐,不如来点实际的。像我们这种无根之人,除了爹妈,哦,不,就是爹妈也没有真金白银来得亲。
可转眼间,何栗一番嘘寒问暖之后,也从梁师成的言辞中听出些怠慢轻视之意,心里早就明白了几分,不管是哪个派系的人,真正不爱钱财的人那是极少的,反正他何栗至今为止是没有见识到过。
何栗起身站起来,从袖口中拿出一个事先早就准备好的,包装精美的小锦盒,双手托着,以示恭敬。
“梁公公,这是来自西洋番邦的极品人参,您这一路颠簸流离,甚为辛苦,正好用它来泡茶喝,起到提神醒脑之功效。”
梁师成这才又换上一副假笑脸:“哎呀,何大人(哎呀,你看,虚伪的连称呼都改变了,亲切的称之为何大人了),你我同朝为官,你这礼物太过贵重了,正所谓无功不受禄。”
确实,这个时候的西洋参极为含罕有,彼时东南沿海已有走私的南洋船只,或为海盗,亦或亦商亦盗者进行货物贸易,任何时候物以稀为贵,这西洋参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自然珍贵。
何栗也是个官场的老油子了,漂亮话张嘴就来:“哎,梁公公,您不远千里来到我们这荆湖北路,这点小心意不足挂齿,还望笑纳。”
“何大人,既然你这么客气懂事,那咱家可就却之不恭了,也不能拂了你的一番美意。”
江陵府却是没有半个人影出来迎接,无他,赵构没有开口,谁敢忤逆他,所谓县官不如现管,算是把梁师成得罪了。
如是汪伯彦、余邦光有心为赵构转圜,向梁师成示好,奈何本主不同意,他们也无计可施。
赵构其实也心中有自己的打算,不是不舍得花钱去讨好梁师成,实在是囊中羞涩,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
加之近来西北战事吃紧,心思多半都放在了宋夏边境战事上,加之何焕、李昌宁、武邦宁等在江陵府肆意哄抬米粮、盐等物价,专与赵构作对,想以此为要挟,向赵构施加压力,达到释放王闳孚的目的。
自从上任江陵府以来,诸事不顺,无他,只因自己还未能够掌握这江陵府的两股势力,一是官方的荆湖北路各地方官员,二是民间的帮会力量。
正当赵构在书房当中寻找破解之局时,门外小奴来禀报:“国公爷,门人来报,府外有一年轻女子推着一老者在门外求见,说是来帮您破解江陵府困局的。
还真是想什么来什么,赵构也是有点病急乱投医了,略微思索一番后立即道:“快快有请,请到大厅内叙话,上好茶侍候着。”
江陵蜀国公府大厅内,陈玉玲推着其父陈其坐在厅内,陈其倒是放得开,拿着案几上的花瓶欣赏了起来,倒是陈玉玲显得略微紧张,毕竟身份悬殊巨大。
为了掩饰其内心的紧张焦虑,陈玉玲开始岔开话题:“爹,你不是经常对女儿说,咱们这些在刀口上舔生活的人,不要与官府的人走得太近吗,今天怎么让女儿领着一定要来这蜀国公府呢?”
陈其很是慈祥的,面带着笑容,半正经半开玩笑道:“当然是为着我女儿你的终身幸福大事啊!”
未经人事的陈玉玲以为爹爹在取笑自己,虽然是自己的亲爹爹,也不免娇羞不已。
“爹爹,你又取笑女儿了。您不是一直想招大师哥为女婿的吗?怎的今日又有他说。”
陈其一听陈玉玲提起宫星君来,立即大声对她呵斥道:“今后少在我面前提起这孽障,欺师灭祖的东西,且让他再多蹦跶蹦跶,长则一年,短则三五月。”
陈玉玲从陈其的语气中已经听出来了,看来,爹爹已经对大师哥失望之极了,才会如此的口吐凶言了。
不到一盏茶的功夫,赵构领着余去非、小奴二人来到大厅,经由小奴引荐,双方算是正式有所接触了。
陈其不愧是个混江湖的老手了,是见过大世面,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以及岁月沧桑洗涤的,在赵构的面前,也是不卑不亢——
“见过蜀国公,请恕老朽不能下地参拜之罪,双腿多有不便,万望海涵!”
赵构见陈其坐在了轮椅上,想必是瘫痪了,自然是不太方便了。又一大把年纪了,心里面很是疑惑,这样一个身体残缺之人如何能够帮助自己破解江陵府目前的这一摊子困局,但是表面上赵构还是保持着对陈其的客气,和颜悦色道:“无妨,无妨!”
赵构落座正厅主位后,屁股还未坐稳,正要开口盘问对方,却被陈其抢先一步道,只见陈其转头示意陈玉玲将他坐的木制轮椅车往中间,往前挪点。
然后陈其拱手执礼:“蜀国公,请恕老朽无礼了,在商谈正事之前,有一事相托,还望万勿推辞,不然破解江陵困局之事请恕老朽无能为力了。”
威胁,这是明目张胆的威胁。
赵构此时心绪不宁,别说一件事情,就是两件、三件再多件事情也没有推辞的道理,连对陈其的称呼都恭敬了几分。
“老伯,你有什么何事相托,但说无妨。”
然而身旁的小奴却不干了,这样明目张胆的相要挟,这如何使得,万一是什么过分的要求,那不是今后要被眼前的父女两牵着鼻子走吗?
小奴愤慨的挺身而出:“你们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胆刁民,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公然的要挟国公爷,不知轻重的东西。来人,将这父女二人、、、、、、”话还没有说完,赵构示意小奴住嘴,并用眼睛狠狠的瞪了他一眼。
陈其倒是有宠辱不惊的定力,依旧如当初刚进入江陵府衙的时候保持着不卑不亢的态度。
待赵构这主仆二人闹腾一番言语之后,确认过不会再有波澜后才又开口道:“此事对国公爷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
说完,陈其将身旁的女儿陈玉玲拉到了自己跟前,正面对着赵构缓缓道:“老朽膝下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年方二八,未曾婚配。如若国公爷不嫌弃的话,入得国公府为奴为婢、为侍为妾,亦或做个暖床的填房丫头也是可以的,如此这般,老朽也算是了却了一桩身后事,才无后顾之忧,不知蜀国公意下如何?”
这番直白的话语,立时让身旁的陈玉玲娇羞不已,满脸通红。这未出闺阁的女儿家自是害羞,陈玉玲没有想到,自己的爹爹第一次与赵构见面,就当着她的面向人家提出那么直白的要求,要是对方不加思索的一口拒绝了怎么办,人家不要面子的吗?
再说,人家可是堂堂的蜀国公,这天下想要娶什么样的漂亮女子没有,自己这长相又不是倾国倾城,怎么能入得了蜀国公的法眼呢?
居中坐在主位的赵构也是被陈其的话惊的外焦里嫩的,与其说这是要挟,倒不如讲是投名状更为贴切。
赵构站在陈其的角度想想,也是这么回事。
二人素昧平生,别人凭什么要平白无故的帮助你,你以为是学雷锋做好事呢,到了陈其这个年龄的人,名与利早已经不是看得那么重要了。
赵构这才细细打量起眼前这个年方二八未经人事的花季少女来。
只见陈玉玲细长高挑的身段,浑身上下散发着青春少女的气息;神采飞扬的含情眼眸,顾盼摇曳,偶尔娇羞之时不经意间亦会流露出几分妩媚与妖娆;白嫩水灵的脸蛋上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红润小巧的樱桃小口微张,露出洁白的牙齿,亦别有番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