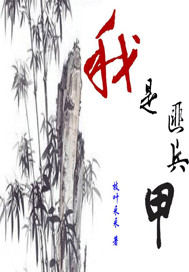康王府中现在已经是乱成一锅粥了,田春罗与姜醉媚两位年轻漂亮的夫人却没有像府中其他的仆人使役那样作鸟兽散,始终同赵构在一起,陪他坚守在府中,不离不弃,令他大为感动。
越是在这种紧要的关头,越不能慌了手脚,而是要静下心来冷静的思考。像现在这样被围困在府中,什么也做不了。
“不行,不能就这样坐在这里坐以待毙,得主动出击才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那些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自己的人,为了不让后世的悲剧不再重演”。
景王赵杞在第一时间得到赵构谋反的消息后,先是震惊,继而一眼就看穿了这是有人在恶意的重伤,而这个重伤是致命的,让他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恨自己不能帮上他的忙。苦思良久后:“李马,你且去点齐府中的兵马,连家丁、男仆人有一个算一个,把大家组织起来前去营救九弟。”
李马一听这就是欠思量了,这还了得,这样只会是适得其反,正好坐实了康王爷谋反的罪名,他立即应声跪下:“王爷,万万不可轻举妄动,您这样不仅救不了康王爷,反而会害了他。依小人之见,当务之急是要派人去接管北门,诱骗童二那厮交出北门的兵权和指挥权才是上策,这样或许还有转圜的余地。再让韩将军他们进城会同高太尉将情况禀明,否则当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个冤屈了。”
赵杞此刻救人心切,哪里会顾及到那么多,便听从了李马的建议:“行,那就一切按照你说的去办,你带兵前去北门,本王亲往太尉府见高俅这厮,他也该出来说两句公道话了,咱们分头行动。”
韦娇娇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儿子会犯上谋反作乱,这实在是有违常理,这当中一定有蹊跷之处。她哭哭啼啼的从她的寝宫当中一路哭着,看到到赵佶后,扑通一下就跪到了他的面前:“官家,官家,构儿一定是惨遭奸人陷害的,他才刚刚蒙圣恩,晋封亲王,官家您又亲自为他挑选了这么好的一桩婚事,我们母子二人感激都来不及,怎么会去谋反呢?一定是有人看见你这么恩宠我们母子,有人嫉妒了,纯心故意栽赃陷害,望官家明察秋毫,还我们母子一个清白。”
他愤怒的将手中奏章扔到了韦娇娇的面前:“贱人,你就不要再为你的那个逆子求情了,小心连你也一并捉拿问罪。”
大殿里除了赵佶响彻的暴怒声,就只有赵楷的心里乐开了花,他的第一步已经成功了。
赵佶一听到有人要威胁到自己的皇位,哪里还顾忌到什么父子情、夫妻情,此时的他全然没有了平日里的温文儒雅,只是一个心中只进了一头性情暴烈的狮子,什么人的话再也听不进去了。
被恐惧、愤怒包围着的赵佶已经来不及,也不想再去仔细的思考了,事情的合理与否,只是一心想着赶紧将叛乱镇压下去以平息事态,好让他再过他的安心日子,让皇位能够坐的更安稳些。
在他手足无措之际,高俅竟身着戎装,从殿外昂首阔步的走了进来,赵佶简直像是看见了大救星一样喜极而泣,不无感慨道:“关键时刻,还是朕的这些老臣们更靠得住。”这话是当着赵楷的面直说的,原以为这回捉拿九弟的头功非他莫属了,这会儿竟然半路杀出来个高俅,想必他一定是收到了什么风声,特意来搅他的局的,作为与本案有直接相关的利益者,不但不避嫌,还公开的跳出来要捉拿自己的同谋,这是想以退为进呢还是想来一招弃卒保車?跟我来这一招,是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的。
赵楷再一次俯首跪在崇政殿上:“父皇,您就安安心心端坐在这大殿之中,儿臣带领御林军前去将九弟亲自给你绑来这大殿之上交由您处置。”
高俅只知道外头发生了叛乱,却不知那人便是康王赵构,惊得他一身的冷汗,难怪方才景王来找他的时候言语多是闪烁其词,原来这背后还有这样的大文章。再一个联想到近日来自己与康王走得颇为亲近,不会让人抓住把柄吧?这个三大王素来心机重,又有夺太子位的野心,是个为达目的不折手段的狠角儿。
赵佶此时也从慌乱中稍微清醒了点,略为想了想:“还是与高太尉一同前往,务必将那逆子给完好无损的抓来,朕要亲自审问他!”韦娇娇一听,立即晕倒在了大殿之上,皇帝没有发话,在这个敏感的危机时刻,人人以自保为主,也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真是落难的凤凰不如鸡。
赵佶现在因为听到赵构谋反,对韦娇娇的态度也是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见到她就想到了谋反的赵构,便呵斥身边的人:“你们搭把手将这个贱妃打入冷宫,没有朕的旨意,任何人不得探视。”
邢博岩匆匆从兵部衙门赶回家,由于走的太急太快,一路上又火急火燎的,担心这事会诛连到他邢府。一回到府中就吩咐管家将她女儿叫来:“就说我有要事找她,事关邢府存亡的大事。”
管家从未见过邢博岩这么害怕过:“老爷,出什么事情了,侍候老爷二十来年从未见老爷您像今天这样?”
“先别问了,你马上就会知道了,先去吧小姐给我叫来。”语气中充满了焦虑与恐惧。
邢秉懿自从与赵明诚私下相会几次后,近日来心情也是大好,完全忘记了自己已经是一个身有婚约之人了。进得书房来却见爹爹满脸的惊恐之状,爹爹戎马一生,经历过大小战争近百场,到底是何事让他都愁眉苦脸呢?如果是朝中之事,爹爹也不会这么匆忙的将自己唤来?莫非又是在边关的二哥闯祸啦,需要她出面去求那个登徒浪子的王爷?
她走到了邢博岩的身边,轻声唤了声:“爹爹,究竟发生何事,让您这么忧虑?”
邢博岩才从走神当中回过神来:“来啦,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咱们家就要大祸临头了。”
头一次发现大嗓门的爹爹说话这么中气不足,看来事情发展的态势比她预想中的还要严重。
她从茶几上将茶壶拎了起来,给他续满。“爹爹,今晨出门的时候你不还是神采奕奕的吗,为何一回到家就换了副面容呢,究竟发生了何事?”
邢博岩哀叹一声:“都怪爹爹死要面子活受罪,邢府上下几百口人恐将大祸临头了哇,女儿。”说着说着,一介堂堂九尺男人竟然当着自己十五岁女儿的面嚎啕大哭了起来,听得她心里头真不是滋味,也跟着眼睛了噙着泪水,但就是强忍着不让它轻易的掉落下来。还安慰着他:“爹爹,天塌下来了,也不用太过于悲伤了。正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
邢博岩轻轻的擦拭掉眼中的泪水,略带歉意:“爹爹失态了,叫女儿见笑了。”
自己女儿怎么会取笑自己亲爱的父亲呢?但是身为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位从小在自己的儿女面前扮演着硬汉形象的爹爹,是全家人守护者的角色,是他们头顶上的一片天,脚底下宽阔的大地。
想想该怎么向她开口说才好呢?这一切的根由都只能怪自己当初太势力了,要不是当初自己总想着攀龙附凤,又怎么会惹上今日之祸;要是当初按照女儿的心思选心上人,赵明诚也会是一个不错的女婿,何况还是能亲上加亲的好事,可这会儿再来说这些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只可惜,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现在说什么也是多余的了。当他把赵构谋反之事告诉她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竟然是——不可能!不相信!绝不会!
她立即关切的询问,以至于用力的抓着邢博岩的胳膊,甚至把他弄疼了都还没有察觉出来他脸部扭曲的变化,几乎是用哭腔:“那他现在怎么了,被抓住了还是已经被、、、?”剩下的话她没敢说出口,只是用手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邢博岩为了宽慰她的心,轻声道:“那到倒还不至于,只是康王府现在已经被郓王爷包围了起来,不让任何人进出。估计等圣旨一到,他们就会立即冲进康王府去抓人了。”
邢秉懿喃喃自语:“不可能,不可能的,一定是背后有人在陷害他。没道理的,没理由的啊,儿子反老子,一定是他最近锋芒毕露了,触及到了某些人敏感的神经,他们害怕了,所以故意栽赃陷害与他。”
邢博岩从小就很疼爱这个女儿不是没有缘由的,他很是佩服女儿的见地:“这么说来,只要能找到背后那个栽赃陷害的幕后指使,就能替康王洗脱掉谋反的罪名了。”
虽然邢秉懿之前一直就特别的讨厌赵构,但是当她听闻他竟然身处这样的险境之时,心中竟然有丝丝的阵痛感传遍了她的全身,牵挂着他此时是否安然无恙,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这样的危急当中自己竟然是很在乎他的。
赵构与两位夫人及小奴在康王府中苦寻摆脱困境的对策,然而随着时间额流逝,他们在等待中蹉跎。
门口的守卫不让任何人进出,但是仍然阻挡不住邢秉懿前进的脚步,她努力的挣扎着:“让我进去,你们知道我爹是谁吗?兵部尚书,让你们的长官来见我。”那校尉用眼瞄了瞄她:“现在别人都唯恐避之不及,你倒好,却是在这里叫喊着要送上门去,是何道理?”
赵构听见门外吵闹的声音,径直朝门口而去,见是邢秉懿。眼下这种状况还是不要将她扯进来为好:“你们放开她,其实本王根本就不喜欢这个女人,太野蛮了,刚才你们也领教了吧。还一天到晚自以为是的,要不是当初父皇下旨,本王怎么会同意与这么一个野蛮刁钻的女子订立婚约呢?”
那校尉劝她道:“看见没有,邢小姐,别把你的热脸贴到别人的冷屁股上了,速速离开此是非之地,不然到时候将你以同谋抓起来送进大牢,你一个千金大小姐也不想去开封府的监狱走一趟吧?”
赵构只是希望她能够明白自己此时的苦心,并非存心要侮辱她的,只是想让她知难而退,远离这个是非之地。她在外头,如果还念情的话,至少还可以帮忙探听些消息,如果一起被抓进大牢了,岂不又是少了一个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