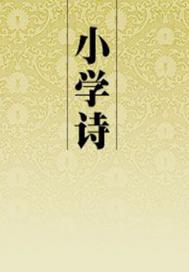我认识一条散漫多弯的河——拒马河。这河从源头开始,便盘旋于太行之中。它绕过山的阻拦,谢绝石的挽留,只是欢唱着向前。在浩瀚的鹅卵石滩、肥嫩的草地,它是一股股细流,只有当白沙和黄土为岸时,河水才收敛起来,变成齐腰深的艳蓝。
那年我在一个有白沙为岸的小村生活、写作,村里的老人给我讲了那个“河里没规矩”的故事。先前,每当夏日中午,村里的姑娘、媳妇便结伴到河中洗澡。她们边下河,边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脱净,高高地抛向身后的河岸。待到她们钻入齐腰深的河水时,自己就成了一个赤条条的自己。而这时,就在离她们不远之处,一群赤条条的男人也在享受着这水。这两群赤条条的女人和男人彼此总要招来些笑骂的,但那只是笑着的骂而已,一切都因了这个自古流传下来的“河里没规矩”的规矩。然而,是女人你就不必担心,说个“没规矩”你就会招来什么“不测”;是男人你也别以为,凭个“没规矩”你就能有什么“便宜”可占。在河里,男女间那个自己为自己定下的距离就是规矩,这规矩便成了那群“没规矩”的人们从精神到物质的享受依据。这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发生在那些处于半原始状态的山民中的一种现代文明,山民的半原始状态和这种现代文明一直延续到距今二十年前。可惜待到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问及那些哼着《潇洒走一回》、衣着打扮已明显朝着都市迈进的当地姑娘时,竟无一人知道这个离她们并不遥远的文明故事。你给他们讲,她们会把脸一扭,好像你的故事反倒是伤了她们的风化。这不能不说是发生在她们身上的悲剧。
我说的散文河,当然不是拒马河,却又觉得散文其实就是一条河。那么在这条散文河里,到底又有多少规矩?假如我是一个地道的散文家,这本是不在题下的一件事,可惜我并不是一个地道的散文家,所以便将计就计地把散文想成了一条河。在我想象的这条河里,自然也就没了规矩。在这条河里游着的男女,你和衣而卧或许并无人说你文明;你赤裸而立,顶多也只会招来几声笑骂,你还会把笑骂愉快地奉还给对方。反之,散文既是一条没规矩的河,河里自然也就有了那个自觉的规矩。伸腿下河的必得是散文吧?你实在不应该把一大堆不好归类的文字都扔进散文这条河里。那些裸着自己下河的女人连脱衣服都脱得有章有法,她们是边入水边脱衣,继而把衣服抛向岸边。于是她们不显山不显水地下了河,没有半点露“怯”之处。
章法之于文学,如果可作形式感解释,那么形式感就标榜着一篇散文独具的韵致和异常的气质。当然,问题还要牵扯到产生形式感的题材,于是我就想,散文这条河里的没规矩,或许应该指散文那形式感的自我标榜。
形式感不应只是描写技巧和作家对于零零星星的韵味的寻找。形式感是就一件作品的整体而言的。有位名叫奥尔班的奥地利画家说:形式感是你在作品中寻找的那种“联合体”。我常注意大散文家们对“联合体”的重视。朱自清和丘吉尔都深深懂得这个“联合体”的重要,于是他们在散文这条没规矩的河里找到了各自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