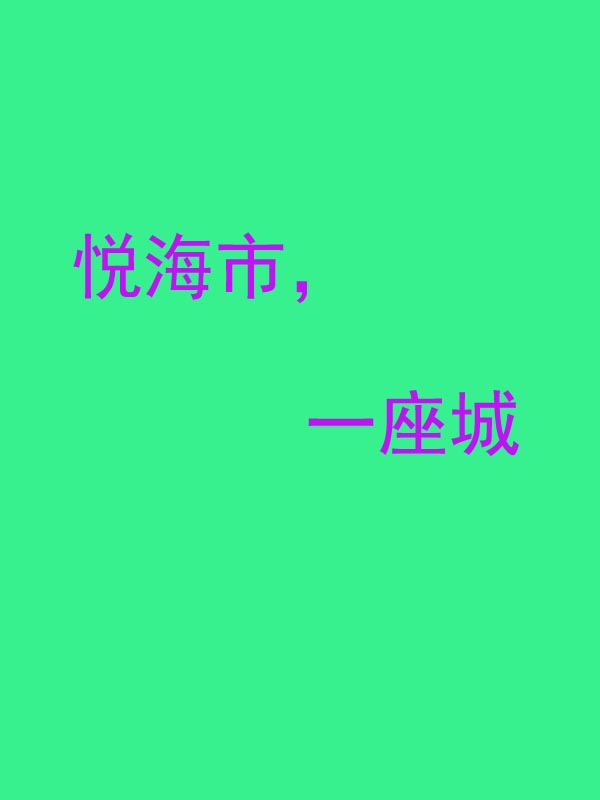山路清幽,又剩下青羽跟谢扶苏两个人,相依相随着回家了。从前种种事情,都像一个乱梦,梦怎么样都能做完,只有他们两个一块儿回去,这好像永远不会变。青羽小声叫:
“先生!”
“嗯?”
“真对不起,秦少爷说他们家里要找我麻烦,叫我躲一躲,后来我又送他离开,不知怎么的越走越远,闹出这么多麻烦来。”
“没事。”
“豆子剥出来放那里,不知有没有干掉呢。如果放汤不新鲜的话,我们煮笋干豆子好不好?”
“好。”
谢扶苏的回答,怎么总是这么干巴巴的啊?青羽叹口气:先生果然生气了吧?“对不起!”
“嗯?”
“先生要骂我,就请骂出来吧!不要再这个样子。”青羽眼里噙着泪水。
谢扶苏终于多说了几个字:“你怎么了?我没有要骂你啊。”
“可是先生这个样子,不是很生气很生气的样子吗?”青羽站住了,大声道,“所以请骂出来吧!”嗯,她虽然害怕被骂,但也比这么冷冷的僵着更好啊。
谢扶苏叹一口气,弯腰看她:“我没有生你的气。是在生自己的气。”
“呃?”——这次终于轮到青羽用一个字回答他了。
“因为没有考虑周到,留你一个人在家,害得你被拐走,还遇上了危险,我非常的生自己的气。所以一直在想:我应该怎么样改正。以后不能让你再遇险。”谢扶苏的口气好认真好认真。青羽“哦”了一声,心底慢慢的暖和起来,好像要化了一样,虽然有点儿不知所措,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配得上,不过……这应该是幸福的感觉吧?
路边有个小茶棚,谢扶苏对青羽道:“去歇歇再说。”青羽是稍稍有些累了,笑着答应,跟着谢扶苏进去,那看茶馆的展眼望见,笑嘻嘻就倒了两大碗凉茶奉上来:“桑叶甘草茶!谢先生,您老用着!这茶不用您的钱!前儿咱狗剩的急抽风多亏了您老咧!您老这又是出诊哪?”谢扶苏笑笑。看茶馆的觑着青羽道:“这位姑娘这是接了谢先生出诊、送他回去?哎,要说谢先生这医术、这人品,是没得说!该当送,该当送!”笑得那个挤眉弄眼儿。
青羽怪不好意思的。谢扶苏已道:“这是我新收的徒儿。”
看茶馆的“哟”了一声:“怪道的!先生房里是缺个人——可是谢先生,这般人品的姑娘,您忍心带人家远远近近的跑?”说着,越发的挤眉弄眼。
青羽羞得埋下头去,谢扶苏正色道:“这是引秋坊的姑娘,从前的老朋友托我照顾一段时间的。不好胡说!老哥,顽笑归顽笑,小姑娘名声要紧的。”
看茶馆的忙点头,冲青羽哈个腰:“瞧我这张嘴,姑娘您别望心里去!”上下再看她一眼,啧啧赞道,“真是那地方的姑娘,瞧这通身的气派儿!姑娘,您怎么又来学郎中了?”说着,向谢扶苏打个躬,“人家毕竟是小姑娘家,先生您勿怪!”
原来栖州既以扇业为民生大业,扇行的地位较高,尤其是引秋坊,嘉老板一个孤身女子清清白白做下江山,尤其叫人钦佩。青羽看起来是这么柔柔弱弱一个姑娘家,在嘉老板手下制扇那是再妥贴不过,出来跟个走方郎中做徒弟,那自然是委屈了。所以看茶馆的奇怪着动问一声,又怕得罪谢扶苏,故告个罪儿。
青羽已红着脸答道:“我笨,做不来扇子,跟在坊主身边没什么用……其实,医术,我也学不太来。”把自己之笨再承认一次,愧不可当。
“不。她很聪明。”谢扶苏在旁边淡淡道。
青羽看了先生一眼,不知道这是替她打圆场、还是聊表鼓励。看茶馆的却当真了,呵呵笑道:“这么水葱样的姑娘家,当然是聪明的!”说着,又有新的客人来,他大毛巾子一甩,上去招呼。青羽这边总算清静下来,松口气,喝茶不提。
他们两个不说话,旁边桌上客人说的话传过来,就尤其听得通切。几句话一入耳,青羽眼睛瞪圆了,看了谢扶苏一眼。你道怎么?原来那几个客人说的是:
“你听说过没?横行的逆天大盗,前儿吃了瘪啦!”
“嘿!可不敢冒犯。得叫逆天王。”
“是,是……这逆天王啊,前儿听说跟一个人打,愣没讨上好。”
“哟?道上什么时候出过这么个英雄?”
“就是没人知道啊!可惜不是比武,没放话,所以道上晓事的谁也没赶上去参观!就一位过路的远远见了,说打得那叫个漂亮啊!对手好像先耗过真力、后劲不继,逆天王还是没能讨上好去,因怀里抱着个姑娘,就拿那姑娘挡着对手招式!对手顾忌着玉瓶儿,才叫他挟着姑娘从容而遁了。听说呀,他们好像在争这个姑娘!”
“那位英雄是谁?那姑娘又是谁?”
“天晓得!这不就是没认出来嘛。说是穿身再普通不过的青布袍子,飘飘然有神仙之姿。那姑娘啊,一定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要不怎么能叫两个高手抢?要说他们的身份……来来,耳朵凑过来!——八成是宫里的!”
“吓?”
“逆天王一直跟官家过不去,官府不是出告示捉拿了嘛?就前几天,他们又劫了少城主心爱的狗大将,半城官兵出去捉拿他们了!所以呀,你说,那姑娘跟王宫有没有关系?突骨冒出来的英雄美女,不是宫里来,是打哪来?”
“……”
他们说得热闹。青羽自听到什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就把脸臊得要埋进桌子里面去。谢扶苏笑笑,叫她:“喝茶。再赶一会儿路就到家了。”
青羽当他没注意隔壁桌的说话,面红耳赤,不知该怎么说。谢扶苏将碗中茶饮完,道:“风吹过去,波纹越扩越大、可是水还是水。”
青羽细嚼此语,大有禅意,方知谢扶苏什么都听见了,只没往心里去,顿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仿佛与清风相处,心下也清了,人家说东说西,都可以不去理。只是欢欢喜喜的、饮干茶,与他走掉,身边是那么满满溢溢平凡又幸福的日子。看茶馆的来收碗,看见碗下的钱,叫一声:“嘿,谢先生,您怎么这样!”谢扶苏回头,向他微笑着抱抱拳,看茶馆的满口埋怨:“谢先生哪!您哪!唉!”可眼里都是笑。他身后,聊逆天王事件的,从一桌两个客人,发展到一堆人。栖州由扇业带动商业,来往行脚奔波的大小商人很多,旅途寂寞了,黑白两道、英雄美女,是最好的消遣,聊完了,上路,可以将这个话题跟新的落脚点、新的人们去聊,朋友就是这样越聊越多,传奇也就是这样越扩越远。青羽发现自己一点儿都不在乎自己被他们说成什么样子,只要先生的身影,还是踏踏实实的在面前;只要回家的路,在脚下一点点变短。
——那时候,青羽一点儿也不知道,她又会遇上一件事,给许多人的人生**很大转折。
事情的发生也算有点征兆:乌鸦在树枝上叫、白色的灵旗飘起来、还有哭声传出,无论怎么看都像在办丧事的样子。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丧家不吉利,会绕路而过。但谢扶苏跟青羽都不是那种庸俗的人,该怎么走怎么走。谢扶苏经过时,很肃穆的静立致意,青羽也跟着静立,向这个不相识的人家致以礼貌的哀悼,然后就可以上路了,可是——
我们主角,总难免经历几个“可是”。
灵柩正好抬出来,大约是暴疾而亡,而且这家人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所以没有用多好的寿材,只是两层漆的薄板。
丧家的人有十几个,包括两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三个哭灵像唱歌一样的女人、四个大大小小的孩子,还有——呃,一个巨人。
这个巨人趴在棺材上,像趴在一个小火柴盒上似的,哭得撕心裂肺,忽然 “咚”的一声,跌倒在地,巨大的身躯溅起一蓬尘土。
老婆婆和三个女人顿时尖声大叫:“爹啊!你怎么把四伢子带走呀!已经有三个儿子陪你,你怎么能把四伢子也带走啊!!”
青羽当时就觉得后背有冷汗流下来。
谢扶苏皱皱眉头,一言不发的过去,摸了摸巨人的额头,把了把他的脉搏,取面部、后颈、虎口三处的穴位,加以揉按,一边皱眉看了看周围,道:“拿个什么东西帮他挡挡阳光。取湿毛巾来。”
原来这人是伤心过度、疲倦脱水、加以太阳一照,故晕厥的。他这么大身坯,不是轻易移得进屋里,谢扶苏只能采用“山不来就我,我去就山”的法子,叫人搬东西到这里。
老婆子推了孩子们一把:“去!”孩子们啪哒啪哒跑进屋中。而女人们就掏了帕子去附近的井里蘸水。须臾,湿帕子搭上了巨人头——三块湿帕,刚够遮他额头——而孩子们也跑出来了。
青羽看到孩子们手里的东西,几乎要骇笑:那是一把巨大的蒲扇!
一个老婆子骂起来:“不拿伞,拿扇子干么?昏了头!”
顶小的两个小孩子一个翻白眼、一个挠头,最大的孩子低头剥指甲,只有第二大的孩子朗朗声道:“伞很贵,要省着用的!再说,我们的伞收起了,拿着费事,还不如拿四叔的扇子快。再再说,四叔的扇子不比我们的伞大?”
青羽看着那把扇子,竹条的骨架,大蒲叶编成的扇面,虽然粗拙一点,制法也算有纹有理,只不知怎么能做得这么大的,果然跟个大伞面儿不差什么,倒配这个巨人。
这把扇子遮定,谢扶苏悉心替巨人料理、推拿,不移时,巨人喉咙里“格”发出声音,翻了个身,手也随之抬起来,要打上青羽衣角。青羽呆呆的不知闪避,谢扶苏皱眉,风一样把她拉开。巨人的手就搭在了棺材上。这一下可是热闹。
原来他刚刚哭灵时,虽然也是“抚棺而哭”,但知道自己身躯太沉重,只是躬着腰,没有真的把重量压在上面。而此刻手一挥,完全打在棺材上。第二个孩子叹口气,很冷静的闭上眼睛,最大的孩子跟第三个孩子有样学样、也跟着闭上了,唯有最小的孩子好奇心重、眼睛咕噜噜盯着,便见棺材发出不堪重负的叹息、散了架,里面的老头儿滚出来。
离老头最近的女人眼睛向天上一翻、就吓晕了过去,另一个女人抱着她唤:“大姐!大姐!”而最小的孩子“哇”哭了出来,扎进第三个女人怀里:“妈!”两个婆子嘴里只管念叨:“造孽!天雷劈的!打折的棺材果然用不得!”
谢扶苏有些哭笑不得,只能再过去看那晕厥的女人情况如何。青羽跟他走,经过那老头,他忽然直挺挺的坐起来,手一伸,抓住她的手:“作坊、作坊,交给你了!”
所有人都傻了。青羽眼睛瞪大一点,看看自己的手腕,看看他。
老头儿眼神空洞,重复两个字:“作坊!”
青羽本能的点点头:“哦。”
老头儿长长吐出一口气,再倒下去,这一次好像真的死了,唇边还带着放心的微笑。巨人到现在才真正清醒过来了:“刚刚爹在说话?”青羽又看看自己的手腕,眼睛一闭,晕厥。在她倒到地上之前,谢扶苏将她扶在了怀里。
他该拿她怎么办呢?谢扶苏看着青羽,想。
他想保护她,希望她一生一世平平安安,不要遇到任何危险与惊扰,可她这个人,简直像有“找麻烦”的体质似的,哪怕闭门家中坐、都能祸从天上来,她倒不是故意找事,可是一步步行来,离家出走、小罗刹和逆天王、甚至炸尸,什么都会碰上,真叫人防不胜防。
老头的尸体,谢扶苏已经检验过了:天生心脉畸形,不久前厥死,家人把他收进棺材,不料他没死透,从棺材中滚出来时,心口的气透了过来,所以还能说出话,说完后,不堪重负的血脉真正爆裂,于是人去了。谢扶苏慎重的保证他不会再“炸尸”,这才让丧家重新装殓。
“装什么殓?哪还有钱给他买棺材!”两个老婆子一起吐唾沫,“家里剩那么多扇子和竹皮,把他捆一捆埋了吧!”
“娘!哪能这样对爹!”巨人一声惨哭,不知是对哪个老婆子叫的,几乎要震聋人的耳朵。
这时候,大家都已进屋了。青羽安顿在半破的竹榻上,谢扶苏脱下自己的外衣给她盖着,一边看看屋内:都是成品、半成品的竹骨蒲面扇,还有大堆原材料。这大约是个濒临倒闭的扇作坊。
“这样对他又咋啦?”两个老婆子一个鼻孔出气,“这老鬼把三个儿子先拖下去给他垫背!早晓得他这个鬼身子骨,生一个儿子寿夭一个,走了活该!叫大儿二儿三儿在地下揪着他问,他干么要把瘟病传给他儿子!”
“娘……刚刚大夫说,爹不是瘟病啊?”巨人怯声怯气道,但嗓门还是太大,震得人耳朵嗡嗡的。
青羽在此刻悠悠醒转,正听到后几个字,惶惑问谢扶苏:“瘟病?”眼眸黑而湿润,像小鸟。谢扶苏摸了摸她的头发:“不是的。遗传的问题。你等我给他们诊断。”
原来这老人的心脉畸形,老是气喘,被家里人当作染了什么病。这心脉的问题遗传给了三个儿子,因为畸形不太严重,所以儿子们不至于童年夭折,但成年之后,体力活加重,身体由盛而哀,遇上什么特殊心情波动时,就发作出来。这三个儿子,有的死在得知妻子怀孕的惊喜中、有的死在干活时,都走在爹的前面,比起来,老人还算是活得最长的。
那个巨人是老人第四子,名唤铁生,那四个小孩,分别叫大宝、二宝、三宝、四宝,则是铁生三个哥哥留下的遗孤,谢扶苏将他们一一诊断,幸而血脉五脏都算正常,只是第二孩子火旺气虚一些、三孩子脾胃弱些、其他没什么大碍。
他这般一一诊完,女人们没口价念佛,道是“皇天菩萨来救世了”。老婆子们念一声佛、吐一口唾沫。铁生难受道:“娘,既然我们没事,何苦还要骂爹。”老婆子一个翻白眼:“他已经造够孽了!”另一个咬牙切齿:“钱没赚到钱。留下这个破家。骂他怎的!”
青羽见满室这些制扇用品,倒心生亲近,想:那位老先生也是个制扇的老手艺人罢,怎的家里变得这般破败?便开口问道:“请问,我们栖州,扇行不是挺红火的,怎的这儿做的扇子像是有些冷落?”
老婆子恨道:“还不是这个死老头!本来做几把破蒲扇卖卖么蛮好的,他去学什么手艺,回来换竹子骨!说竹子高档!买蒲扇的谁要加个钱买扇骨啊?正经做折扇团扇他又不会。不亏本才怪!”
原来,再繁盛的地界,也有生意做不下去的人家呵。“所以老先生才这么担心作坊吗?”青羽轻声道,眼睛里又有泪水泛出来。
“呃……”谢扶苏盯着青羽,产生了很不好的预感。不要啊!不会又揽事上身了吧。
“老先生临走的时候,把作坊托给了我。”青羽坚毅道,“那么,先生,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撑下去!”
“呃……”
青羽第一个反应是找坊主帮忙。
坊主白手起家建起引秋坊,又照顾了她一生,要重振蒲扇坊,找坊主帮忙,岂不是理所当然?但是谢扶苏不同意。
“不要再去找她。”他道。
“为什么?”青羽茫然眨眼。
谢扶苏只能叹一口气、又叹一口气。
不,不可以说理由、不可以说担心——怎样对这个孩子说,她奉若神明的坊主,其实跟他有宿怨?那徒增青羽的烦恼罢了!他真希望当初那何老头儿坐起来时,他狠狠心发掌在第一时间把老头儿劈死,别叫他说什么临终遗言,那世界就清静了!
“因为——至少——你看,我有其他法子帮他们。”他只能这样说,“我的行医所得应该也够他们吃饭了。”实在不行,他还能重操旧业、劫富济贫,不是吗?
“先生,何老先生托的是作坊,只有把作坊救活,才能抚慰他在天之灵吧?”青羽紧蹙双眉,“而且,全靠你,你会太辛苦。”
“我不会。”谢扶苏咕噜。
“——而且人总要自食其力、自己有一份家业,才会比较安心吧?”青羽担心的把手放在他手心里。“先生,还有什么问题吗?”
她的手很小,而且也做不了什么事,但,一直在努力的想帮忙别人。她是这么愚蠢而温柔的女孩子。
“有……什么问题吗?”二宝也担心的把脑袋伸出来,像只脖子长长的乌龟。这小子刚刚缩在桌子下面睡觉,一听神仙姐姐和神仙大叔有问题,梦里都吓得醒过来。
“没有。”谢扶苏拍了拍青羽的肩:“你去吧。”
虽然仍有点怀疑,觉得先生瞒了她什么事,青羽到底回了引秋坊。
这是她生活了十二年的地方。从记事起,青羽跟着嘉,那时还没引秋坊呢,嘉身体不好,为了两人生计,仍然强撑着做扇子,终于有一天,握着一把素扇,在窗前对着月光慢慢旋转。
小小的青羽也知道眼前一亮。
如果说嘉以前做的扇子是制作良好的商品,那这一把,就是艺术品。它有了气韵。
“这一把扇子,叫苏铁。”嘉将它挡在眼眸与月亮之间,这样静静说。月影落在她眼睛上,幽深如前世的孽。扇光如雪。小青语不敢言语。
就用这把扇子,嘉一举夺得宝扇会的第三名,卖了它后,价银建了引秋坊,生意一步步做到今天。引秋坊栽下的竹子长到手臂那么粗时,青羽听见行脚商人谈起一种植物,叫苏铁,那是他们从海外贩过来,要卖给达官贵人的。青羽触动心事,奔回去问坊主:“苏铁这种植物,坊主养过吗?青羽好像听您提起过呢!好像很重要。”
“有这种事?胡说,你记错了。”嘉不动声色。
真的是这样?青羽左手握住右手,想了很久。童年的记忆模糊在迷雾中。她道歉:“我记错了,对不起,坊主。”
那一天,青羽知道了苏铁是一种喜光、喜温暖的植物,生长缓慢,叶片柔韧而美丽。那一天,她统共忘记苏铁与坊主有什么联系。
在腰门外的厚厚青苔上,青羽轻轻跺了跺脚。
只有引秋坊有这么厚实的青苔,只有引秋坊的坊主敢命令说:“给我建一个院子,不许种花。一两根槐树、七八根梧桐、半角青竹。叶子掉下来时,不要扫完,留它几片。”
这个命令下达时,园丁都很挠头;这个园子建造时,工人们都很困惑;这个园子刚建成后,看到的人都窃窃私语;这个园子彻底养成后,多少文人雅士都借着买扇子由头,没黑没白往这里钻,就为看一眼园景,直到有人借着醉意在墙上题诗:细挽秋声浅映墙,天然墨意写文章;如何修得眠于此,美景美人两益彰。
嘉看了看,也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冷冷笑了笑:“什么诌断了气的,白污我一堵墙,刮去了,重涂一次,今后这里不许人进来了。”
这是气话,她自己是人,她自己总要住的。但从这句话后,除非经通报、得嘉特别首肯的人,果然再没进过园子。此刻青羽在青苔上一跺脚,看门的听见了,探出头来看,立刻笑得满脸花开:“青羽!你这丫头怎么跑回来了。”是乌大娘。
青羽每次见到乌大娘,总觉自己又回到小小的、还梳着丫角麻烦她照顾的年纪,有点畏缩、心里又特别的暖和:“是我。大娘——”
一句话没完,就听院里有人急扯白脸道:“坊主,我是为你好!你真的要小心!”
竟是男人的声口,总有四五十岁了,不甚悦耳,听起来且有点熟悉。
青羽一看,见着那竟是秦歌的父亲,秦家商号秦老板。他在栖城生意做得这么大,难免跟引秋坊有来往,所以青羽见过,却从没见他出现在这院子里。
他能生出秦歌,五官总也不太差,但再帅的帅哥,上了四五十年纪、套上四五十斤的脂肪,那就基本只能往猪圈里蹲着了,哪怕套上金光闪闪的员外服、熏上一身铜香……不不,猪还是猪。嘉怎会让他进院子?
青羽只怕他是硬闯来的,忙一步跨进去,要替坊主撑腰。嘉脸上倒没什么特别的神情,看到青羽,点点头,示意她站着,边淡淡对秦老板道:“妾身知道了。谢过您。”
“坊主,那李鬼可是不得了,仿的扇子比真珠还真!城主说要揪出他的狐狸尾巴围剿,到现在也不知怎么样。大家的生意难免有些影响,坊主要是有什么想帮忙的,说一声,我秦某愿肝脑涂地效劳!”秦老板表忠心。
“我的扇子还真不怕人仿。”嘉淡淡道。秦老板灰心丧意要退下,她却又回眸向他,转了口气,“难得秦老板想着小坊,妾身心里领您的情。大娘,请秦老板坐到厅里喝口茶。”目光落在秦老板身上,笑了一笑,媚如春花开放,光彩流动。
秦老板登时脑壳上“轰”了一声,骨头酥麻麻从后颈骨一路麻到尾巴骨,头翘尾翘,不知今夕何夕。
他跟乌大娘下去了,青羽张口结舌的,但此刻才叫得出一声:“坊主。”
“你回去看了扇子了?”嘉拿小手指搔着头,张口就问这么一句。
她许多动作其实根本粗俗,毫无教养、不管不顾的,但就是美。再怎么俗气的动作、古怪的行止,搁在她身上都应该似的,所谓风姿。
青羽被她问慒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是关系着赌约期限的那把扇子,惶惑摇头:“对不起,还没有去看……”
“你遇着什么难办的大事了,指望我能帮上你的忙?”嘉目光真毒,往青羽上下一打量,准准猜中。
青羽“卟嗵”跪下去:“这件事只有坊主才能帮上忙了。”便把来龙去脉说一遍,才说了两句,嘉打个呵欠,往树干上倚,青羽晓得她身子骨不好、沾不得冷湿,自觉奔进屋里把椅上、榻上常年散放的那些小枕头拿了个出来,给她垫着坐了,方继续说下去,直到说完,嘉又打了个呵欠:“是我变笨了、还是你变聪明了?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
“坊主!”青羽着急。
“一个乡下的小作坊要倒闭,”嘉打断她,“那又关我什么事?若说他们生意不好,又不是我挤的。便是我挤的,我也不在乎。若说你要替他们找份工,我这里是有门槛的,总不能痴肥呆瘦疤疤麻麻都塞进来,当是什么?难民营?我一个商人照顾了难民,平白养着一伙儿官吏是做什么的?谁有那兴趣越俎代疱,找谁去!总之不沾我这里分毫。”
“坊主!”青羽焦灼,“我知道您好厉害,所以想请您帮忙想想办法看,怎样能帮他们站起来。”
“世道如棋、商道如镜。他们只要够有能耐,当然能站起来。帮要怎么帮?当初是谁帮我,我才站住的?”嘉摇头,“我原想你有了进步、可以好好**你试试,现在看来,错了,你还是糊涂着。”拂袖,“走吧。”
“坊主……”青羽像飘在风雨中的草梗,只有一棵大树能作依靠,但这棵大树都离她而去,她惶然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最讨厌求人帮忙的。比最讨厌还讨厌,就是为了别人求人帮忙的。有能耐,自己的腿走路、自己的手做事、自己的担子自己扛;没能耐,找个地方清清净净去死,麻烦别人干什么?你有什么权利麻烦别人?”嘉冷冷走开,却又回头笑一笑,“再说,你自己能利用的地方还没有用尽,不是吗?”
青羽跪在地上,觉不出膝盖疼。
坊主不会乱说话。她自己能做的地方,还有什么是没做到的吗?如果没有做到,就跑过来乱求救,难怪坊主会生气了。
可,到底,什么是她没做的呢?
“你在这儿!”猫一样的轻捷,一个人把她拉起来,“你跪在这儿作什么啦!”
青羽抬头,看见依依。
她瘦了些,眼睛比从前睁得更大,像是受惊的样子,虽然动人,但也没得叫人心里发毛。
“你怎么过来了呢?有什么事?是不是求坊主帮忙?”她嘴里不断问着,眼神不时向左右瞟,好像在提防着什么。青羽结结巴巴把事情说完,她目光的准星总算定在青羽脸上,好好看了她一眼:“你这个人啊……”贴到她脸边,飞快的耳语道,“记得我给你的东西、说的话。”把她一推,提高声音,“难怪你惹坊主生气了。走吧走吧!”
青羽迷糊着,脚不沾地给推了出来。
外面,一袭青衫,青得像雨水刚洗过的天空。安安静静的等在那里,好像一场地老天荒。
推人出来的、跟等人的,刹那间目光碰了碰,然后推人的关门回去,等人的微欠身:“你出来了。”
他对她总是客气,像是礼貌、又像是把自己定位在侍卫这一类身份,比谁都亲近、比谁都疏离。青羽手躲进袖子里,摸到光滑的埚,喉头作哽:“先生。”
“刚刚送你出来的女孩子,好像叫依依?”谢扶苏道。
根本不是“好像”。他注意她那么久,她身边的人,他都知道。
“是。”青羽不明所以的点着头,眼神清澈无邪。她什么都不懂。
“她好像有点事?”谢扶苏问。该毒的时候,他眼神比嘉还毒。但问话时,他比嘉客气。
于是青羽也就很糊涂的说:“没有啊。她就是跟我打个招呼,然后,她有送过我一个扇坠,要我记得——哎那个扇坠,还有我当时做的那把扇子,都还放在家里呢!我要去看一下。”
听到她说“家里”,谢扶苏嘴角不自觉上扬三分,听到“要去看一下”,又滑下来。她要撕扇那场面,他至今记忆犹新,听到她要去还要去看那玩艺儿,难免有些不快:“好好的看它干什么?”
“坊主说要看的,也许那扇子有了什么变化?总要看它一下。”青羽细声细气解释。
“不要看了。”谢扶苏总觉得看了没好事。
“为什么?”青羽继续张着纯洁的眸子好问不倦。
“我……”谢扶苏还是只能把头埋下去,“我送你回去看好了……”
天生万物,一物克一物。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他就一路被克到今天。可怜,当年一剑逍遥、快意江湖的他啊,他怎么就到了今天……
几天没回家,井台上落了些灰,丝瓜老了很多,晃晃悠悠在架子上打秋千,有几盆药草稍微打蔫儿了,母鸡光凭自己草堆里刨吃的,满足不了胃口,咕咕咕拍翅膀跑到主人跟前。青羽口里念着:“马上就给你加餐了。”一边先急着把扇子与扇坠找出来。
那把扇子一露面,她像被大砖劈头打到,闷疼,一时作不得声。
难看的黄斑生了满扇。连日湿雾,又未被好好保养,扇子已经丑若出天花破相的妇人。
“天气不好,我也没有放好它,不是你的错。”谢扶苏努力安慰她。
“不是的,是我没有处理好扇面。”青羽喃喃,“就连扇骨,也是因为扇坊的人先处理好了,不是我的功劳。一个真正制扇的人,怎么可能连这点都没做好,明知使用的环境潮湿,却做出放几日就会出黄斑的扇子?这是我的错。”将扇子反复翻看片刻,又醒悟,“坊主原来说,出不了一年,并不是说黄斑。因为我扇面没弄好,现在已经略有些变色,到一年后,发黄会看得出来,而这竹骨,靠着坊里的手艺,是一年绝不会发黄的玉竹,两相搭配,就很不协调了,竟不如选有些黄调的竹子、或者上漆的,那还看得过。真正在扇子上用心的人,怎能容许自己的扇子才出一年,就没法入目了?我果然没有做好!”
“青羽……”谢扶苏心里很不好受。
青羽站起来,给谢扶苏深深鞠下一躬:“都是我不好,让扇子这么容易就会坏掉。我要回去坊主那里了,请先生保重!”
“你要回去?”虽然早就预料到,谢扶苏还是胸闷,“反正她也不知道会出霉斑是不是?这样,可以再多一年……”
“先生,答应了的事,怎么可以骗人?”青羽吃惊看他。
“如果这件事关系很重要呢?”谢扶苏无可奈何,“如果我说,这关系着你的身世,你不应该回到那人身边呢?!”
青羽呆立片刻:“我的身世?”
“是。”谢扶苏豁出去了,“你有可能是我要寻找的一个人的孩子,你们坊主知道你的身世,却不告诉我!我一直在努力确定,你是不是那个孩子,请你多给我一点时间。”
“我……”青羽看了看自己,难得脑筋转了过来,“我长得,不像你要找的那个人?”
“不是很像。”谢扶苏只能承认。
“所以,教我吹埙,还有教我其他东西,是想确定我像不像吗?”青羽悲伤道,“因为我的父母会这些吧?我学得都不好,所以,完全不像是他们的孩子吧?”她把埙拿出来,交在谢扶苏手里,“让先生白花力气了,对不起。”
“别说得那么早!”谢扶苏心烦意乱,“气质上也还是有点像的。也许你就是。”
“如果我是,先生会怎么做?”
“让你过好的生活,带你回去给父母上坟。”
“如果我不是,先生又怎么做呢?”
“继续找下去……当然,我也还是会尽力照顾你。”
“对我来说,好的生活,也是可以继续跟先生和坊主生活在一起,练习我熟悉的事,比如做扇子,争取把它越做越好。”青羽微笑,“所以这样看起来,两种也没什么区别呢。坊主不对先生说,一定有坊主的道理。先生不要责怪她。”
“你这么信她?知不知道她是什么人!”谢扶苏这些年再修身养性,烈火性子也终于给勾了起来,吼道。
“坊主是坊主。”青羽坚定,“就像先生,虽然会飞、会跟人比剑,但先生还是先生。”
“你……”谢扶苏双肩垂下去。真的,嘉以前是什么人?他又是什么人?他有什么资格谴责嘉。他们几个,都是做错过事情的人而已,嘉也许深恨着他,但按这几年的情形来看,对青羽是不赖的,不管青羽是不是那个孩子,也许继续让他们过这样的生活,对谁都好。他为什么一直不敢对青羽说身世?可能因为嘉威胁他不准说出来,可能,因为他自己不敢把自己的身世向青羽坦白。栖城呆久了,悠然温润的气候渗进骨血,他仿佛真以为自己是个与世无争的郎中先生,要怎么说当年啊!当年……
“你还是要回你坊主那里去吧?”他问。
“是。”青羽回答得很难过。但只要确信是对的事,她就一定要去做。多固执的脾气,多像那个人……
“随你吧。”谢扶苏收起埙,转身离开。
他已经不太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不确定自己应该做什么。在栖城这个世界里,他永远是局外人。不,在整个人生中,他都一直是局外人。离开也好。门外黄叶零落,栖城的秋天已经到了。
四季轮转,再和熙的城池也有秋天;再大的决心、再高的期许,也终有一天,抽身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