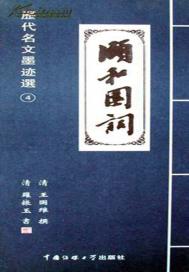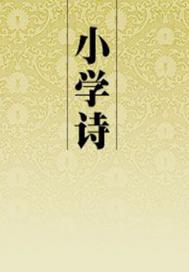胡大夫一行在十支枪的“保护”下,随罗洪夫人来到一个山谷。
山谷中散乱地坐着、蹲着、卧着带枪的彝人,至少有三四百名。少数黑彝头人聚在一起喝酒、吃肉。大多数鸠形鹊面,衣不蔽体的彝人,或聚或散,坐在树下水边,剥着自己带来的烧土豆,或是从羊皮袋掏着糌粑面往嘴里填。拿的枪却是各种各样,日本造、捷克造,美国汤姆式,加拿大***。
娃子给工作小组送来了烧肉和土豆。黑夫人远远地坐着,看也不往这边看。
胡大夫招呼大家吃饭,人们都过来拿土豆和烧肉,唯有罗赤中低头坐在一边看也不看那些食品。穆歌劝他说:“你也吃一点嘛。”罗赤中说:“我陪大家到我的家支来,受到这样对待,没有脸吃饭。”
杨柳堤说:“大家知道你作不得主。坦白地说,以前听说你是奴隶主,我对你还有点戒备,现在对你完全理解了。”
罗赤中说:“你看这些人,盲目崇武,真够可怜。”
曹先生和谷剑云不放过考察机会,一边问一边掏出笔记本来记:“这些人都是你家娃子?”
罗赤中说:“大部分都是曲诺。阿呷和加西不参加打仗,本来也不多。”
孟先生也跟着问:“他们的枪是主人发的还是自己带的?”
罗赤中说:“自己买的,连饭也要自己带。为主人打冤家是曲诺的义务。”
曹先生又问:“如果打死了呢?”
罗赤中说:“要是本家败给了对方,就白死,赔偿费还要曲诺分担。如果打胜了,向对方要赔偿。死一个曲诺赔十二两银子,给他家人六两,主人留下六两。呷西和阿呷死了,赔的钱全归主人。”
谷剑云问:“要是打死了黑彝呢?”
罗赤中说:“那就赔得多了。总要百两以上。”
穆歌和张念本听他们谈这些有点不耐烦。穆歌打断他们说:“我们不能就跟着他们走,必须设法制止。”
孟先生是信佛的人,连说:“对,以和为贵,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曹先生和谷剑云很想看看彝家打冤家从计议到发兵的实际情形,提出来要争取参加他们活动的全过程。希望能得点第一手资料,当然也不愿他们真打得死的死伤的伤,血流遍野。希望制止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既看到点真实情况,又避免真正开火。但这话没法说,就沉默观望。
杨柳堤看出他们的心思,便不指名地说:“各位,贯彻民族政策要紧,咱那学术研究还是放在第二位吧,能早一分钟制止住别拖到下一分钟。”
胡大夫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叫我开个腹腔,截断肢体我倒不怯阵,可叫我跟人唇枪舌战谈正事,我的话碴总是跟不上。杨柳堤跟穆歌二位是老同志,你们是不是找那女人再谈一次?”
穆歌说:“可以,我去把政府精神讲透,告诉她,如果不听劝告,将来政府要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张念本说:“最好讲点策略,好言相劝,不作警告、威胁之语。这是个没开化的女狂人,闹得太尖锐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穆歌说:“罗赤中都要用胸膛挡住枪口,我们还怕什么?要敢杀我们,为坚持新中国的民族政策而死,也算死得其所。”
张念本说:“您还是讲点策略,暂时收起你的艺术家气质!”
杨柳堤说:“罗赤中同志谈谈怎么讲好?”
罗赤中说:“为避免流血,叫双方都往后退一步,坐下来讲理;政府会秉公而断。”
曹先生说:“彝族是个尚武民族,打起仗来个个争先恐后,还会有退让的事情吗?”
一直沉默的曲木阿芳,这时插嘴说:“有的。要叫进攻一方暂停火,双方后撤,有个百发百中的办法!”
大家忙问:“什么办法?”
曲木说:“那要被攻的一方有个女人站出来,挺立在火力中间摇摆她的裙子,再凶的头人看见也要停火。这是我们彝族的习惯作法,大家都遵守的。”
曹先生马上问:“为什么?”
曲木说:“女人亲戚多,万一把她打死,她的娘家亲属,姐妹家族,妈妈的亲戚家族都会发誓为她报仇,全成了凶手的冤家,谁家也不敢结这么多的仇人!”
曹先生和谷剑云赶紧把这一条又记在本上。
曲木带挑战意味瞟了罗赤中一眼,说:“可不知阿候家有没有个姑娘,能冒这个险。要不为了心上人,怕是没人上火线上舍这条命的。”
罗赤中瞪了她一眼。但曹先生全顾不上这些,仍接着问:“非要阿候家的女人吗?罗洪家的不行?”
罗赤中说:“这是要进攻一方停火的办法,我们家的姑娘不能自己阻挡自己人!”说完他小声用彝语对曲木嘟囔了两句,曲木顽皮地笑了。
黑夫人传令继续前进,把话题打断了。
从这里出发后,又转换了一个方向。胡大夫问罗赤中,现在到底在西昌的什么部位?罗赤中在手心画图说:“我们从西昌的东北转到西北,距西昌比前两天还近了些。”
当晚他们到了一个很小的寨子,只有一户人家,把工作组的人安置进屋,其他的人,连同罗洪夫人都在树林里过夜。
彝人们在树林中烧起篝火,埋锅造饭。晚饭后,黑夫人叫出罗赤中在门口谈了半天,随后罗赤中领那女人走进屋内,对胡大夫说:“她说队伍集合起来了,非要请政府来的领导讲话。你自己对她说吧!”
那女人便微笑着说了一阵,曲木为她作翻译。
曲木说:“她说这次出来要打阿候家,收回失地。阿候家是反动派,当过剿汉司令部的分队长,现在也不跟人民政府靠近。她要替政府除去一害,政府的人随同来到前线,大家很受鼓舞,开战之前请政府首长一定给他们训话。”
曲木翻译完,罗赤中对那女人叫了声什么,那女人也回了他句什么。站在门外的两个带枪彝人听到叫声,冲进屋子,气氛骤然紧张,有一触即发之势。胡大夫不知所措,杨柳堤却露出笑容说:“大家不要动气,我们讲话就是了,大家随我来。”
曲木把话翻译完,那女人冷笑着瞪了罗赤中一眼,请小组的人跟她一起走出门,走向烧着篝火的地方。
彝人的武装,其实称不上是军队。行军是一片,驻军时是一团。既不列队也无编制。各头人带着自家娃子,散乱地凑成一堆。
罗洪夫人先给大家讲话。曲木小声翻译给胡大夫等听。罗洪夫人说:“我们这次来打阿候家,有政府派来人亲自坐镇。阿候家不听政府的话!他强占我家的地盘,今天也该归还了。我家罗洪支头是政府的官,占我家的地就是反对政府。你们要勇敢地打。现在请胡长官讲话!”
胡大夫给人看了半辈子病,从没遇到这样狡猾蛮横的人,气得找不到话说。彝人叫了半天,他还没想好措辞。在一边的穆歌对胡大夫说:“我替你去讲。”张念本想要阻拦,胡大夫已点了头。
张念本着急地对胡大夫说:“你怎么叫他讲,这个人不讲政策,感情用事,闯出祸来怎么得了……”
话没说完,穆歌已经用他唱男低音的嗓子,一字一句讲起来了。
“诺苏兄弟们,你们支头反对不听政府话的人,这很好。反对彝人之间互相抢占地盘,我们也赞成。”说完对身边的罗赤中喊道:“你给我翻。”
张念本着急地对罗赤中说:“先别翻。”穆歌喊道:“快翻。”下边的彝人也催促快翻,罗赤中便大声地翻译起来。
张念本埋怨说:“完了,完了,我们不能制止可也不能赞成哪!叫他讲话犯了个大错误。”
杨柳堤沉着地说:“别急,大不了他讲完我上去补正一下,叫他往下讲吧,总不能讲一半把他拉下来。”
穆歌又接着讲了,声音又比刚才提高了八度!
“可是除去解放军之外,政府反对任何人使用武力!我们来坐镇是劝大家停止战斗。不听政府话的人,可以把他的罪行告诉政府,由政府处治。彝人间的历史旧账,只有在政府调解下谈判解决,不能再打冤家。过去反动政府,军阀杀我们还杀得不够吗?不能再自己杀自己。我劝大家向后转回家去,有问题请政府协助解决!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罗赤中开始翻译时还有些犹豫,有些勉强,随着穆歌的论点一转,调门提高,他的精神也足了,几乎是声嘶力竭,一个字一个字喊出来的。
罗赤中这边喊,罗洪夫人那边就焦燥地作手势要他停嘴。等他全喊完,有的彝人竟欢呼起来。她扫兴地骂了句什么,叫人把慰问团的人连同罗赤中全请回屋里去,在门外多加了一道岗。从此再不跟慰问团的人接触。
回到屋里有人给穆歌鼓掌,有人向他伸大姆指,还有人说:“您这大贝斯嗓子,就是好听,比您唱歌还好听。您不光是歌唱家,这回还兼演说家,外交家了!”
杨柳堤说:“老天爷,你讲头几句,吓得我心快跳出来了,没想到还有个大转!真有你的。今天咱们得为歌唱家记一功。”
张念本讪讪地说:“您那天一冲动,什么政策都不顾了。怎么今天这么有分寸?”
穆歌不无得意地说:“告诉你们,咱是当过演员的!那天毫无准备,受到突然刺激,忍不住暴露了内心感情。今天这事已有思想准备,主要的话是准备好跟黑夫人个别谈的,临时掏出来用上了!见笑见笑!”
正说着外边砰的响了一记沉闷的枪声,大家赶到门口,只见几个彝人抬着一个腿上流血的中年支头过来,罗赤中问了几句,对胡大夫说:“正议着事有个人枪走火了……”
胡大夫马上叫人把他抬到院里,找来一块较干净的木板铺在墙边,把那人放倒。那彝人痛得浑身抖动,震得木板咯咯响。胡大夫叫彝人们散开,他和邵美华动手为他先止血,后检查,查看了足有二十多分钟,胡大夫擦着汗说:“粉碎性骨折,而且这子弹含铅,必须马上动手术截肢,时间一拖延怕后果不良!”
罗赤中把话一翻译,众人一片骚动,连黑夫人都面色紧张,因为那受伤的是她娘舅。一扫刚才的倨傲劲,对胡大夫连连作辑,求他千万保住伤者的性命。
胡大夫跟邵美华小声交换了下意见,无可奈何地说:“我尽我的力量吧,可你要叫伤者忍住痛。你们赶紧想法去找一把锯来,把这锅烧满开水,尽快烧开后把锅洗净再烧一锅备用,别的人都散开,这地方不许闲人再进来!”
黑夫人传下令去,众彝人都退了出去。胡大夫就请大家都把行李打开,把被单凑在一起在院里搭起个临时手术棚,并把自己一条新床单撕开,放进大锅中去煮。他点名请几个人作助手,别人一律退后。他要的是谷剑云,张念本,杨柳堤。谷剑云和杨柳堤的任务是等他锯腿时负责按住那伤者的脑袋和全身。张念本的任务是帮助邵美华传递纱布等工具。把找来的锯,刀,和他带来的镊子,夹剪用石碳酸和酒精消毒。
穆歌和罗赤中来找胡大夫,对他说:“这是天赐的机会。现在我们准备同黑夫人谈判,动手术可以,但要她停止进攻阿候家,如果不听劝告,这手术就不作!”
胡大夫连连摇摇头,张开两手说:“不行,绝不行!虽然我知道你们是好心,我更反对打冤家,可是作为医生我不能同意,救死扶伤是不能讲条件的。你们再想别的办法,绝不能以拒绝救命作威胁!”
胡大夫一向说话风趣平和,从没这么严肃郑重过。穆歌和罗赤中只得扫兴而去。
黑夫人经过一番辨论后,说服了众彝人,准备明日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