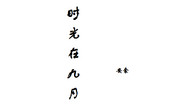一九四九年冬天到一九五〇年春天的北京城,天天像过节,时时有喜庆,这里新单位建立,那里老章程革新,南边解放一个城,西面起义一个军,开不完的代表大会,不间断的庆祝**。苏联专家拍电影,各单位要到天安门协助演出;****首脑海外归来,各方面赶去车站欢迎,拍的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讲的是“各族各界大团结”。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上演;新中国第一个剧院成立;新中国第一批飞机上天,新中国第一辆机车出厂……凡是新中国的新事全要庆祝一番,兴奋一番,人们忙得天旋地转却又嘻笑颜开,谁都那么任劳任怨,谁都那么大公无私。古旺元在这种气氛中,忘记了自己烦恼,到剧团后跟大家一起很高兴地疯干了一阵子。
当这股建国热潮慢慢降温,回到正常生活轨道上时,他就觉得不如意了。
在演出团体没有发展前途,才离开宣传队来北京。到了北京还是在演出团体,却又失去了同甘共苦过的战友和了解他的上级。烦得他一天到晚唱:“我好比南来的雁,失群飞散;我好比浅水龙,被困在沙滩……”
这是个新成立的剧团。人员有三大类。一类是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老延安;一类是早在国统区就出名的大明星名导演;第三类是进城后才招的小青年。古旺元跟哪一类都靠不上。与明星名人固然不沾边,距老延安也差着千八百里。可他又不肯承认自己属于这小青年阶层。他参加过抗日,打完了整个解放战争。艺术修养,工作经验上自认为比这些娃娃高出不止一头。
他往高人中凑,人家不大答理他;青年朋友主动来找他闲聊,他又看不惯人家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谈话口气中总表现出资格比人老,干起活来又不比人高,他又有表现欲,当了几年文艺兵别的没学会多少,却记住了文艺界的一些奇闻趣事,天方夜谭。每到换完布景,在后台休息时就又跟人胡吹乱侃。这后台本就是个传小话惹是非的所在,他说时只顾眉飞色舞,听得人也忘词误场,但走散后人却对他更加摇头。没有多久,古旺元在剧团就成了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角色。
一个团体有一个团体的风气,一个团体有一个团体的传统。在军队的宣传队中,成员都和古旺元相处多年,同甘共苦,经历相似,互相间的性格,作风也都看惯听熟。到了这陌生的地方,不懂得入乡问俗,古旺元处处碰壁,是理所当然的。
古旺元感到孤寂和苦闷。后悔没回军队。也终于明白,不论在哪儿,要想有出息,都得靠自己努力拼搏。
人们聚会聊天,结伙出游,自然而然把古旺元排除在外时,他就把业余时间全消磨在图书馆里。
附近有个公共图书馆,书虽不多,报刊倒齐全。他每天都在这里消磨几个小时。
古旺元没受过正规教育,读书倒是既上瘾又用心。
这天看杂志上有篇小说,题目叫《石锁》,写了个农民出身的军人故事。说这农民参军前见了地主叫干爹,生来有奶便是娘,自己老婆叫地主占了还忍气吞声。直到这地主弄出人命。密谋要把他送到县衙去抵罪,他才吓得跑出去参加八路军。一下子竟成了革命英雄。古旺元觉得和他熟悉的革命军人相去太远,丑化了他的战友,伤害了他的感情。一时义愤,就写了篇反对的文章。学着批评家语气,连问了几个:“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这样形容我们的革命战士,是哪个阶级的思想感情?”等惯用词句,寄给了刚创刊不久的文化杂志。
稿子寄出后他掐着指头数日子。到临近那刊物出版的几天,天天注意报纸上的广告。
上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新一期刊物的目录上他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他立即上邮局指名买这期刊物。可人家说刚见广告,按规矩要过三四天刊物才能到门市。
他坐立不安,连坐下来看书也稳不住神。就上公园转了一圈,又逛东安市场。晚上早早的就去了剧场后台。
一进后台,几个提前来化装的人眼光都投到了他身上。有人喊道:“哈,青年批评家到了,大家欢迎!”有人说:“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别看人家平时稀里晃荡,肚子里还真有学问……”这里有赞扬,有玩笑,也有讥刺。古旺元心情好,毫不计较,笑脸相迎。他估计是人们见到广告,在这里已经把他议论了一番。故意装作摸不着头脑地问:“怎么了?今天商量好了拿我开涮?”一位演员就说:“别装了,大作我们刚才轮流拜读了,说话就要鸟枪换炮,名扬四海,快掏钱请客吧!”古旺元再沉不住气,说道:“真见到我的文章了?可我刚上邮局去买,他们说还没到呢。”这时吴峰就把一本新的刊物送到他面前。说道:“那是零售,我是订阅的,收到得快,你看看。”
古旺元抢过杂志,先翻目录,眼睛在自己的名字上停留了足有三分钟。等到翻出自己那篇印铅字的,加了按语的,占了整整一页的文章,他心动加速,血液上涌,只觉每个字都在跳动,想认真读一遍都有点困难了。
但还是飞快地把编辑按语读了一遍。编辑说:“旺元同志这篇文章,虽然分析粗糙了点,论述简单了点,但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指出的问题是严重的。值得重视,希望引起讨论……”
吴峰说:“不错,到底是老同志,在政治倾向问题上还是敏感。以后再接再厉。人家编辑给你提的缺点也要重视。看来你的聪明劲够了,就是学问上还差点。以后多自学点理论知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
古旺元听了连连称是。这倒不是应付,而是出于诚意。他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听人家批评心平气和过。
正被大家连玩笑带赞扬弄得有点昏昏然时,平日不到剧场来的穆歌进来了,手里也拿着一本杂志,面带不快之色。一见古旺元在座,便举着杂志问道:“这篇东西是你写的?”
古旺元道:“是的,请您多批评。”
穆歌斜眼看了他一下说:“年纪不大,口气不小。人家赵树理还没你懂得多?”
古旺元被说得摸不着头脑,说道:“我这文章跟大作家赵树理同志没什么关系!”
“你看你看,杂志到手光看你自己的文章呀?看看你后边那篇!连那本杂志是赵树理同志主编的都不知道,还写文艺批评!有不惹事的吗?”
古旺元再把杂志打开,这才发现,就在他的文章后边,确有一篇署名赵树理的答辩文章。题目就是:《旺元同志文章读后》。
古旺元匆匆读了一遍,这篇文章用语很客气,对古旺元的批评表示接受一部分,但也有一部分持保留态度。
古旺元看完说:“赵树理同志也没说我批评的全错,而且并没有生气的意思嘛。”
穆歌说:“人家是大作家,有修养,对你小孩子犯不上动真气。可是你等着,下一期这本杂志就有篇完全肯定小说《石锁》,对你严加批评的文章。你作好思想准备吧。”
古旺元说:“人家编辑的按语早说了,欢迎继续讨论。我愿意好好听取别人批评,提高自己的认识。”
穆歌说:“爱好写作就写点通讯呀,散文呀什么的练练笔呗,上来就批评人。太不知天高地厚了。作文字工作的,就要讲究谨慎。没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像你这样不知天高地厚,早晚要捅大漏子。小心点吧,你。”
一盆冷水,把古旺元的高兴劲全浇下去了,他便低下头跟人去搬布景。
古旺元离开后,吴峰对穆歌说:“您是不是也太严厉了点。年轻人写篇东西,还是以鼓励为主嘛。”
穆歌机密地说:“杂志社的一位老朋友来看我,偶然说起熟人情况,他讲张念本近日交给他一篇文章,是评论小说《石锁》的,写得热情洋溢,赞不绝口。他刚走我就看见了小古这篇文章。这个张念本你是知道的,消息最灵,跟政策最快。他没有把握不会为别人的作品叫好。小古这不是找苍蝇吃吗?我是为他好才批评他。”
吴峰听后没再言语。他对穆歌很了解,这老先生向来是听见风就是雨,对人马列对自己自由。不然不会三八式的老专家,直到进城之前才入党。此人资格老,脾气怪,谁也不愿惹他。剧院安排他个研究员闲职,他则以老专家自居,到处插嘴。领导也只能听之任之。人们背后称他是用不着、调不动、管不了的“三不干部”。他爱管闲事,考试古旺元时,吴峰临时找不到人就找他,因为按规定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考官在场,才算有效。
整个晚上,古旺元都低着头过的。散戏之后,大家都上东安市场去吃夜宵,古旺元无心同行,自己想遛回宿舍。吴峰从后边赶上,拍拍他肩膀说:“你不必泄气,真有不同意见的文章发表也是好事。真理越争越明嘛。再说你的文章又不是没道理。只是分析得简单,口气大了点,这叫粗枝大叶的老气横秋。可看得出你在这方面是有发展的。继续努力。你会有成绩。”
他听了感激不尽。连声说等那篇意见相反的文章出来后,一定仔细学习。今后也要认真多读点书,再不写这种简单化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