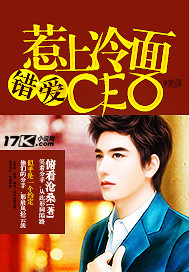一
现在正是下午两点钟。西去的太阳够意思,拂在身上不冷不热不亲不疏不卑不亢挺舒坦。我的长征牌自行车在砂石公路上哗啷啷地转。这车子主儿多。谁摸到手里谁摆弄。我骑时把座子拔出来,我老头骑时又把座子按下去。高高低低三番五次,把个车座拧得直摇晃,一骑上去就象腿裆里夹了个不安分的小毛驴,一忽儿东一忽儿西,别扭得没法说。就这种车子还驮了俩人。后面衣架上坐的是我的堂弟我二叔的儿子大嘴。他叉开两条木杠似的长腿双手搂着我的腰正在哼唱着自由散漫惬意曲。他个儿比我还猛,不时地把两个大脚板搓在地上,弄得沙沙直响,我老大不快,用胳膊肘朝后一拐,捣在他肉绷绷的胸脯上。他可着嗓门“噢”地一叫,不用看我也想象得出,他的大嘴角到耳朵根恐怕只有一指头宽了。“别叫!你下来,该你带我一会了!”我说着就从车大梁上一收腿,支住了车子。大嘴仍旧坐着不动,我搡了一把说:“给你跑腿办事老叫我出力,象话吗?”大嘴右腿一迈下了车,不情愿地咕噜:“我骑不住这摇摆座儿,这哪有我的‘凤凰’好骑!”
“臭美个屁!‘凤凰’好骑算个鸟!你想要黑妹子呢!”我的调侃竟使大嘴乐起来,微微一笑模样惨极了,眼睛眯得好小好小,嘴巴咧得老长老长,这种笑态我敢打赌举世无双。
来时我就说过,大嘴今个儿穿得象入殓,时新花格衬衣,尼龙记者长裤,不看面相倒也有几分人样。可再好的衣服也掩不住他身上一股股的汗臭酸气。二婶常训他,“身上灰有铜钱厚,赶明儿成了家,让媳妇在你背上擦火柴!”我则打趣说他身上有座自控化工厂,专产碳酸氢铵和尿素。他也不在乎,在乎又怎么办?他在水泥厂干活,活儿重出汗多,加上他又懒洗弄,常年身上有股味。一看到他,我就想到这股味,索性背靠背坐在后衣架上。脸朝后坐车有一种新奇的快感舒服得很。小风微微吹,象一只温柔的素手轻轻地抚摸我的脸,使我产生了一种温馨的冲动和莫名的渴望。四月是充满了梦幻的季节,天空象碧蓝的宝石,偶尔有几朵白云缓缓移过,如刚刚弹松舒软的棉絮,把湛蓝透明的空间,擦拭得更加透明闪光。那盎然的绿充满生机一直延伸延伸,直到天尽头,大平原上的村庄全都被浓绿淹没了,连同我们刚刚离开的杨庄一起。只有路旁稀稀疏疏的小花不时的在草丛中探出羞涩的小脸。鹅黄的蒲公英、雪白的荠菜花、紫红的麦眼珠子,还有蓝格莹莹的野藤……
我提到黑妹子后,我俩都不说话了,车轮在转,没准儿我们两条汉子同时都在想着一个人——黑妹子。
二
黑妹子几乎和所有的乡下姑娘一样,身材不高很壮实,脸孔不白很耐看,衣料不好很鲜艳。唯一不同的是她没有象其他乡下女孩子那样烫起蓬松的卷毛。依旧是整整齐齐一刀剪,顶上劈出个大圆盘,那只发卡倒多少有点现代化气息,金黄色的花纹在朗朗的太阳天里直晃眼,恰到好处地点缀那一头略显呆板的乌发。黑妹子上过几天学,多少识几个字。亲娘死得早,便早早辍学来家带弟弟。父亲有老年病,一入冬便似蛙儿入蛰躺进了被窝,稍微受凉伤风,便打针吃药咳个不停。黑妹子带着弟弟跟着父亲打发日子真够难为。父亲每发觉病重便哀戚戚地独自落泪,唯恐过早地伸腿闭眼抛下个独头儿子打了光棍断了祖宗的烟火。黑妹子自打下学便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手巧腿勤,过日子总想跟人攀比。心有天高,命比纸薄,摊上了这老老少少病恹恹的家,死活累几个子儿还不够拿药钱。常常落到叫天不应哭地不灵的地步。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从各家门前过,“困难户”的牌子一背就是多少年,黑妹子自觉出门矮人三分。赶集上店、下湖种田,自个儿沿路边匆匆走,从不与人交往。这几年乡里姑娘闹“自由”,跑的逃的多的是,唯独黑妹子落了个老实憨厚的好名声。黑妹子原本有小名,叫黑妞。有一年,村里来了个做木匠活的江苏小蛮子,人称小木匠。一日清早小木匠去井台打水,看见了正在洗菜的黑妹子,顺便问了房东一声:“井台上是谁家的黑妹子,恁俊俏!”村里人叫小名叫惯了,一听到房东传出的这话,便觉得很新鲜,又加上黑妹子的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粘糊味,就象品尝五月仙桃子似的,试着叫起了黑妹子。黑妹子长黑妹子短,一叫还真的叫开了。从那以后全村人都知道黑妹子,却把黑妞忘了个净光。黑妞这名儿太土气,听起来叫人不快活;黑妹子早就心烦了,可是小名是爹娘所起,就象道路可选择出身不由己一样,烦也没有办法,现在人们统称黑妹子了,黑妹子打心眼里乐意。她感激这个小木匠,听说还拿着功夫暗地里偷偷给人家做了双松紧口灯芯绒布鞋,可是没有送成,那小木匠做完木器活急着归家就溜了。黑妹子暗暗流泪,难过了好些日子,咒那个小木匠没命享用。后来黑妹子渐渐成了大模大样的女孩子,这事也就没人再提,再后来就是黑妹子弟弟拴柱长成个儿,黑妹子父亲整日东托西托找人给儿女“换亲”,这二年愿换亲的不多了,人们情愿多出几个钱也不肯担那个名气。
三
我们这个村子在我上小学的时候,还和周围所有的乡村一个模样:门前栽树屋后种瓜,水下养鱼水上放鸭。春播夏锄秋收冬藏,年三十贴门神正月十五打灯笼端阳插艾蒿中秋节摸秋送冬瓜。那时我们村子叫花巷子,三十五户杂姓人家,共同杂居于此,不分亲疏无忌长幼,朝夕共处,声息互通。我们村不远有个古老的镇子,格局不大挺有来历,据说刘邦项羽曾在此驻足,一场力拔山兮的恶战留下了千古不绝的悲歌。一忽儿这镇子升成了县城,这县城象吃足了化肥水似的,一股劲儿地向外涨。没有几年光景,就把四周的乡村土地揽了过去,我们花巷子也跟着编到城关镇蔬菜大队。那乌黑的沃土一点点被蚕食,一幢幢火柴盒似的楼房竖起来了,大大小小的机器拉来了,一个个白底黑字的牌子挂起来了。种惯了芝麻黄豆小麦大红芋的乡亲们开始挖机井挑粪桶修菜园。新旧更替,原是势所必然的事,但对于这些世代认为玩龙玩虎不如玩土的农人来说,不亚于拿刀叉吃饭,多么的不习惯不适应!再说那些大包菜、花菜、空心菜、柿子椒真比表叔二大爷还难侍候,水多淹了、水少干了、热了冷了无所适从,一点不周就出漏子。花巷子的人不甘心吊在种菜这一株树上,几百口子各自寻找发财之道,跑天津上海做买卖,在街头巷角摆地摊,三五个一伙搭个棚子卖小吃。几个月下来一合计都比种菜合算。不管干哪行,挣着票子就行,有票子就有饭吃,没有票子日天的本事也白搭!这就是花巷子人的信条。那些长着前后眼的小诸葛,看准了小城的发展趋势,干脆找机会私下里将地皮卖了,三五千腰包一装,虽然多少有些后怕,但总是喜悦大于不安。我二叔就是这种情况。每逢邻居喜形于色地数着票子合计又赚了多少钱的时候,我家老头子就蹲在墙角红着眼叹口气:“外财不发命穷人,走着瞧吧!”他的话算个屁!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人家都靠外财发了,这年头什么叫外财?什么叫内财?翻老皇历不行了!别看我家老头古板没本事挣钱,就是有本事生养儿子。七大娘就笑话过他,说他是个种马。我排行老大才满二十三岁,下面嘟嘟噜噜却还有五个弟弟。照现在的行情市价,六个闺女六个金库可以竖起六栋楼房,而六个儿子把老头子累断筋骨也娶不上六房媳妇。我们弟兄几个也不觉多少清闲,老三老四老五老六正在上学,家庭作业多如牛毛。老二初中毕业没考上重点中学在职业高中混了二年溜回家来吃闲饭,新近勾搭了个水果摊上的红唇儿,天一黑就双双搭肩勾臂,进剧院去看草裙舞、三点式健美操,还有震耳欲聋的迪斯科皇后。反正花销都是红唇儿卖水果扣下的零钱。至于我嘛!唉!提蓝小买拾煤渣,担水劈柴卖甜瓜,爹是出嘴瞎指挥,我是卖力实干家。白天累得腰眼疼,晚上打呼噜的劲儿都没啦。刚高中毕业那年,眼看我的同学上大学的、招工的都混得挺气派挺神,可我只能挑着粪桶转悠,真恨不能一下钻进地缝里去。几年过去,村里人,当然后来就不叫村了,叫居委会叫安乐巷。巷子里的房屋一律地换成了青砖平楼,独我家的依旧是土墙土院土草屋土门楼,老远望去象久经风雨侵袭的古堡,极寒酸极悲凉极显眼醒目。眼下学杂书费涨潮一样加价,每学期一开学我家就得几百元砸进去。二年前我老头眼看种菜实在不行了,才咬咬牙买了一辆小板车和一头小毛驴,让我参加镇上的短途运输队。一个高中生并且是挺有水平的高中生,每天和一头毛驴子靠膀子轧马路,这形象有多难堪!我伤心得一夜间几次想爬起来去摸电灯插头。我爹开导我说:自古人生事难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要他弟兄四人能念出书来,将来大学一毕业,咱贾家也就人财两旺出人头地了。最管用的是那头一百元买来的大灰驴,它吃的是草,出的是力,流的是汗,每天省了我许多力气。放空车的时候,我就跳上去,躺在板车上蒙上双眼,吹起口哨。我的口哨吹得相当来劲,大嘴恭维说是肉琴。大灰驴颇通人性,口哨一响,碰上什么复杂的局面它都不惊不乱,有条不紊地撒开四蹄。太阳总是暖哄哄的,我睁开眼睛偶尔望见了大灰驴那根悠来晃去挺有风度的长尾巴,便突然联想到女人乌黑发亮的辫子,真他娘的见鬼了。
运输队的分配制度也渐渐体现了时代风彩“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我和驴子一同加劲,那大票子便哗哗进了哥们的腰包。我的心情随着票子的增多,逐渐地安宁悠闲下来。我家老头也渐渐地习惯并弄懂了挣大钱的道理。我们家第一次筹划着盖新屋了。和隔壁二叔家一样盖平楼。二叔家人口轻、底子厚,大嘴和妹子毛丽都不上学,二叔整日捣咕转手生意,二婶在建工队打杂,四口人进得多出得少,加上盘算日子特精细。一划为城镇户口时,二叔眼明手快,将分得的菜地卖了一角,三千元一把头交给了新建的水泥厂,给大嘴买了个合同工干,大嘴一转身变成了县城的工人。天底下还是钱好,有钱能买鬼推磨,就凭大嘴念了八年一年级那副灵性,也穿上了工作服。而我呢,高考只差两分没走掉,却只能天天陪着驴子走大街过小巷招人白眼。唉,每当夜晚,大嘴在隔壁平楼顶上喊:“大全哥,大全哥!来,快上来!上来看灯火,亮得很呐!”我就在院子里的小草屋暗暗忧伤,我和二叔家的房子原来都是一条脊的平房,并排六大间,后来东西邻居都盖起了楼,拉起了院墙,我们两家自然连成了一个大院子。小草屋对门就是我妈住的土屋。我望着土屋里我老头那一明一灭的烟火,恨不能将那土屋一下子踹倒,可惜不能这样,因为我妈还在里面摸黑为我搓洗衣服。
其实我心里真瞧不起大嘴,别看他有钱,财大气粗。我和他比,简直就是西施兰夏露和马尿并举。他识不了几个数,连秤星也认不准,去年他小妹毛丽子还常常叫嚷他尿湿了被子。他比我小两岁,样子看上去却大得多,一年四季面孔红红,就象平锅上贴出来的高粱面粑粑。平时言谈,三句不说就下道,露出一副不癫不实的气相来。他五岁时还不会说话,十岁时不会提裤子。二叔说不着急,就凭大嘴这福相,也能一强压百弱。大嘴福相是七大娘给发现的。据说,大嘴刚出生时就眼小嘴大,不受看,二婶有些不喜欢,七大娘却说,人生有几种福相:脚大走路稳,这是打长工的料,手大拿钱准,这是个管家的相;眼大看四方鼻大闻臭香,这是个官样;嘴大吃猪羊,这是福相,这孩子嘴大有吃福没罪受的。这么一说,二叔二婶无比的欣喜了。他们坚信,不管走什么运都行,只要福禄一生就不枉活一世,大器晚成的多着呢!后来二婶生了毛丽子,就再也生不出什么来了。我妈说这叫斑鸠生,一辈子只能生两个,还有一辈子只生一个的叫秤铊生。大嘴成了二叔的独根苗,二叔把他视为掌上明珠。儿子总是自己的好,不管别人怎么看待大嘴,二叔总是挺优越地说:瞧瞧吧!这孩子总算成人了!大嘴的个头窜得也真快,呼呼地见长,二叔二婶早已聚钱存款,托东家央西家给做媒人,别看二叔夏天冰棍都不舍得啃一支,可家里值钱的东西却不少,电视机录音机缝纫机……反正市面上流行什么他买什么,买回家来紧紧地锁着。那缝纫机二年不蹬,听说轴儿都锈得不转了,急得二婶直跺脚。俩口子一见七大娘就苦哀哀地说:“七嫂,总该想点法子吧!”七大娘说:“不急不急,二十刚出头,早呢!”二婶说过得快着呢!转眼几年就过去,越大越不好找!二叔说:“好找也得花大钱!”七大娘摊开两手表示无可奈何。二叔二婶便塞过些小东小西以示感激央求。七大娘便留下吃饭,这样的饭不知吃过多少次,总算有了点眉目。二叔二婶的脸上便突然象抹了层光油,格外地亮堂起来。平楼新粉刷了一层白,走廊的木柱子滴血似的红,让人一看便有了红白喜事的气氛。大嘴这小子也突然穿红戴绿的俏起来。可是,大嘴穿得越好,在我眼里就越象马戏团的小丑。
一天傍晚,跟驴子奔波了一天的我,在院子里轧井边冲洗了一会儿,就钻进草屋倒头便睡,刚想入好梦,我妈悄没声地进来了。“大全,睡着了吗?妈给你说个事!”“什么要紧的事明儿不能说!”我不耐烦地冲了她一句,慢慢地翻个身又去追寻那个刚启序幕的梦境,因为听人说,梦是一泓水,小心奕奕别撞着中断了还能续上,要不一翻身就忘个净光,再也寻她不着了。象我这样的小伙子真正有味道的日子都在梦里呢!
“大全,你别给我发横!”我妈用那双枯柴棍一样的手狠劲地推了我一下,“明天别去拉车了,你二叔找你去办点事!”原来是二叔求我。我拽件衣裳搭在膀子上,望着妈:“说吧!什么事?”
“你二叔说,东头你七大娘这一阵子跑了几趟,想把他娘家侄女说过来,再过一个月咱城关镇的居民户口都要转成商品粮了,吃小本子的,你七大娘是紧锣密鼓,催得很紧,叫明个儿去杨庄子见面相亲,妥了回来就过红子办喜事!”
原来是这样,我的睡意消失,周身一下子热起来,脸上臊红一片。我不再为我妈冲撞了我的好梦而不耐烦了。梦总归是梦,我不能老在梦里生活,这会妈说的才是真的。我吞吞吐吐说:“爹呢?我爹他怎么说?”
“呀!你二叔就是跟你爹商量的,你爹叫我过来告诉你!”
“好吧!明儿去!”我想不到自己答应得这么爽快。我常常想起高中同学李小丽,我俩一块参加华东六省一市作文竞赛,一同获奖,一同领奖。我俩一块儿参加大联欢晚会,她就是那样对我深情地唱:“请你对我说你爱我永不离开我,就象一股爱的暖流多幸福,伸出你的真挚双手紧握我的手,就象一湾清澈小河流进我心窝,请你好好把握千万不要错过,别让美好时光流走!”可是美好时光已经流走了,李小丽流进了复旦新闻系,我流进了马路架子车队。是我没好好把握吗?我要不是在考场上帮李小丽做了两道习题,也不至于数学弄了个六十分。不是这样,眼下该是两种天地。不是我家老头死活不让我复读,也说不定我现在胸前挂上了哪个学院的牌子。后来李小丽还算义气,给我寄来了一张散发着熏人奇香的歌片,就是那种明星歌片。上面印的是《那天晚上》,歌词说,“我知道你会怎么想,把我想成变了样,我不怪你会这么想,换了我自己也一样,那天晚上有美丽的月光,没有你走在小路上,那晚上有美丽的月光,没有你依偎在我身旁。”想不到我这个堂堂大男子,看完歌片竟软蛋熊包女人一般地嚎啕大哭起来。哭得昏天地暗、回肠荡气,哭得手足麻木头皮发炸,眼睛一夜间成了两个水灵灵的红桃。哭过后,心里好受了许多,松了口长气,便就原谅了那个可爱的月光。遥望南天默默**:小丽呵,有这歌片就足够了!哥儿们不怪。弯刀对着瓢切菜,骑驴背个破口袋,一个复旦高材生,一个马路天使驴把式,叫哥儿们自个儿做主也于心不忍。Bye-bye!我的青春、我的初恋、我的月光都淹没在得得的驴蹄声之中了。进了搬运队,也曾有几个姐儿眉来眼去暗送秋波。可是说真话,我一个也看不上。不是太俗就是太实惠,叫人没劲儿。从此,劳累时就盼那西边日头东边雨,寂寞时就哼几句“摇摇你的头摆摆你的手——”,那异性的风姿不再想。说是不再想,总有一番苦味在心头。特别是原野里开满了春花的时候、公园里逛满了游人的时候,还有那太阳暖洋洋地晒在我的肌肉上电风扇悠悠地吹在我的皮肤上的时候,一种蓬勃的诱惑叫我烦恼叫我忧伤叫我跃跃欲试叫我焦躁不安六神无主。我不得不诅咒这原始的撩拨,正是这撩拨使我的脑细胞活跃异常,不时地涌出一个又一个标致温情可亲的人影儿。我知道这叫走神。走神不是好事,古来为之丧命者不计其数。好在对我来说总是一瞬间闪过。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儿。一天的指标不完成,提成减少,奖金扣发。立杆见影就得受损失。我不能因虚无的幻想而失去实在的东西。真没想到,我妈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给我操办了这事。也没想到我这么快就答应了!这一晚我翻来覆去辗转反侧没打盹,我在想着明儿去相的那个女的是什么模样。象李小丽?象搬运队那几个狐眉子狐眼的?象二全的红唇儿?是胖是瘦是丰满是苗条,我的脑海成了荧光屏,一口气闪出十几个特写镜头,仔细一琢磨,都是看过的电影明星,或矜持微笑;或穿金戴银,或长发横飞,或搔首弄姿。我骂了自己一声“蠢蛋”,便如驼鸟似的钻进被褥,蒙住上半身睡了。可是,天知道有谁这样睡过,不久我便闷得喘不过气来。睡也折磨、不睡也折磨,索性起来到院子里走走。这晚月亮真好,月光无所阻挡地透过大气层,从邻家院墙上树缝里筛落下来,没有一点儿风。二叔家的墙壁与月光相映。一片爽心的银白。又见月光,又见月光,又想起那天晚上,李小丽乘着月辉,向我款款而行。她的长发也象明星似的隽永飘逸,她的衣裙也象明星似的超短艳丽,她披着银色的网,捧着特大的彩色封面采访本,腰里背着送话器,我怀疑那会不会是电棍,不敢立刻迎过去。其实我还没有内心有愧的事儿,还没有贪脏枉法的条件,是电棍又怕个什么。我骂着自己胎带的奴性伸长脖子睁大眼睛,终于什么都看清楚了,连她那白皙的小臂,修长的大腿,美丽的脚趾。她穿的是无跟平底皮凉鞋,唯一没有看到她的面孔,尽管我数次转身可也无济于事。她总是用柔软的长发遮住脸庞。是存心不跟我面见?一忽儿我也真的想不起她的鼻子眼睛小嘴巴是如何排列如何分布的了。一丝惋惜,一缕惆怅缠住了我的心,我醒悟出:那个面孔永远从我的生活中失去了,给我留下的只能是残缺的记忆与忧伤的回味。这足够使我难受一辈子。唉,毛驴子吃草真响啊!
四
受了一夜折磨,原来竟是这样!我又好气又好笑一个劲儿地朝我妈翻白眼。为什么昨晚不把话说清楚,害得我一夜神游,天亮起来胯骨眼里直转筋,下了几次决心连喊一二三才爬出被窝。真想赌气不去了,可耐不住二叔的软缠硬磨,七大娘的薄嘴唇能把扁的说圆死的说活,又加上大嘴可怜巴巴地望着我。好吧,一天少挣六七元算个什么!只是我觉得让我陪大嘴去相弟媳妇有点驴头不对马嘴。可是为了大嘴不再打光棍为了他不再去死眼珠子看那个黄毛丫头片子,我就答应了。其实我的任务很简单,就是骑车带着七大娘陪大嘴去杨庄走一趟而已。临出门,我二叔把大嘴喊到里屋,停了十几分钟推出一辆闪得晃眼的新凤凰自行车。啧啧!我清楚眼下黑市上凤凰的行情,这种正宗名牌,不容易弄到。二叔准是被那些黑心烂肝的倒爷捉了肉头。一问大嘴,才知道果真是三百五十元昨夜现推来的。我吸了口冷气。二叔真舍得出血。我家的破长征也推出来应急。三人二车一个不大的小队伍就朝七里外的小杨庄出发了。
车队行进到离杨庄子不远的小苗圃,大嘴突然跳下车,宁死不肯进村子。一会儿叫肚子疼一会儿叫头疼。这模样如何去相亲?我积极建议七大娘打道回府吧,七大娘看着蹲在地上的大嘴沉思片刻,便胸有成竹地说:“大嘴,你疼得可能受住了吗?”
“只是不能再走路了!”大嘴吱唔道。
“那好,你就躺在这片杨树林里,别动也别吭声,等我和大全进村办完了事,再回来找你!”
大嘴听完了,便象兔子似的嗤溜一声爬起来就朝林子里钻。慌得七大娘连喊:“车子!车子你看着!”等我把破长征搬进林子里,大嘴已经眉开眼笑的在地墒沟里挺直了身子。
出了林子,我心里直打鼓:家里叫我帮大嘴长个眼还可以,但大嘴自己不去怎么行?相亲相亲,他不去还相个什么亲呢?
我的疑虑神色自然逃不出七大娘的双眼,七大娘说:这也没啥大不了的,你是大嘴的哥哥,又有学问,自然当得起大嘴的家。再说,咱也不能白跑一趟。大嘴不能去,咱把见面礼凤凰车子送去,到时你什么也别说,尽管复个眼就成了!
没想到竟是如此简单,我也真想看看七大娘到底给大嘴找了个什么样的女孩儿,我甚至醋意地想到:好女孩儿若是给了大嘴未免太可惜!
黑妹子住在村西头一个独门小院里,房子很旧,茴草苫顶,小厨房用三根木棒斜叉下来顶着,一进屋就闻到一股年深日久的草霉味儿。一脚跨进门槛,差乎绊了我个倒栽葱,那感觉就象掉进井里差不多呢!房里很暗,刚从外面进来,什么也看不清,只听见一串串的咳嗽声,挺扎耳。七大娘径自朝那黑影里的咳嗽走去,一会儿就有了叽叽咕咕的说话声。
我站在冲门的地方,慢慢适应了屋里的黑暗,就看清了屋里的摆设,三间房两头住人,中间用蓝土布做帘子隔开,西间看样子是黑妹子的闺房,拾掇得清爽,黑墙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烟纸和影视明星头像。七大娘扭着小脚走出来了,给我倒了一杯茶让我坐会儿,之后又神乎乎地走回东头帘布后面。
看了一眼那个粗瓷大杯子,我喝不下去,便出门到院子里转转。出门槛时,我偶尔一回头,竟发现一个女孩正愣怔怔的出神瞅着我,那双眼睛闪着明亮的光,我被瞅得难为情,便赶紧跑出门外。到了院里,竟然还觉得背后仍旧有些异样。
太阳真好,四月的太阳映得小院一片辉煌,大丽菊正开得血红,几只小蜜蜂撅着屁股拱进花心里繁忙,院子里有一株弯枣树,树丫上两只斑鸠咕咕地叙着情话。自从村子划归城关镇,自从土地上垒起了那些扁方圆正不一的楼台,我再也没有见过这种仁义可爱的小鸟了。一见到鸟就止不住手痒,我突然恶毒地想到我的鸟枪、或者那把新做的弹弓,我曾经用它一口气打下四十二只麻雀,炒了一大盘子。那个香啊,绝了!差一点超过李小丽送给我的香片。瞧,我这个混蛋怎么又提起了李小丽。为了甩掉我对李小丽的情思,我忍住馋,不再去看弯枣树上情切切意绵绵的斑鸠。走到墙角那棵刺梅旁,我扶起了一枝将要折断的花盘,从地上拣起一小截塑料麻绳,轻手轻脚地拦在另一枝花茎上。完了欣赏自己的杰作,轻轻地吹起口哨,突然意识到是在黑妹子家,便嘎然而止闭上了嘴,很不好意思地朝墙根溜过去。墙上有个一尺见方的小木窗,我在小木窗前一过,我的天,又见到了刚才那双眼睛!刚一接火,我就差一点弄懵了,真见鬼!她为什么老是这样瞅着我?乡里人少见多怪,眼珠儿不转圈,难怪城里人都这么说。
饭后,我们终于要告辞了。七大娘说还有些琐事需多住二天,我便逃也似的出了门。看得出,黑妹子特想送我,无奈七大娘连说:“免了免了!”我走了老远,还望见黑妹子站在弯枣树下土门楼旁,呆呆的象尊泥塑。我不敢回头,我害怕那目光,那眼神。我突然觉得黑妹子给大嘴做老婆有些可惜,而大嘴摊上这样目光的女子是福是祸也难说。
五
唉!你说什么样的瞎子气不毁眼哪?等我急匆匆地赶到村外苗圃那片杨树林子里,大嘴正睡得象死猪一般。离老远就听到呼噜声震天响,汗水把衬衣都浸湿了,紧紧地裹在肌肉上。解下来的裤腰带,一头拴在脚脖梗上,一头拴在车轱轮上。“大嘴!嘿!”我喊了几声,不应。便又踢了两脚。这个黑红汉子连身子都没翻一下。依旧是四肢伸展,依旧是鼾声如雷。我顺手掐来一根细棍,插在大嘴鼻孔里,轻轻拈动打着转,大嘴微微摇头,禁不住扑通扑通两个震天撼地的喷嚏。这才睁了睁惺松泛红的睡眼,骂道:“娘的!”
“起来!”我朝他大腿就是一脚,“南柯一梦,可交什么桃花运?”大嘴定神辨出是我,腾地翻身跃起,哗啦一声,拽倒了自行车,两条裤管嗖地滑落到脚脖子上。这个呆子竟连条短裤头也没穿,那身子挺瘆人地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哭笑不得,弯腰解去车轮上的裤带,这个蠢货,系得净是死疙瘩,长纱布带捆了一道又一道,越急越是解不掉。我只好从腰间取下水果刀一一地割掉了,又一一地拴起来。大嘴拍着腰上系得大疙瘩连小疙瘩的带子,咧嘴直笑说:“好玩好玩,真新鲜!”我指着他的裤腰问:“你那裤子上的挂钩扣子都去哪里了?”他说:“那日吃得太饱,一抱水泥包全给挣脱了!”“唉,你也真是,睡的这么死,拴个带子做什么用,连你一块扔河里都不知道!”见我着真训他,他便嘿嘿傻笑说:“谁扔我做什么?能抱动我的还不多呢!”我苦笑了一下,不再说什么了。
我们俩往回赶,同骑一辆车。
路上,大嘴问:“大全哥。”
“嗯。”
“看到了吗?”
“看到了什么?”
“那个女的!”
“嗯,看到了!”
“怎么样?”
“谁知能配上你不?”
“大全哥,你又要逗我了!”
“逗你啥?配你是绰绰有余呀!”我一只手背过去,拍拍大嘴的屁股。大嘴美的直抖擞,车头乱拧,差一点将我俩都甩到路边的灌溉渠里。
“爹说,今个儿交给一千五百元见面礼,送一辆自行车,全都不做数,是赏给她老头的,她的礼物另买。要多少给多少,不还价!”
“你怕什么,二叔抠了半辈子,有的是大票子!”
“大票子也是不好挣呢!我爹常熊我,说,钱难挣,屎难吃!”
“花钱却是容易得很!”我说。
“哎,那女的给你说话了吗?”大嘴问。
“废话!我是送礼的,给我有什么话说!”
“我以为她和你该说几句小话呢!”
“你少出愣气,我可是她的老大伯哩!”我用力地捶他的大腿以示警告。
大嘴终于不出声了,车子蹬得飞起来。链瓦咣啷咣啷直响,挺有节奏。
四月的原野真迷人。
那双眼睛真吓人。
已能望见县城了,电视转播塔顶尖尖地在太阳底下闪着白光。
我的驴子该饿了,我仿佛听到了它咴咴的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