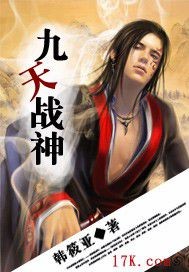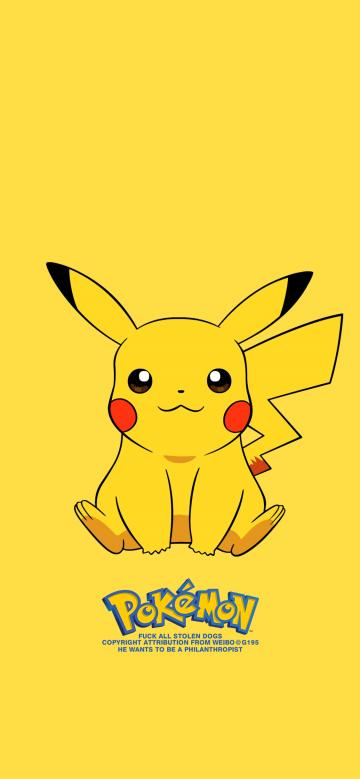盛安仍严厉地批评了黎江北。
黎江北跟楚玉良刚一吵完,楚玉良就跑到政协向冯培明告状,正好这两天冯培明正为别的事闹情绪,楚玉良添油加醋一说,还把黎江北跟吴潇潇的事夸大了几倍,冯培明就不能不管了。于是冯培明去找盛安仍,问调研组是不是没事做,如果没事,就让黎江北回江大,安心教书,别打着调研的幌子尽干些不着调的事。
“你有什么理由跟他吵,跟他闹?”
“他滥用职权,打击报复。”黎江北固执地说,本来他还想检讨一下自己的行为,一听楚玉良找冯培明告状,情绪就又激动了。
“怎么滥用职权,怎么打击报复?难道一个党委书记,变换一下下面同志的工作都不行?”
“问题没这么简单,他掉换的是强中行。”
“强中行怎么了,强中行就不能掉换,他比别人多长一个脑袋?”
“这……”黎江北让盛安仍问得张口结舌,在盛安仍面前,他的反应速度远没在楚玉良面前那么快,半晌,他小心翼翼道:“首长,问题没这么简单,背后有原因。”
“什么背后不背后,一件很正常的事,你们为什么要想得这么复杂?还有,他是党委书记,你找他大吵大闹,本身就是错误的。你难道不懂组织原则?凡事应该按程序来,这么简革的道理也要我提醒你?”
“首长……”
“不接受是不是?批评错了是不是?特权思想要不得,莽撞行为更要不得,你这样一来,会给调研工作带来更大阻力。我已代你向培明同志作了检讨,你要好好反省,必要的时候,要向政协作出检讨,委员不是到处找人兴师问罪的。”
黎江北不说话了,盛安仍这番话让他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他也很懊悔,那天怎么就那么冲动呢?思来想去,还是长大搬迁的事在起作用,楚玉良至今不同意他提出的方案,他去长大这么久,一件实事也做不了,怎么不急。
盛安仍接着又指出他最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浮躁、急于求成、感情用事、个别地方过于偏激。
“认真想一想,这些问题在你身上有没有?光有激情不够,工作得踏踏实实去干,矛盾得一步步解决,遇到问题就急、就发火,说明你对解决问题缺少办法,更缺少信心……”
黎江北让盛安仍批得心服口服,他向盛安仍作检讨,盛安仍道:“检讨就不必了,能汲取教训就行。对了,长大搬迁这件事,你就不要管了,建议和方案都已提交有关部门,别人做的事,你我就不要抢功,我们毕竟是调研组。”
黎江北一愣,盛安仍怎么现在变得如此谨慎?
“首长……”黎江北欲言又止。
盛安仍依旧板着脸:“黎委员,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调研组的同志都希望你能冷静,能顾全大局。”
“我怎么就不顾全大局了?”黎江北忽然觉得有些委屈。
盛安仍并没给他争辩的机会,继续正色道:“不只是你,还有党校林教授,最近你们火气都有点大,这样不好,干工作嘛,还是心平气和好。还有,任何时候,都要以大局为重,以整体为重,切不可因小失大。”
这话让黎江北似有所悟,盛安仍这样说,分明是在提醒他,省委或者是调研组正在从大局上着手,怪不得楚玉良现在有些着急呢。
他没敢将心里的疑惑问出来,只是机械地点点头。盛安仍接着道:“吴校长已经回到了长大,火灾原因已查清,她最近情绪不好,抓紧做做她的工作,让她振奋起来。”
“这……”黎江北再次犹豫起来。听到这个消息,他本该高兴才是,可不知怎么,楚玉良那番话忽然在耳边响起来。
吴潇潇的情绪果然很低落。
这是八月下旬一个光线暗淡的下午,连绵的阴雨将金江的天空染得一派迷蒙。虽是盛夏,空气中却裹着一丝凉意。
位于长江边坝子口的江都花园,向来被认为是富人居住区,吴潇潇在这儿拥有一套200平米的住房。父亲死后,她将父亲在金江的居所变卖,在这儿新购置了一套房。因为她怕父亲失败的阴影纠缠她,更怕沉溺在悲伤中无法自拔。然而,换房无法把一切都换掉,住到这儿以后她才发现,思念是一头顽固的恶魔,越是想驱走它,它在你身体里盘踞得就越久。
吴潇潇轻轻合上影集,她捧着父亲的照片,看了已有两个小时,窗外光影的变幻中,世事在变,她的心事也在变。
火灾事故调查小组经过一轮接一轮的调查和取证,昨天终于作出结论,发生在长江大学的火灾,确系电路起火引起的,调查小组排除了人为纵火的可能。跟她一同接受调查的6名师生先后回到了长大,可长大在哪儿?
一想到这些,吴潇潇的双眼再一次被泪水覆盖。
她现在是越来越脆弱了,越来越经不起风雨,刚回国时那个意气风发、满脑子都是幻想和希望的女强人已经不见了,她越来越像个饱经风霜的小妇人。
她对自己好失望。
门铃一次次被摁响,手机已响了无数遍,她懒得起身,懒得接听,懒得再听别人那些毫无意义的劝解和鼓励。没有人能帮得了她。
这是一场持久的消耗战,调查也好,取证也好,貌似合理的一次次问话,无不是在消磨她的意志,摧毁她的信念,目的,就是让她不再对长大抱有信心。难怪一同接受调查的副校长要冲他们发火,要把一肚子的不满和牢骚发泄出来。吴潇潇忍不住又想起了调查期间一次别有意味的谈话,找她谈话的,仍是那位领导的秘书。
秘书兜了一个老大的圈子,最后才把话落到实处:“江北商学院可以赔偿你父亲的损失,双方纠纷可以友好解决,但你必须承认,这是一起合同纠纷,不牵扯别的。”
吴潇潇困惑极了,她不是早就屈服了吗?早就不再主张什么权利,甚至那些损失也不抱追回的希望了,他们怎么还不甘休?
秘书接着又说:“其实你也是被人利用,想想看,那个李汉河,还有黎江北,他们帮了你父亲什么?什么也没帮。你父亲曾经三番五次请他们为长大出谋划策,他们都冷漠地拒绝了。现在他们为什么要跳出来,居心不良啊,他们是想借你或长大,达到他们的目的。”
不是调查火灾吗?这些事跟火灾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一次次提出来折磨她?
过了两天吴潇潇才听说,戴在长大头上的“紧箍咒”取消了,原来被有关单位收回的权力又落实到长大身上,长大又可以自主招生自主申报专业了。
但她高兴不起来,想想这两年的周折,想想这两年经历的一切,她就怀疑,谁能保证不再发生这种出尔反尔的事?
她打开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长大发生火灾前她委托一家评估机构做的,她想把长大的资产评估一下,如果有可能,她想给长大重新找个婆家,最好能一次性将它收购掉。两年的实践表明,她不是一个办学的人,父亲这项事业她继承不了,更无法将其发扬光大。她努力过,奋斗过,挣扎过,但她失败了,按商业场上的话,这次,她输得很惨。
她已委托一家中介机构,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听说万氏兄妹有这个意向。她现在已不在乎对方是谁,只要能替她把这个包袱卸掉,她就感恩不尽。
她怀念香港,怀念过去的日子,她想,就算把长大全部扔在江北,一无所获地回到香港,父亲也不会怪她。
吴潇潇的泪水再一次抑制不住地流下来。
又是一小时后,外面响起轻轻的叩门声。吴潇潇犹豫了一会儿,走过去打开门,她原以为是保姆,自从她被调查组带走后,保姆算是放了假,昨天她打了电话,让她今天晚些时候过来。开门一看,却是满头银发的副校长。
这位副校长是父亲最好的朋友,父亲到江北第一天就跟他在一起,这些年,为父亲,为长大,他真是呕心沥血,无怨无悔。想不到,调查组竟把怀疑的目光也投向了他。
吴潇潇感到深深地对不住他,对不住啊——
“快请进吧,老校长。”
老校长站在门外,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局促了半天,他重重地叹了一声,从包里掏出几页纸,递给她,一转身,快步朝楼下走去。
吴潇潇喊了一声,老校长生怕她要追出来挽留,下楼的步子比年轻人还快。
吴潇潇一头雾水,老校长的脚步声消失后,她才猛地记起手里还有几页纸,打开一看,她傻眼了。
老校长递上的,是一份辞呈!
老校长之后,又有五位教师提出辞职,尽管还在放暑假,这消息还是惊动了高层。李希民第一个坐不住了,跑来找吴潇潇。吴潇潇显得很平静,跟几个月前相比,她老练了许多,再也不会为一件小事变得焦躁不安了。面对李希民一连问出的几个问题,她淡然一笑,用沮丧的口气道:“李厅长,这些问题,你真不该问我,我自己也很糊涂。”说着,伸手捋了捋头发。
李希民发现,吴潇潇的发型变了,跟刚到江北时相比,她的发型越来越保守,越来越没个性了。是否这也意味着,两年多的磨炼,真把她的心劲儿磨平了?
“吴校长,别灰心嘛,出了问题不可怕,我们尽力解决就是。”
“解决?”吴潇潇苍凉地笑了笑,“那好,问题都摆在这儿,你李厅长解决便是。”说着,吴潇潇手一扬,刚刚应聘来的秘书便抱来一大摞材料,都是这些日子教职员工写来的。有催促落实工资待遇的,有催促落实住房的,有过问职称评定的,当然,反映最集中的还是下学期到哪儿上课,总不能把学校搬到广场上吧?
李希民随便翻了几页,这些问题不用翻,全在他脑子里,讪笑道:“都是老问题了,不好意思,我这个厅长不称职,没能把工作做好。”
“别,李厅长,这么说我担当不起,是我无能,父亲原本指望我能扛下来,谁知才两年,我就连大本营都丢了。现在好了,我认输了,我扛不动了,因为输或赢结局都是一样的。”
“什么意思?”李希民惊愕地问。
“曲终人散。”吴潇潇丢下四个字,起身来到书架前,本是想拿一本棋谱,想了想,没拿,转身走向内室,半天,从里面走出来,手里多了样东西。
李希民一看,差点惊得失声叫出来。吴潇潇手里拿的,竟是一件陶器,猛一看,跟他送给盛安仍那件一模一样。
“怎么,厅长对陶器也感兴趣?”
“不,不,我对它一窍不通。”李希民连忙否认。
“我马上要回香港了,这是我来时朋友送的,厅长如果不嫌弃,今天我就把它当礼物送给你。”
“太贵重了,不敢收。”李希民有些慌乱,生怕吴潇潇真把这陶器送给他。他脑子却在飞快地转动,吴潇潇拿出这件陶器,到底目的何在?
“贵重?看来李厅长真是对陶器不了解,这不值钱,仿的,不过仿得真,拿到市场上,没准儿就当真货蒙人了。”
李希民的脸色在急剧变化,一会儿白,一会儿红,额上已有细密的汗珠渗出。没人知道,他送给盛安仍的那件陶器,也是别人送他的,当时并不知道它来自哪里,是真还是假,到底值不值钱。收了便一直放在办公室,再也没碰过。盛安仍带着调研组来到金江,有天夜里他去拜访,心想怎么也得带件见面礼,原想拿幅字画的,一想到孔庆云,忙把这想法压了回去,后来又挑了几样,都觉得不合适,思来想去,忽然就记起盛安仍喜爱陶器,还是半个收藏家,没再犹豫就带了它。谁知送出不久,就听说春江那边出了陶器案,还牵扯到两条人命。这两个月,一想到陶器,或者一听别人提到陶器,他就紧张,就出汗,生怕那件陶器就来自春江,就来自那个工地,如果真是这样,他可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送他陶器的不是别人,就是冯培明儿子在香港的合伙人,一个叫阿朱的古董商,人称“四老板”。
“不说陶器,不说陶器,吴校长,你刚才说要回香港,不会是真的吧?”李希民忽然有些担心起来,至于具体担心什么,他也说不准,但这种感觉很强烈。
“多谢厅长关心,香港那边的公司要重组,我不能不去。”吴潇潇没说假话,香港吴氏企业真要重组,她已接到董事局发来的信函,后天就动身。
李希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吴潇潇不会一去不复返吧,要不然,她怎么会对教职员工接二连三的辞职无动于衷呢?
李希民没敢在吴潇潇办公室多滞留,如果吴潇潇真的一去不返,后果将不堪设想。别看吴潇潇损失了几千万,但她留给省教育厅的将是几千名学生。这些学生哪里去,怎么向社会交代?这可是一所大学啊,不是一家幼儿园,说解散就能解散了。何况,就算吴潇潇不再回内地,一样可以在香港打官司,商学院欠她的钱,还有因违约造成的损失,一分也跑不掉。
高啊,相比两年来她做的种种努力,这步棋,才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