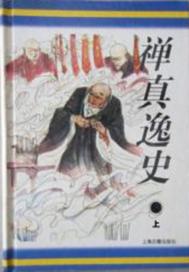商尹君的名头玉染不是没有听说过的,应该说,哪怕那人仅仅只是出现在传闻之中,也足以让她如雷贯耳。
那是一位传说中在三十年前德才兼备,聪慧冠绝之人,也是当时唯一一位受得百姓和主君同时极为欣赏的太子。
三十年前还不曾有明戌皇朝,但整个疆域上也不单单只有四国。
而商尹君南宫和裕则是那时商国的储君,也是现今商君南宫翎父亲南宫燕的长兄。那时的南宫和裕明明还未即位,却已是被人以商尹君相称,可见他的声望究竟有多高,一如当下的玉染一般。
只是,当时的商国内政同样混乱不堪,其三弟南宫燕同样想要一争储位。而朝内分为两派,拥护商尹君者居多,可也有部分人支持行事果决的南宫燕。南宫燕一派的人认为商尹君虽说有才,可却在有些问题上优柔寡断,太过感情用事,不适宜作为一位决策之人。
两边一直相争不下,最后还是当年的商君最后决定将传国的帝印玺交到了商尹君的手中。商国的帝印玺是历代商君继任时所需要的,并且整个商国上下都认定只有持有帝印玺的人才可以坐上商国主君的位置。也就是说,谁拥有帝印玺,谁就可以成为商君。
南宫燕以及他那边的人知晓事情不妙,已经没有了回旋的余地,于是暗中策划了谋反的计划。当年的商君发现了这件事,也知商国的不少势力都已经被南宫燕的毒辣手段给控制在了手下,于是只能偷偷让商尹君离开。
商尹君万般不舍,却只好带着帝印玺连夜逃离了王宫。最后在兵刃交戈之间,谁都不知商尹君到底是活着离开了,还是死在了谋反的战火之下。
而南宫燕即位之后,便自此昭告天下说商国朝野之中出现叛徒,意欲谋逆,致使商尹君至今失踪未归,连同商国帝印玺也同样消失。
没有了帝印玺,就算再怎么有人拿它说事儿,那也没有用了。
“是啊,知道旷鸿掌门就是商尹君的时候,我也讶异得很。不过父亲说他当年与商尹君有些缘分,而后明明知晓内情,却已经没有机会言说了。”夏侯央叹息道。
“如若你父亲说了,那可是满门遭殃的事情。”玉染不免提醒道。
玉染一直都觉得昊天宗的掌门旷鸿是个挺难测的人,而且她也猜想过旷鸿和商国的王室或许沾些关系,但她倒是没想到旷鸿居然就会是当年名动天下的商尹君南宫和裕。
那这么看来,之前旷鸿交给她的印玺应当便是那帝印玺,而那封她至今未拆的信中所写的内容就更加值得斟酌了。
“没想到都已经三十年过去了,居然还有人重新将主意打到商尹君和帝印玺的头上。”夏侯央有些惋惜道。
玉染眼帘微垂,薄唇一勾,道:“这是正常的,他们如今已经动不了身为昊天宗之主的商尹君,并且也心知商尹君没兴趣掺和进他们的事,所以自然不会自找麻烦地再去难为他。但这帝印玺嘛,那可是商君权利的象征,谁都是想要得到的。”
昊天宗名闻天下,昊天宗掌门旷鸿的名字世人里只要有些名头的都会知晓。而且旷鸿的武艺内力一直都是闻名遐迩的,就算你派出几个人去暗中查探,也得不了丝毫好处,反而会遭了昊天宗的敌视。昊天宗之徒都是四海天下的名仕,要是真的明着得罪了,哪怕是商国的夏侯家,那也是无力直接抗衡的。
玉染也没弄懂商尹君究竟是个什么想法,莫非商尹君当真认为她玉染就是个谦谦君子,能够得帝印玺而心不乱吗?
这可不是。
商尹君既知她是颛顼染,又知她是赫连玉,她这勃勃野心都已经昭然若是了,又岂能对帝印玺不动心思呢?
不过商尹君愿意在十几年前收容袭为徒,想必就是看中了容袭的治国之才。而如今又将帝印玺交给玉染,应当便是觉得玉染的身上也有他看重的地方。
不过玉染一直将自己当作个没心没肺之人,于是那时的商尹君也就索性同玉染道愿不愿意和他做个交易。
商尹君给玉染以武功和帝印玺,换以玉染一句承诺保天下太平,这是商尹君的本愿,所以他觉得不亏。而玉染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她也觉得不亏。所以两人便达成一致,没有什么好辩驳的地方了。
“方才叔父同我说,帝印玺如今应当是在赫连玉那儿。可我现在不过是个典客而已,就算真的能和赫连玉说上话,也不过是只能聊上两句宁、商两国之间的……宁商两国的关系……唉,真是不说也罢。”夏侯央说到最后,只能苦笑着摇了摇头。
玉染只是略一思量,便笑出了声,她赞同道:“确实,这次本是华、商之间的联合,至于赫连玉,不过是恰巧陪同而来罢了。若非江家压上头来,恐还不会出面。至于宁国与商国的关系——诚然一言难尽,一言难尽啊!”
“姑娘觉得慕容袭和赫连玉二人究竟是否同传闻中说得那样早已分裂?毕竟之前那场华、宁之间的战事,确实闹得不小。”夏侯央认真考虑着问道。
玉染扬了扬眉,问:“若他们早已分道扬镳,那如今二人又为何会一道同行?”
夏侯央思讨了片刻,道:“或许是为了给他国制造一个假象,让人觉得华与宁皆是坚不可摧?不是世人都说赫连玉的心思莫测,叔父也道畏惧于赫连玉,觉得赫连玉是满口谎言,无法探究。所以也有可能是赫连玉为了宁国的利益与曾经喜欢过的慕容袭做了个交易,他们说好了一道来,就是为了给商国一个下马威。啊……抱歉,我忘了姑娘现下的情况。”
夏侯央知晓女子如今是在帮赫连玉或者慕容袭其中一人做事的,他说这些委实是不应当。
“不要紧,我也只是接了个生意罢了,对于客人背后到底在想些什么我都用不着管。”玉染笑着摆了摆手。
“姑娘身为红月阁中人,不用受他人限制办事,真是让央羡慕极了。若我有一日也能够不用再身处于如此囹圄之境中,那想必也能快活不少。”夏侯央说道。
“你觉得商国于你而言是个牢笼?”玉染的目光落在夏侯央面上,她的语气很温和。
夏侯央闻言,无声一笑,却是沉默了。
玉染也是温温一笑,一手轻轻抚着窗框,修长的指尖蜷了蜷,道:“天下何其大,可处处是牢笼。身处低位时,牢笼压身,无法喘息;身处高位时,牢笼加身,难以回头。其实都是一样的,不过是后者比前者多了几分选择的余地罢了。但想来,你现在虽然将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但那一切只是权宜之计。你想要走上后者的路,很累,也很难,而且少不了给自己添堵。”
“给自己添堵?”夏侯央拣出了这个词来。
玉染轻笑着说:“恩,添堵。比如受尽他人非议,比如手上沾着看不见的血,比如你觉得自己的心越来越麻木。”
“姑娘……”夏侯央蓦地看向玉染。
“怎么了?”玉染偏了偏头。
“姑娘会这么说,莫非姑娘有经历过?”夏侯央好奇。
玉染眼底一深,唇角含笑,她极为认真地回应道:“赫连玉经历过。”
“这相当于没有回答吧?”夏侯央无奈失笑。
玉染耸了耸肩,没有应声。
她怎么就没有回答?她分明清清楚楚地回答了夏侯央才是。
赫连玉经历过嘛,她就是赫连玉啊。
“唉,说到底,一切还是得先从怎么解决叔父的问题开始想起……”夏侯央揉了揉额角,头疼不已。
玉染低笑一声,不怀好意道:“解决你叔父的问题那多难啊!不如先从如何解决你叔父开始想起?”
夏侯央被玉染的话又给吸去了目光,他盯着玉染晌久,最后无奈笑道:“姑娘……姑娘可真是语出惊人啊。”
“我不是在诓你,我是认真的。”玉染眨了眨眼道。
就是知道姑娘你是认真的,所以我心里才更慌啊!夏侯央嘴角扯着笑,心里不禁抖了抖。
“我们还是一步一步来吧。”夏侯央说道。
“跟你说了,你光在心里想,却没有做得胆量是不行的。这样下去,就算你有一天真的扳倒了本家,那该是何年何月的事情了啊?”玉染一手撑着头,半是笑意地说道。
“我有的。”夏侯央反驳道。
“哪里有?”
“……真的有。”
马车帘子忽然被掀起,驾着马的夏侯央的贴身侍卫浮飞白一脸无奈地转过头对他家公子道:“公子,求您别再说了,您越说属下越觉得您没有底气了……”
“专心驾你的马车去。”夏侯央恼道。
“是,是,属下知道了。”浮飞白一脸无奈地摇着头放下了马车帘。
玉染笑了,“你的贴身侍卫真有意思。”
“他就从小就这个样,喜欢挖苦人,我已经习惯了。”夏侯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