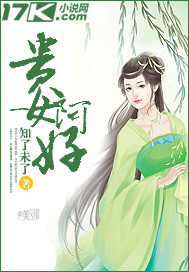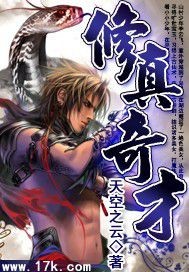夜玘桃不知道,当时,妫翼在斩断二人之间的绳结时,是不是又令妘缨想起了,那夜湠漫顶,姬雪灰飞烟灭的情形。
但是,她清楚地知道那种被人抛下的感觉,真的不好受。
大战开始后,妘缨凭着心底这股对妫翼的气愤,一路砍杀,甚至在商德邻选择弃城逃跑时,独自一人骑着马从城西门出,追了十余里,险些追到了余陵,才将商德邻就地斩杀,拖着他的尸身,回到了潼安城。
黎明时,战火才渐渐消去。
亏于这场征战的速战速决,使得城中民众大部分得以保全,除却城墙轻微受损,城中房屋并未遭受重击,得以完好保存下来。
妫翼将城中唯一一处神殿作为指挥大营,其余空闲房屋,先以安置民众为主,余下作为兵将休息之所,如房屋不够,可在临靠神殿四边的街巷内安营扎寨,决不可使民众流落街头。
她命百里垣壹在不惊吓民众的前提下,在城中继续搜寻混迹的梁军,将其等一一寻出,关押于马厩旁的土楼之中。
妘缨回到潼安城时,城内已是井然有序,甚至火营的炊烟冉冉,饭香味外溢。
可她现下并无心情吃饭,听闻妫翼在神殿,便径直寻了过去。
两人都才各自忙完,来不及洗去身上的血迹,虽然心里清楚血迹大约并非出自己身,却仍旧异口同声地问询道:“可有受伤?”
妫翼心中有歉意,又在方才向她禀报城内伤员之事的夜玘桃口中,得知姬雪与妘缨为护佑彼此安妥,而相互诓骗的往事时。
她的心底愧意加重,愈加歉疚。
她又道了一句:“对不起。”
可她仍然觉得自己并没做错,又在对不起之后,多加了一嘴:“我并不想让你受这帮乌合之众的胁迫,所以一开始并不打算将你牵扯到这场征战之中。”
若是妫翼不填这后面一句,妘缨见她疲惫之姿的歉意,已然心软了。
“牵扯?”妘缨委屈地嘶吼吓得妫翼一个激灵。
“饶了这么一大圈,你现在和我说,不想将我牵扯进去?”
妘缨看向妫翼的眼神,仿若是再看着一个刚被确认为有严重癔病的人一般,不可置信。
“若是怕我牵扯,为何逐除朝见天子时邀我共进安阳,为何要在千面阁的饮宴上跳出来维护我,为何当初西去晋国复仇,又派人来通知我做接应?”
“若怕牵扯我,当初你在安阳,从那场噩梦中新过来时,便不该决定去宋国救我,而是让那样一个我,烂死在天阙台一了百了。”
妘缨头一次在妫翼面前失控,甚至有些无理取闹。
妫翼砸吧砸吧嘴,当真不知该说些什么。
她想起小时候,每次惹她生气时,服个软,她便不气了。
于是,她站起身,走到妘缨身旁。
她猛地抱住妘缨纤细的腰身,侧脸紧贴着她的心口,细细地说道:“对不起,骨碌,你知道我关心则乱时,向来是不带脑子的,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还不行么?”
妘缨方才烧得沸腾不已的心火,瞬时成了温茶的文火,温度尚好,且暖意融融的。
她哽咽起来,却不愿让妫翼看到她的眼泪,顺势按住了妫翼欲将抬起的头。
“你也应当知道我,既然选择来你身边,便不惧怕他们的威胁,即使那商德邻认出我,即使大周封梁国的大公子为梁公,楚国将他送回了西梁。”
“若是我无法破解这些个诡谲的计谋,早前那些风雨,便都是我白白经历了。”
妘缨既然想清楚昭明太子的手段,也敢明目张胆地来潼安支援妫翼,便早已想好了应对之术,更不可能再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妫翼安静地趴在妘缨心口,她听着她坚实地心跳,不知怎地,感觉那个叱咤风云般的人,忽而变得多愁善感起来。
相隔开着这些年,两个人都好像没变,可又好像无声无息地改变了。
妫翼的肚内传来不适宜的叫响,空旷的殿内,尤甚清晰。
妘缨这才破涕为笑,忙唤门外守兵传饭来。
今日火营做了菜团子与豚骨汤,这菜团子是将黍碾成粉,与葵糅杂,捏成团子,蒸熟而成。
妫翼下令火营在行军所准备的饭食,上下一致,即便是食不求甘,也至少能鼓腹饭饱。所以她们每日所食的饭食,皆与众兵将的一模一样,那一大盆的豚骨汤已叫妫翼颇为满足,菜团子说什么也吃不进了。
恰逢殿外有人来禀报,说在西城的城墙根儿下发觉一位耄耋欲带着十余幼子出逃,在被百里垣壹将军盘问后,得知老人的身份是东楚三朝老卿孋老丈,便将其送来神殿,由妫翼来发落。
妫翼斜倚着凭几,回想着曾在何时何地听得来的孋家之事。
往往越是在那处栽了跟头,她越是记的清清楚楚。
楚国的翠缥是她的伤心地,所以她记忆才尤为清晰。
这孋老丈归家种田后,带着曾孙前去翠缥,并在翠缥办立私学,收了些许当地楚民孩子为弟子,也包括那高高在上的翠缥郡主。
妫翼立直身子,随即叫妘缨先下去休息。
妘缨闻声,却一动不动地跪坐于一旁。
妫翼见状无奈地摇了摇头,便叫人将孋老丈带了进来。
孋老丈身着青灰的衣裳,发髻霜白,身形纤弱,颇有仙风道骨之姿。
妫翼以为他是一人,却瞥见其身后还跟着些许面容灰锵锵的幼子。
幼子的年岁大约在四岁到十岁不等,女娃娃偏多。
孋老丈拜国公之礼于妘缨,再拜侯爵之礼于妫翼。
妫翼不禁心里念叨着老顽固。如今除却天子之礼大有不同,九州侯爵公卿,皆为同礼。
孋老丈所拜之礼,多见于周殷王的诸侯归顺时期。
“而今贼首已死,愿请陈侯许我等归家。”孋老丈从容而语。
“家?”妫翼笑道:“这里不就是孋老丈的家吗?”
孋老丈一怔。
“楚公将你们送来潼安,便是想叫你们于此处安家,既是君意已决,孤怎好辜负呢?”妫翼的言外之意在于提醒孋老丈,潼安本是陈国之城,是因楚国的不义之战而陷入混乱,多少陈民流离失所,失去家园。而造成他们背井离乡,远离故国家园的人,并不是妫翼。
孋老丈自知理亏,故而道:“君主间的不义之争,多为谋私,祸不及百姓,陈侯贤明,必不会为难这些幼子。”
妫翼冷笑一声:“老丈此时才想起孤的贤明,是不是有些迟了。”
“贤明与否,多半是老身的恭维之话,九州上可称为贤明之君的人,比比皆是,可当真能做贤明之举的,却是凤毛麟角。”
“为君者,肯为百姓着想,愿为百姓着想的,岂会因老身的一句恭维就能改变自身本质的?”孋老丈豁达地笑道。
他真诚地将妫翼捧上高座,既不强硬,也不怯懦。
“如此说来,身为楚国三朝老卿的孋老丈的本质是什么呢?”几经世事无常,妫翼颇为擅长与固守成规的老顽固博弈。
她甚是享受看到这些人手足无措,冲冠眦裂地模样。
“是为天下公的贤明,还是只管楚民活命的徇私呢?” 妫翼道。
孋老丈笑道;“老身不过一匹夫而已,所做皆为私,怎敢比天下诸公之贤,天命予我不过再多二三年而已,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无论老身处于何地,魂归故里,或客死他乡,总躲不过这一死,只是可怜这些年少孤儿,无人庇佑,终年兵荒马乱,着实不幸。”
妫翼倚着凭几,搭耸着眼皮,故意问道:“这样的话语,你同那商德邻讲,他可听你的,饶了这些少年孤儿?”
“商德邻怎与陈侯比,他过是流寇匪首,怎明白这世上的仁义贤明?”孋老丈说道。
“嗬。”妫翼冷笑。
“这世上懂得仁义贤明的,就必须要以德报怨,反而流寇匪首,仗着不懂道理,却能痛痛快快地屠戮报仇,这又是什么道理?”
“你身后的那些个年少幼子,哪个父母兄弟没有屠戮过陈民,又有哪个在长大之后,不会尊楚公之命,反过来攻杀陈国?”
妫翼抬起的眼眸中蕴藏着杀意,孋老丈甚是怕她即刻下令绞杀这些幼子,随即匍匐于地,道:“君命难违,他们也别无选择,更何况兵连祸结,也都是为了活下去,诸公不在意蝼蚁生死,怎又不许蝼蚁偷生?”
“既是选择舍生他人而偷生,便要想好因果报应,这世上总叫杀人偿命,天理昭昭,父债子偿。”
妫翼与孋老丈二人争夺到剑拔弩张之时,一只瘦弱且脏污的小手从几案下,伸了上来。
许是因年幼身形瘦小,妫翼并未发觉她的靠近,待她将瓮中的菜团子拿在手上,往嘴里送时,
妫翼才留意到,有个瘦骨伶仃,灰头土脸的小人儿正蹲在几案下,狼吞虎咽地吃着菜团子。
孋老丈身后有二三些许年岁较大的少年,她们轻轻地唤着小人儿回来,可那小人儿吃的正欢,根本没功夫搭理那些声音。
待她吃完手上的菜团子,再要去拿第二个时,一抬头,便对上了一双魅惑且冷峻的双眸。
她吞了下口水,不禁打了个冷颤。
可是她,并没有退后。
小人儿眼睛明亮,嘴角还挂着一小团菜渣。
“叫什么?”妫翼问道。
“小,豆子。”小人儿回答道。
妫翼听她说话的口音是陈民,便又从瓮中拿了一个菜团子放在她的手里。
“阿爹阿娘呢?”妫翼问道。
小豆子摇了摇头,一边大口吃着菜团子,一边道:“被他们带走之后,便没再回来找我了,阿爹让我跟着孋老丈,说孋老丈会带我去能吃饱肚子的地方。”
“我想着那些人是招儿姐的阿爹和桐哥儿的阿爹,我们刚被那大魔头抓来时,还是他们救了我们,给我们吃的填饱肚子,还送我们炭火取暖,所以,他们绝对不会伤害我阿爹和阿娘,我这才乖乖跟着孋老丈走了。”
随着小豆子说话,妫翼的双眸向孋老丈身后的少年扫过去,其中有一男一女闻此,忐忑不安地低下了头。
“可是我等了很久,阿爹阿娘都没有回来,招儿姐说,阿爹阿娘跟着临晩阿姐去了很远的地方,可能要等我长大之后,才会回来。”小豆子眼睛湿润,忽然觉得喉咙有些发沉,便缓缓放下了往嘴边送去的菜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