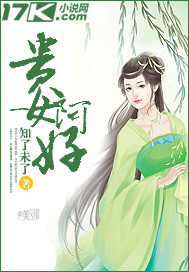如今身形早已是摇摇欲坠的百里肆哪还有余力与少公子吵嘴,还未等少公子走入长信宫,他便栽倒在地,不省人事了。
莘娇阳面露惊色,快步而去,将百里肆护在怀中,轻轻拍着他的侧脸,唤他名字。
可他双眼紧闭,毫无反应。
陈候见此,令身侧的宫人将百里肆送回上卿府,并随请医官一同回府为他诊治。
少公子看了一眼忧心忡忡的莘娇阳,便说道:“你若不放心,便也一起去,只是早些回来,我怕还有事情要劳烦你。”
莘娇阳满眼感激地点了点头,便紧握百里肆的手,离开了长信宫。
陈候告知少公子,绥绥已昏睡四日,身后的续命蝶已然完全呈现墨色,甚至看不出原先的翅膀脉络。
有关她背后那只续命蝶之事,是凤姬夫人讲与陈候听的。只是,他所知的续命蝶,是可以净化致命之毒的宝物,却不知在续命蝶离身后,宿主会魂魄灰飞烟灭的事情。
“乌头的毒虽然可被净化,可至少需要半月之久,这期间绥绥会因乌头的毒素产生错乱的梦境,若是她沉浸在这梦境之中,便永远都不可能再醒过来。”少公子不禁自嘲,仿佛每一次他的出现,都伴随着福祥公主中毒或是受伤,他内心百般地祈求,但愿下一次再见面时,不要再这般断人心肠。
“孤听闻这乌头是有解药的?”陈候道。
少公子摇了摇头道:“乌头的解药最快也需要三日才能配好,绥绥现下已然陷入了昏迷,怕是等不及。”
“所以,我需要用自身内力,将她体内的毒逼出来,在此期间,决不能有任何人前来打扰,否则我同绥绥可能会一同陷入梦境里,再也醒不过来,所以,劳烦陈候安排信得过的人来守门。”少公子说道。
陈候闻声,坚定地点了点头,道:“昭明君这般舍身为小女,老身必当亲自为昭明君守门。”
少公子将绥绥扶起来,让她依偎于自己的怀中。
“还有一事,今日是月圆之日,我体内的母蛊怕是会作祟,如若我在子时还未走出房门,请陈候尽快将我送去尔雅城,交给守城将军澹台不言。”
母蛊发作时运行真气,轻者损伤内力,重者怕是会真气逆行,经脉断裂。如今尔雅城澹台大伯和澹台不言在,若是他真气逆行,他们定然会想尽办法救他。
陈候放心地将福祥公主交给少公子,退门而去,便如先前所承诺,亲自守在前厅为少公子看门。
少公子见一切都稳妥了,便抬手将绥绥的寝衣退下。他见到在她背上,有一道浅浅的刀疤。
这刀疤是在雅安关前,为了保护他挨的那一刀。
少公子抬起手,轻抚她背上的痕迹,心里的痉挛更剧烈了些。
许是她缠入了梦魇之中,眉心紧缩,泪落眼角,却呢喃地唤着少公子的名字。
少公子将她的身子立直,运行体内的真气,将浑厚的内力,由几处大穴缓缓地度入她的经脉之中。
不巧的是今夜月满,有母蛊在少公子体内折腾,几经六七个来回,少公子深觉胸口如千斤巨石压迫,更觉体内真气已经耗尽了一般,衣衫被汗水浸透,印出坚实无瑕的身形
他调稳气息,遏制内力输送,再缓缓地张开眼。绥绥背上的续命蝶,已经从墨色逐渐变回成紫色,蝶上羽翅地脉络也清晰起来。
他放下心来,准备归息时,胸口猛然一紧,像是刺入了锋利的尖锐之物,一呼一吸皆是剧痛疼。
他身子使不上力,便往后仰了过去。
与他同时倒下的,还有恢复如初的绥绥,她安详地伏在他的胸口上,气息平稳,眉眼舒畅。他低下头,再度深情地望了她一眼,便眼前一黑,陷入沉睡。
待少公子醒来时,已经是十天之后,他身处尔雅城内的清华寺。他慢慢起身,调动起体内的真气来。
经脉顺畅,内力无阻,他能收放自如,便放下心来。
“公子醒了?”少公子闻声望去,却见鸑鷟端着木碗从屏风后走了进来。
“你怎么会在此处?”少公子问道。
“当日我见公子神情恍惚,便觉事有不对,于是跟在公子身后一同去了陈国,只不过我没有莘娇阳的通行令牌,所以耽搁了一点时间,等我到圣安之后,便在宫门口遇到了莘娇阳,她带我入宫后,发现公子昏死于床榻,还抱着人家肤如凝脂的福祥公主经脉逆行了。”鸑鷟将木碗里的汤药递给少公子,少公子一边喝,一边听着鸑鷟讲话。
待听到最后那一句话的时候,少公子将嘴中的药喷了出来。
“不过好在陈候并不介意,还打趣地要昭明君做他的小婿。”
少公子擦了擦嘴,将木碗还给鸑鷟道:“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胆敢打趣你家公子了。”
“公子既然涉险之前都与陈候交代了后事,还问我做什么?”鸑鷟耸耸肩,拿着木碗便要出去。
“这是谁让你受了气,连话都不好好说了。”少公子侧过身,倚着塌边问道。
鸑鷟背对着少公子没有说话,少公子见她的肩膀颤抖片刻,又抬起手用衣袂擦了擦脸。
看来那天晚上,他经脉逆行的一定很严重,否则鸑鷟不会担心到哭鼻子。
“你瞧我这不是好好的么?”少公子又道。
“麻烦公子下次冲动之前,想一想远在安阳的长公主,她什么都没有,就只有公子。”鸑鷟微微地俯了俯身,便跑出了屋子。
少公子淡淡地笑了笑,心里萌生暖意。
也是后来,莘娇阳告诉他,如若不是在赶往尔雅的路上,鸑鷟用血灵虫锁住少公子的经脉,少公子怕是早就经脉断尽,暴血而亡了。
至于血灵虫,是蛊女以血控制的一种灵虫,通常是用作制蛊时的引子,但有时也可作为蛊女的意识进行操控,只是会耗费蛊女体内大量的精血。
如今的尔雅,经由澹台不言的接管后,逐渐恢复的战前的模样。蔡国的国人皆是惧怕战乱,因而十分倚重澹台不言,甚至比以往还要积极地上交存粮,充作军饷。他们似乎知道,只要是澹台不言留在蔡国一天,那么楚国的铁蹄就踏不过来。
霍殇带兵前往蔡国另外几城平匪乱,至今仍旧未归尔雅城,如今蔡国百废待兴,还当真是一件伤神的事情。
楚军撤走时,一把火焚了尔雅城的蔡宫,屹立百年的富丽堂皇,便在这一把火中消失殆尽了。
如今的尔雅城墙上,昔日的满墙芙蓉花,尽是战火缭绕后的疮痍。
少公子坐在桐花台的软榻上,仰头望着正值时节的落花纷纷。楚人虽信鬼神,却也对佛道抱有敬畏之心,想来这尔雅城中,唯有清华寺和这棵桐花树仍旧是完好无损。
只是这庭树不知人去尽,今夏还发旧时花。
少公子不知怎地,胸中多有烦闷。他忽然就想起白老将韩子送回到紾尚阁后,与他离别时说的话来。
他说:“如今的蝴蝶谷,已是人去谷空,想当年君家选择避世,便是不愿意后世再尝别离之苦,君婀和公子还有君绫既然是自己选择了出世,那么老身便替你们守着蝴蝶谷,只是从今往后,前路漫漫,莫说后悔。”
少公子忽而觉着,他似是得到的权力越多,身边的人却越来越少。
恰逢时机,澹台不言拎着两壶酒坐在了少公子的身侧。
少公子接过他手里的酒壶,仰头便是一饮。
这酒味道辛辣,甚是热烈,一路而下,似是击破了少公子胸口中的烦闷,倒是酣畅痛快。少公子不禁又是仰头一口。
“昭明君可还记得当年在桐花台的比试吗?”澹台不言饮了一口叹道。
“怎么会不记得,只是可惜了叔姜,跟着那样一个君主,不值得他用命尽忠。”少公子依旧记着桐花台上,叔姜不卑不亢,刚直不阿的风骨。
“叔姜所守护的,非君王,而是身后的国人,他若倒下,国便亡了,所以即便是生命的最后,他以环首刀撑地,万箭穿心了,却不肯倒下。”澹台不言抬起手,接住一瓣正落下的桐花。
“你可愿为我而不肯倒下?”少公子手上的酒壶已是快见底,他双颊绯红,醉意朦胧。
澹台不言微醺地笑了笑:“早前这桐花台上,昭明君为保全我在师父面前的颜面,故意输给我,不如今日昭明君再同我比上一比,若是昭明君赢了我,我便愿以命相付。”
“我要你命作甚,不比不比。”少公子将酒壶内剩下的酒一饮而尽,而后靠在凭几上,赏起了落花。
蔡国初夏的风最是迷人,不热烈又不安静,能惊起落花,却又不割人脸颊。少公子闭着双眼听风,感受桐花散落的窸窸窣窣。
少时,少公子忽而听到长剑破风的声音,他张开双眼,瞧见澹台不言正在桐花台上挥着他的纯钧剑。
他的剑法不同于少时的青涩,极易让人看出破绽。似是历经了沙场征战,他的剑法变得坚韧有力,每一招直冲命门,每一剑攻无不克。
少公子兴致偶起,抽出腰间的含光剑,上前同他比划起来。
依旧同原来一样,少公子以含光剑缠住了澹台不言的纯钧,而这次,澹台不言并没有转动剑柄挣脱,反而以真气打入剑身,纯钧剑直直地朝少公子面门而去。
少公子不紧不慢地收紧含光剑,反手用力,将纯钧的剑身换了方向,朝着桐花树去了。
澹台不言平地而起,追剑而上,在收回纯钧后,俯冲而下,他一剑朝少公子劈去。少公子以含光接招,二人的剑气再次击落了树上的桐花,簌簌而落,如同冬日之中的白雪皑皑。
比试了一番后,依旧是难分伯仲。少公子此时酒醒,也比划累了,索性飞身上树,靠在树枝上不下来了。
澹台不言收回纯钧于剑鞘,而后也飞身上树,坐在少公子身旁。
“楚军已经发兵于陈国余陵,看来楚王从一开始,便是要将陈息蔡三国收入囊中。”澹台不言说道。
少公子靠着树枝远望,刚好能瞧见已经被烧成废墟的蔡国王宫。曾经的朱楼玉砌已是残垣断壁,曾经的美景良辰已是物是人非。
“如果你是楚王,你会在这个时机去攻打陈国吗?”少公子问道。
澹台不言垂眸思索而后道:“或许会,也或许不会。”
少公子勾着嘴角,淡淡一笑:“会,是因陈国早前内乱,如今政局不稳,君主权力被架空,刚好是出手的好时机,如若乘胜追击,给予致命一击,那陈国也同息国一样,土崩瓦解,大厦倾倒,不会,是因如今蔡国表面上看起来是被周王收入囊中,可暗地却是我屯兵之地,如我是楚王,应当尽快安排白素从息国攻来蔡国,将蔡国夺回,否则就算将陈国收入囊中,陈息两国之间还隔着蔡国,光看着这糟糕的版图就很膈应了,更何况还要屯兵,还要统治。”
少公子猜测的,澹台不言也都想到了,可这些只都是猜测罢了,是否为真,还需要观望一阵。
“可自从息国全境被楚国霸占后,倒是安静的很,尤甚是雅安关,看不到有楚军任何进犯的踪迹。”澹台不言问道。
“这便是最可疑的地方,蔡国以东是楚国,以西是息国,若是东西夹击而攻,蔡国全境即刻尽可收入楚国囊中,可偏偏为何要多此一举去攻打陈国?”少公子依靠在枝桠上,他大约能猜到楚王的计谋,可尚不确定陈国与蔡国的轻重。
“如今蔡国多乱之时,先暂且送澹台大伯和你的姐姐们远离此处,若是楚国出其不意地从雅安关攻过来,尔雅便不再安全。”少公子嘱咐道。
澹台不言垂下眸子点了点头道:“不如去安阳如何,父亲也说想见见小喜和成蹊。”
少公子侧过头看着他,温和一笑道:“而今安阳亦是多事之秋,我连自己的娘亲都护不住,更何况你这一家子,若遭人谋害,我岂不是罪孽深重了?”
不管澹台不言是否在试探他,澹台大伯几次救他的性命,一个澹台成蹊,一个澹台小喜便够了,他可不能让这一家人都去安阳冒险。
澹台不言没再说话,他低着头摩挲这纯钧剑,剑鞘上的花纹。
“不如送去齐国吧,有齐国君和你师父照应着,总比在此处颠沛流离要好。”少公子说道。
“若是有朝一日昭明君承大统,可否能使澹台不言的家人不再颠沛流离,能聚于一处,共享天伦。”澹台不言抬起头,看着少公子笑的有些苦涩。
少公子仰起头,胸有成竹地道:“那是自然,如若继承大统,执掌九州,我必将使九州百姓皆不再颠沛流离,聚于一处,共享天伦。”
“昭明君既有这般的雄心壮志,那么我愿为昭明君在征战之中不肯倒下。”澹台不言抱着纯钧剑,依靠在枝桠上,斜阳掠过他的双眼,发散着晶莹的光亮。
少公子望过去,忽而不觉得如先前那般孤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