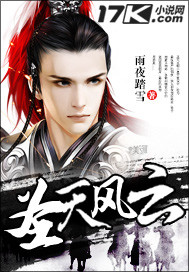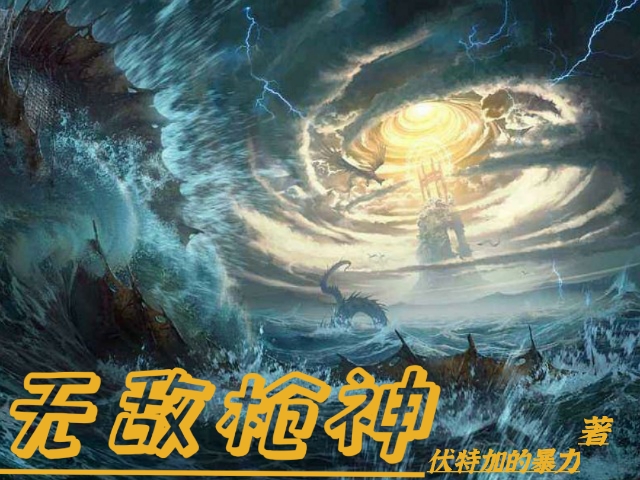宋老生虽然急于求战,而且被一帮坑爹的上司下属们折磨得欲仙欲死,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失去冷静,仍然按照惯例将斥候放出了十里。对于一支全部由骑兵组成的军队来说,十里的距离足够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对突发的敌情作出反应,想要伏击一支纯骑兵部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千难万难。
这一日他率军刚离开祁县县境,离着叛军的集结地清源还有四十多里,宋老生却一点也不急着赶路。这一回他放出去的斥候足有千余人,足以封锁前方的大小道路,使主力的行迹不至于泄露,他打算在清源城外十多里的一个山谷潜伏至日落,然后趁着暗夜偷袭一下叛军。这一招宋老生以前没少用,对付那些军纪松懈、缺乏弓弩的土匪流寇堪称百试不爽,就没失过手。而且据河东军送来的军报,叛军大概也就两三万人,能撑住他手下这些百战精骑的一次冲锋就不错了,就是不知道黑灯瞎火的能不能抓住那个杨玄感的亲儿子,就算抓着了又该如何处理?有屈突通的前车之鉴,宋老生也有些挠头,更感到无趣。
宋老生正在百无聊赖的信马由缰随着大队前行,突然看见远处有一骑快马卷起满天的尘埃向着他疾驰而来,宋老生的脸色不由得一肃,眼睛也眯缝了起来。他已经认出来人正是他派出去的斥候,而且背后插着三面红旗。
按照隋军惯例,前出斥候若无敌情须一刻一回报,背不插旗。如发现敌踪须立时回报,背插红旗一面。如遇敌军主力,但是敌军并未发起攻击或作出攻击的举动,则须背插两面红旗。要是遭遇敌军大举攻击或是发现伏兵踪迹就比较严重了,斥候不仅需要立即背插三面红旗飞马急报,还需射出响箭接力示警。要知道斥候前出侦察敌情可是有讲究的,绝不是一窝蜂似的只顾着往前边跑就行了,而是要梯次出发,并在每前出一段距离之后留人沿途驻守,待后续斥候赶到之后再滚动前进,以免齐头并进被伏兵一锅烩了。另外一个作用就是一旦前方有警发射响箭之后,后方呈梯次分布的斥候可以接力示警,以给主力部队更多的准备时间。可是这回就斥候背着三面红旗跑回来了,响箭呢?宋老生可是清清楚楚的记得那是一声也没听到。
这帮兔崽子们表现得太过分了!宋老生本就勃发的怒气再也抑制不住了,右手忍不住握住了腰间那把百炼横刀的刀柄。
能当上斥候的无不是精明干练之辈,眼神尤其要好使,哪有看不出老宋要拿刀砍人的道理?所以斥候离着宋老生还有八丈远就翻身下马,单膝跪地大声禀告道:“总管,前方十里外发现敌踪,但敌军举止甚是怪异,属下无从判断其意图,故此不敢贸然发射响箭示警,唯恐惊动敌军,只能来请示总管,请总管定夺!”
“哦?敌军是何方兵马?有多少人?骑步弓兵各有多少?领军之人是谁?举止如何怪异?”宋老生也很奇怪,但还是按照常规向斥候询问细节。
“这个……总管,敌军的旗号很是奇怪,属下无从判断是何方兵马。人数在十万以上,男女老少都有,却大都赤手空拳……具体情形还请总管前去一观,属下实在是说不清楚……”
宋老生越发奇怪,这个斥候跟着他也有快十年了,一向精明强干,今天怎么成了一个糊涂蛋?而且什么都说不清楚?可是接连几个斥候都如此说法,不但都请他过去看看,脸色还一个比一个怪异,宋老生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心,于是下令全军戒备,向前缓缓行去。
等到了地方,宋老生才明白过来为什么斥候们背插三面红旗、却没有发出响箭示警了。这一代地势平坦、一望无际,连个稍微冒出点头的山包都没有,敌军想埋伏下几个伏兵都没处躲没处藏的。而且这种地形最是适合大规模的骑兵冲锋驱驰,就算是数倍敌军也休想阻挡他麾下精锐的左骁卫骑兵来回的冲锋、肆无忌惮的砍杀。哪怕宋老生不想打这一仗,也是说走就走,方圆数十里地内没人能追的上他。
可是对面那些敌军算怎么回事?好吧,宋老生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对面那黑压压的一片人山人海到底能不能算是敌军。之所以看不明白,是因为宋老生这帮子古人压根没见过世面,随便拉来一个后世人只要看一眼就能看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大规模群众集会吗……不对,应该叫大规模的群众集体散步。
对面这些不知是军是民的队伍人数倒是不少,足有十几万排成了一列纵队,均不披甲,更不执兵,数百人一排,整个队伍延绵数里,却都是青壮居于首尾,把老弱妇孺包裹在中间。宋老生看得有些迷糊,你说这是个一字长蛇阵吧,可谁见过这么肥的蛇?而且一字长蛇阵讲究的是击首则尾卷,击尾则首咬,击腰则首尾齐绞,最强调两翼的机动性和攻击力,一般都由骑兵充任。而这条肥蛇的首尾都是些徒步的青壮汉子,别说马了,连头驴子宋老生都没找着。更别提整条蛇身歪歪扭扭、松松垮垮,既不见掩护也不见配合,所以别看这支队伍看似人多势众,但是宋老生相信他的骑兵只要两侧一包抄,用不了半晌工夫就能把这十几万人杀的一个不剩,想逃跑都没门。
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宋老生疑惑之心更盛,眼见这些人手里大多举着些布条之类的东西,有些人还用竹竿和木棍将其高高举起,上面隐约有些字迹的模样。因为离得远,宋老生抻着脖子看了半天也没看清楚上边写着些什么,便情不自禁的策马向前打算弄个明白。
离着这只奇怪的队伍大约一箭之地,宋老生勒住缰绳刚要问话,前方的人群突然动了。
只见数百面大旗从人群中高高竖起,每面大旗上都是漆黑恍如暗夜的底色,上书“讨胡”两个鲜红的大字。这俩字一概写得东倒西歪,其丑无比,间架像刚刚习字的幼童般青涩稚嫩,笔力如快断气的濒死之人一般软弱无力,只是“胡”字的最后一笔无勾,仿佛一柄利剑般的喷薄直下,几乎要破旗而出。而且在两字四周,遍布着鲜血一样的墨迹墨点,几乎是肆意淋漓的泼洒在“讨胡”二字的四周。
那恍如在不见一丝光明的暗夜中被鲜血染红的“讨胡”,仿佛一个濒死战士最后的呐喊,激得宋老生的眼眶一阵刺痛、心底一片火热。他刚要说话,没想到更刺激的又来了。
站在队伍前排的数名大汉,变戏法似的不知道从哪里拽出两根长达两丈有余的木杆高高的举了起来。随着木杆竖起,挂在上面的两面白底黑字的长幡便哗啦啦的招展开来,上面的字足有斗大,这回的字不但写得苍劲雄浑,而且即便站在远处的那些左骁卫的骑兵们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对面突然亮出来两面白幡,把宋老生吓了一跳。这年头白幡有两种用途,一个是表示投降,一个是给死人招魂,适用于这个场面似乎只能是前者,难道这些人是来投降的?
可是当他看清楚白幡上书写的文字,脸色就一下子变得很难看。
只见左手边上的那面白幡上书“我以我血荐轩辕”!
右手边上的那面白幡上书“大隋故征北元帅杨景武”!(注1)
这回整明白了,这帮似军似民的家伙原来就是叛军啊!没等宋老生说话,他身后的一些骑兵们就开始抽刀拔矛,口中呼喝有声,看样子不管这帮叛军是否手无寸铁、是否怀有敌意,只要总管一声令下,他们就要冲上去砍杀一番了。而更多骑兵脸上的表情则是十分复杂,手上更是全无动作。
之所以他们的反应差距这么大,是因为那些一确认了叛军的身份就蠢蠢欲动的大都是当兵没几年的新兵蛋子,屁事不懂;而那些按兵不动的则大都是参加过开皇十九年和仁寿元年那两次与突厥人大战的老兵。大隋的府兵可是正经的职业军人,一旦从军理论上要终身服役,所以三四十岁的老兵在军中不但很常见,而且这些经验丰富老兵还是军中的骨干,不仅那些新兵蛋子对他们服服帖帖,连那些兵头将尾的校尉、旅率之类小军官也得对他们客客气气的,否则手下不出乱子才怪。
注1:杨景武即杨素,景武是杨素的谥号。杨素两次北击突厥时的军职应为行军元帅,并无征北的前缀,此为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