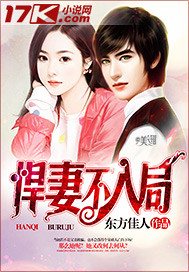时简闭着眼睛,靠在秦涣宽厚温暖的肩上,他的身体跟他这个人一样,热情,暖,就像阳光一样。
而不像方青俜,他身上很凉,一年四季的身体,比她一个姑娘都凉。
也许这就是两人的不同吧,秦涣虽然面上高冷,不好亲近,但他的心,以及人都是热情,火热的,让人依靠着感觉温暖和安心。
而方青俜,他面上温润,平易近人,可为人确实冷。
他的冷,是冷在骨子里,冷的太像个商人,审时度势,狠心果断。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几乎把自己的青春都给了他。
虽然没有挑明,可是,她的整个青春时代,为数不多的十多年,都给了他。
如今,也算结束了吧。
可是,那是十几二十多年啊感情啊,怎么能说放下就放下了!
时简靠在秦涣肩膀上,眼泪一滴一滴地顺着眼角往下流,她哭的无声,秦涣也没再说话,两人在放着萨克斯的清吧,各想各的事情。
女人难过了,哭了就过去了,何况时简也不是那种想不开的人,哭过了一定会好的,秦涣如是想。
想着,突然听到耳边不同于哭声的声音。他低头,就看时简脸蛋皱成一团,脸色发白,嘴更是白的吓人。
而她的手放在小腹上。
想到他的生理期,秦涣心里一激灵,伸手抓住她捂在小腹上的手,着急地问:“是肚子疼吗?疼的很厉害?”
耳边的传来的声音,几乎是用吼,时简却感觉安心,她慢慢地抬眼,看着面前秦涣俊郎着急的脸,扯出一抹笑,如实地说。
“疼,像要死了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她在秦涣面前说不来假话,也异常的娇弱,这样的她,就算在方青俜面前都没有。
他的手已经穿过了她的腿弯,时简看着不说话,闷头把她抱起来的人,揽住他的脖子问,轻轻地开口:“你是喜欢我吗?”
秦涣脚下的步子停了一下,停了之后,他低头看着对他笑着,脸白的像个鬼一样的时简。
还对他笑?看他着急,看他慌,看他像个知心大姐一样对他陪聊,陪抱,她很开心是不是?
就有理由不好好爱惜身体了是不是?秦涣的心火一下子涌了上来,这个女人,出现就是专门来折腾他的。
“我他妈喜欢死你了!”
所以,你就使劲折腾老子吧!
时简听秦涣与众不同的示爱音调,又笑了笑,只是,她的肚子太疼了,绞痛着,似乎要把五脏都搅碎一样。
一阵痛感来袭,她说不出话,只得靠在秦涣身上。
秦涣看着突然不说话的人,吓得手都是凉的,她……她不会也是死了吧。
秦涣心里直发凉,哆哆嗦嗦地喊了一声:“时简。”
没有人应。
他的心又沉了一分,手更抱不稳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轻微的嘤咛。
秦涣身上整个血液都回暖了,还好,还好,人还活着……
去医院,马上去医院。
他抱着时简出门,到门口跟前台说了句:“帐先记在我头上。”
看今天是秦少爷来了,经理一直在前台候着,这会儿看秦少爷抱着人大步流星地走着,脸上的急色他从来没见过,经理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他小跑着亲自把清吧的门推开,让秦少爷过去,丝毫不提钱的事儿,说道:“秦少爷慢走。”
等人走了,经理才关上门,新来的员工问他:“经理,那人没结账,你怎么对他还那么客气,万一是来吃霸王餐的呢?”
“吃什么霸王餐!”经理朝新来的小菜鸟头上敲了一把:“你可不看看那人是谁,能是缺钱的人?你刚来,少说话,多用眼!”
说完,就走了,走着经理心里暗道,这一桌子酒虽然也值些钱,可是比起在秦少爷面前买个好得到的好处,这算什么,九牛之一毛都算不上。
秦涣把人送到医院,直接请了母亲的好朋友,严医生。
虽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可医院是个不分黑夜的地方,华灯初上,这里跟白天并没有什么区别。
依旧是冷,难闻。
秦涣坐在外面长廊等着,大约二十分钟,严大夫就出来了,边摘口罩,边跟他说:“姑娘的身子怎么能那么折腾?生理期还喝酒,她本来就宫寒,以后你们不想要孩子了是不是?”
“严重吗?严姨?”
严医生瞪着秦涣:“严重?什么才叫严重?以后不能生孩子了才叫严重?”
严医生跟秦母交好是看着秦涣长大的,她说这话,是对一个晚辈说的话,她知道秦涣能听的进去。
秦涣也确实听进去了,他皱眉:“她前两天感冒吃药,那个就没有了,今天又实在心情不太好,我……我也就任着她了。”
谁知道竟然那么严重,竟然疼的昏了过去。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严医生叹气:“不好好爱惜身子,我不不是让你们喝酒,是生理期前后真不能喝。我刚才给她摸了摸脉,这姑娘,宫寒,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身子已经虚了,再这样下去,可不行。”
秦涣听着皱眉,问:“那严姨您说怎么办?”
“怎么办?你们年轻人有工作,总不能天天在医院住着,这事儿,还得你们自己操心!”
“严姨,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监督他的。”秦涣对严医生说,也是对自己说。
这个时简,照这样下去,她迟早得把自己作死,他本来想着不着急,温水煮青蛙,现在他改变主意了。
不温水了,直接上大火!
严医生看秦涣态度很好,也很欣慰,拍了拍他说道:“让护士给她收拾了之后,你就进去吧,没什么事儿,输了水,醒了就好了。”
说完严医生就走了,秦涣坐在外面等着里面的小护士忙完,等着等着周尧夏来了电话。
一开口便是:“你这在哪儿花前月下呢?家都不回了。”
“鬼的花前月下!”秦涣被气笑:“我在医院呢?”
周尧夏坐在床边看和晏贴面膜,问道:“怎么又在医院?今天喝酒喝的了?”
秦涣以前酒量不是太好,被灌多了,进医院很正常,只是商场陪酒了这么久,他的道行不会还那么浅吧。
“是喝酒喝的了。不过不是我。”秦涣叹了一声:“是时简,这个人,不把我折腾疯,是不痛快了。”
短短三天进了两回医院,动不动就不醒人事,真是在考验他的心脏。
还能说这种话,说明事情并不太严重,周尧夏轻笑:“那你自己乐意,愿意疯,谁能有什么办法?”
“滚蛋,说的我跟自虐狂一样。”
“你喜欢人家,自己给自己找的虐,不是自虐狂是什么?”周尧夏站起来,往梳妆台走:“你要是不想自虐,不管她,谁能虐得了你。”
“……”秦涣骂了一句:“竟说风凉话,你是明天就领证了,心想事成了,可也不能这么不管兄弟死活了。”
“管,我们怎么管?你这不是发展的很好吗?我相信你秦少爷的能力。”
被夸奖的秦涣表示很堵,周尧夏这个人,就是在看他的笑话!
周尧夏笑罢,说了打电话的目的:“明天我跟和晏领证,两家晚上一起要吃饭,咱们约好的,提到中午?”
“无所谓,你是新郎官,你说了算。”秦涣心里泛酸,周尧夏这抗战是结束了,他这个连开始都没有。
周尧夏知道秦涣这会儿正堵着,为了给他的心防加固,他说道:“那你在医院吧,我跟和晏得睡了。”
“……”你们小夫妻睡觉,还用给他这个尚未摆脱单身的人报告?
讽刺,赤裸裸地讽刺!秦涣这次很有骨气地挂了电话。
通话被挂掉,周尧夏笑着趴在和晏脖颈处,只笑的和晏直摇头:“你天天老逗秦涣干什么?幼稚不幼稚。”
“不幼稚。”周尧夏正经地摇了摇头:“我从小就喜欢看秦涣着急,二十多年,改不了了,看见他就想逗。”
和晏笑,二十多岁,这还不叫幼稚,她想起刚才听到有人住院就问周尧夏:“是谁病了?”
“时简。”
“时简?”和晏回头,看着周尧夏:“她怎么又病了?不是刚好。”
“不知道。”周尧夏摇头,把和晏因为说话而弄皱的面膜抚平,安慰:“听秦涣的意思并不严重,你不用担心,明天中午见面了问问就是了。”
“也只能这样了。”和晏想到今天婚宴上出现的人,叹了声:“今天时简到休息室的时候就很不一样,我跟梁泠也没多问。不过我算是知道谁是他父亲了,看起来倒像是个好人,没想到竟然是那样一个人。”
狠心,自私,把亲情都放在一边。
周尧夏对于别人的事情不怎么上心,听和晏这样说,只是清淡地答了一句:“她是个聪明人,你放心吧,再说有秦涣在呢,他可是护短的。行了,别想着不开心的。”
和晏想想也是,就点头,催周尧夏笑去睡:“你先去睡,我护理还没做完。”
“你平常也没这么麻烦。”
“平常我又不结婚。”和晏白了周尧夏一眼,然后揭了面膜,对着镜子给自己作按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