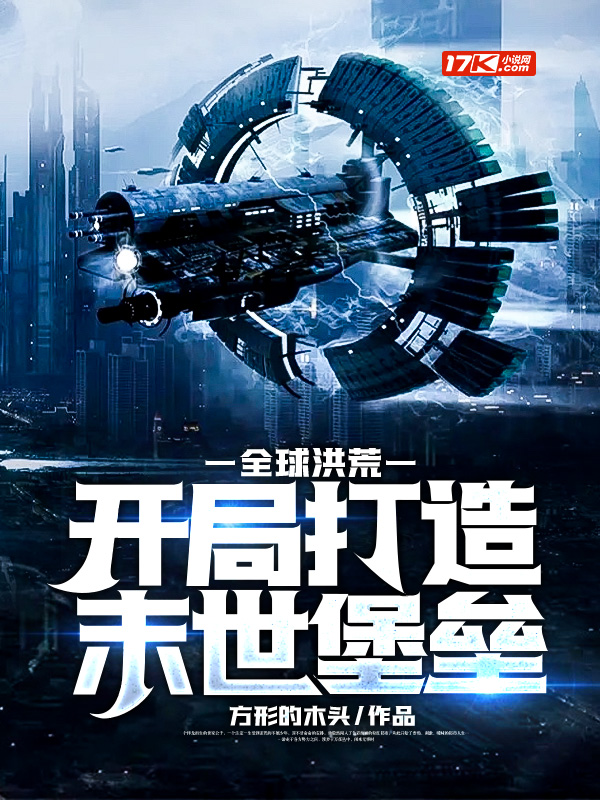朱棣眼见俘虏众多且回归之路遥远,一面向朝廷报捷并传下军令,调遣士卒快马加鞭先行赶回长城内的边关卫所,调集粮草前来接应。一面传下军令,让众军宰杀那些伤重难行的战马以作口粮,押送着三万余元军俘虏浩浩荡荡的踏上了班师之路。
数日之后,回到开平卫所之时,一众元军俘虏早已是衣衫褴褛,狼狈不堪。原来明军加之俘虏数量庞大,粮草消耗甚多,朱棣每日里只许俘虏们吃一餐,却要用双脚赶数十里路,一群北元士卒饿得头晕眼花下只得像羊群般被驱赶着前行,哪里却有力气作乱。
朱权眼见万全都指挥使已然尊奉朱棣军令,调集粮草及军队前来接应,此去北平当无大碍,便即和部下杨陵,景骏等人统帅大宁驻军与朱棣分道扬镳,改道回转大宁。
北平高大的城垣渐渐映入眼帘,乃尔不花,咬住相视苦笑,心中滋味苦涩之极,难以言表。当他们在草原苦苦撑持之时,梦寐以求的便是有朝一日返回这元朝的大都,重振元朝余威。今日总算如愿以偿,可惜自己却不是作为大元朝的复国重臣,纵兵掳掠而来,而是成为了束手就擒的明军俘虏,此情此景,当真是情何以堪。
朱棣策马缓行,身侧马匹之上却是端坐着一个身穿黑色袈裟。生就一双三角眼,貌相颇显狞厉的老和尚,正是得到明军捷报,出城数十里迎接的僧道衍。
道衍看了看神采飞扬的朱棣,突然微笑道:“殿下得胜班师,想必陛下很快便有旨意到来嘉勉。”
朱棣闻言甚喜,正欲说话之间却听道衍淡淡说道:“陛下龙颜大悦,自然会嘉勉殿下,可是只怕这数万军队便要返回各自卫所了。”
朱棣闻言心中不由得一凉,原来他麾下护卫人马不过一万八千,此次率军远征的大部分人马皆是遵从父皇朱元璋的旨意,从北平附近卫所抽调而来。初战便即俘获三万余元军,使得他的内心中隐隐抱有一丝侥幸,希望自己的父皇能给予自己更大的军权,此时满心欢喜之际给道衍如此直言不讳,不合时宜的一番言语,心中不禁颇有些愤懑不平之意。只可惜这股愤懑却是无从发泄,虽然他曾经是沙场上叱咤风云,一马当先的统帅,但自内心中却是深深敬畏着当今大明朝的皇帝陛下,自己的老爹朱元璋。
道衍仿佛对朱棣看向自己眼光中的恼恨浑然无觉,依旧是那一副好整以暇的样儿,嘴里淡淡说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世上最为难以得到的究竟为何物?以贫僧看来,殿下今日之所得,远远大过了所失。”
北平在元朝之时乃是都城所在,自徐达北伐收复大都后经过多年的恢复,人口更是大胜从前。此时的城门之外云集了北平各级文武官员,正自翘首以盼,迎接远征归来的燕王朱棣。
城墙之外,早已是人山人海。数之不尽的汉人百姓,城墙之上驻守的明军士卒将校眼见昔日作威作福,将自己的祖先肆意欺凌的鞑子高官,士卒们一个个灰头土脸,狼狈不堪给押送到来,不禁爆发出了此起彼伏,山崩海啸一般的欢呼。
跟随朱棣出征的数万士卒历经艰险,侥幸生还而归,听得这般欢呼之声更是群情汹涌,难以抑制,个个手舞刀枪嘶声怒吼,不但为自己依然活着欢呼,更是为了身先士卒,率领他们扫灭北元大军的统帅,燕王殿下欢呼。
朱棣高踞汗血马上,昂然而行,眼中见得北平一众大小官员望向自己的目光中,个个充满了敬畏之意。耳中听得此起彼伏的欢呼直冲云霄,朱棣胸中也是豪情万丈,难以自已。内心之中那一丝阴霾早已荡然无存,暗暗忖道:但教本王坐镇北平一日,就绝不容那些蛮夷之辈再肆虐于我大明的锦绣江山。这一刻的他,忽然明白了道衍所言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真正含义,也真正明白了自己那位生杀予夺的父皇为何拥有至高无上的威信,因为他不但是大明王朝的开国之君,更曾统帅千军万马浴血沙场,替普天之下千千万万的汉人百姓夺回了尊严与自信。
大宁,王府后花园中。徐瑛静静伏在朱权怀中,眼望苍穹天际处给夕阳映照得甚是绚丽的云彩,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安静祥和之意。
朱权忍不住笑道:“你也不问问我和朱老四此次出征的战果么?”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无论是胜是败,注定已然有人无法回到父母妻儿身边。”徐瑛轻轻叹息一声,微微摇头。言语之间,心弦颤动下不禁有些害怕,害怕朱权下一次出征。思虑及此,双手不由自主的抱紧了朱权。
朱权感觉徐瑛柔软的娇躯微微颤抖,竟似畏惧着什么一般,心中不忍下柔声说道:“我想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用再率军出征了。”嘴里这样说,心中却是暗自忖道:北元虽灭,鞑靼瓦剌势必取而代之,希望下一战晚些到来吧。
徐瑛闻言甚喜,情不自禁的抬起头来,注视着朱权柔声道:“ 此话当真?”
眼见徐瑛睫毛轻颤,眼中充满期盼之色,朱权胸中不禁柔情顿起,微微颔首。
徐瑛低声道:“希望我的儿女出生之日,已然是天下太平,再无征战。”说到后来,已然是俏脸晕红,声似蚊呐。
朱权闻言一愣,犹自没有回过神来,待得徐瑛羞恼之下在腰际狠狠揪了一把,吃痛之下这才回过神来,心中欢喜之情犹如泉涌下激动不已,紧紧抱住徐瑛,在她粉颊一侧狠狠一吻。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正当大宁军民忙于春耕之际,一个不速之客不请自来,由高丽踏入了辽东兀良哈三族的栖居之地。却是来自高丽国王的使者李成元,以及手下的一百余随从。
大宁乃是朱权的就藩之地,兀良哈三卫目下更是宁王部下,三族首领不敢怠慢,连忙派遣手下骑兵护送李成元来大宁觐见朱权。
王府客厅之中,朱权一面打量着这个年约四十,颔下三缕长须,作一派中原文士打扮的李成元,听着他一口流利的汉话,不禁暗自纳罕。他却不知高丽自隋唐其便深受中土文化影响,国内读书之人莫不以会说汉话,会琴棋书画为荣,却和草原游牧部族大不相同。
李成元乃是目下高丽国王李成桂的族弟,而李成桂则是昔日高丽的统兵大将,迫于无奈也曾率军犯境,逼近大明铁岭卫所。
原来高丽面对中土强大王朝之时历来是心存畏惧,昔日畏惧蒙古骑兵的骁勇善战,也曾是元朝的藩属国。历代元朝皇帝也素来以和亲的方式笼络这个小国,故此来自元朝的王后,妃子依仗元朝势力,在高丽可谓是呼风唤雨。徐达,常遇春北伐攻取大都,洪武皇帝朱元璋一统华夏,元朝皇帝逃亡草原后,高丽国内也逐渐兴起了一股亲明势力。无奈北元重臣纳哈楚统帅辽东元军二十万盘踞辽东,近在咫尺,依旧不是高丽弹丸小国可以抗衡,故此元朝后宫势力依然占据上风。待得纳哈楚被冯胜大军迫降,李成桂被迫率军进犯铁岭,实在不愿以卵击石索性率军回国,以清君侧的名义彻底肃清了国内亲元势力后,逼迫国王禅让,成为了高丽的一国之君。李成元素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钦慕中土繁华大国,索性向族兄讨了这个出使大明的差事。
朱权眼见这个李成元言辞之间甚是谦恭,不禁颇有好感,无奈对方意欲前往应天觐见大明皇帝朱元璋,念及此国不但曾在元朝后宫指使下杀死昔日大明派往高丽的使者,亦且自不量力的兴兵进犯铁岭卫所,也不知朱元璋和朝中一帮大臣对这个小国是何态度,沉吟片刻后便即淡淡说道:“贵使远道而来,便请暂居大宁,待本王启奏朝廷,再作决断。”
李成元本待拜见朱权后便即起行南下,前往大明朝的都城应天,此时听得这位手握重兵,驻守大宁的王爷如此安排,不禁颇为失望,心念转动之间忙即微笑说道:“昔日妖后,妖妃蛊惑本国朝野,目下本国乃是新主执政,已然将那些祸乱社稷的狐媚女子尽数处死……”
朱权对于大明使者身死,李成桂率军犯境之事本是耿耿于怀,此时听得这个李成元哪壶不开提哪壶,心中更是不悦,皱眉沉声道:“皇帝陛下日理万机,本王念及贵使远道而来,特此相见。还望耐心等待为是。”
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高丽自上而下,对于当今大明朝的皇帝,对于这个数十年间就能叱咤风云,灭亡元朝的朱元璋那是自心底里深深畏惧,眼见朱权神色间颇为不耐,也就不敢再行啰嗦。
朱权策马出城,正在军营观看明军士卒操演之际,突接风铁翎禀报,瓦剌首领马哈木率领手下五百士卒,来到了大宁城外,意欲求见自己,不禁愕然。
待得眼见满头白发的马哈木率领手下五百士卒,若无其事的来到自己军营帅帐相见之时,朱权眼见对方神情冷肃,泰然自若,和李成元全不相同,心中也不由有些佩服,暗自忖道:这些能在塞外称雄一方的部族首领,胆识气度倒是让人不得不服。念及他那个狡诈多智的儿子脱欢,心中不禁暗自叹息忖道:上次没有趁机干掉脱欢,只怕以后机会再也难得。
夜幕降临之下,王府书房之中,荆鲲听得朱权诉说今日面见瓦剌首领马哈木,以及高丽使者李成元的事后,略一沉吟后淡淡说道:“高丽小国实力远远不可和大明相比,且颇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对中土一统王朝素来是敬畏有加,暂时不具威胁,不足为虑。但瓦剌趁北元灭亡后趁势崛起,非是高丽可比,马哈木此次前来虽则亦是愿意臣属大明,但所求封号之事却是值得商榷。”说到这里,看了看端坐一侧凝神倾听的朱权,微笑说道:“马哈木希望瓦剌臣属大明后,得到皇帝陛下降旨封为瓦剌国可汗,此举万万不可,还是封王较为妥当。”
“难道称号不同,意味却也不同?”朱权狐疑道。
荆鲲微笑摇头,正色道:“可汗在草原之上代笔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颇有和咱们中土皇帝陛下平起平坐之意,而一个王爷则永远只能臣服于皇帝陛下驾前。”说到这里,端起茶盏浅酌两口后说道:“故此殿下在上奏之时,必须声明对此事的看法。”
二十余日之后,自应天而来的圣旨到达大宁。洪武皇帝朱元璋允准瓦剌首领马哈木,高丽使者李成元进京朝见。出乎意料之外的却是,特命朱权亲自率军护送二人回转应天。
徐瑛甚是挂念远在应天的徐辉祖,无奈已然是数月身孕,不便远行,不由得怏怏不乐,只得嘱咐朱权回到应天之时前往魏国公府看望。
朱权唯唯诺诺的一口应承之余心中却不由自主的暗暗苦笑忖道:这个舅子一心忠于太子朱标,和黄子澄,方孝孺一般将我这个就藩的王爷视若仇寇,当真是不如不见。
朱权,马哈木,李成元一行晓行夜宿,南下而来。冰雪消融下春意盎然,一路景色倒是颇减旅途寂寥。待得踏入江苏境内之时,大道之上忽然多了许多头戴方巾,三三两两结伴而行的读书士子,年纪从弱冠少年到四五十余岁之辈尽皆有之,行色匆匆之际竟是不约而同的俱都朝着应天赶去。
朱权心中好奇下询问沿路接待官员,这才知晓原来今年恰逢三年一次的大考,士子们寒窗苦读,俱都是前往应天参加春闱。
夜色笼罩下的应天,紫禁城御书房中 ,朱元璋端坐书桌之后,打量着眼前不远处的朱权,回想这小子昔日里胆大包天,竟敢先斩后奏下与徐瑛拜堂成亲之事,心中甚是恼怒,脸色也不由得颇为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