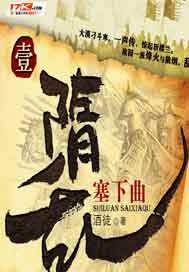第二天,郑敏之也提四样糕点来到义和顺,郑庆义在客厅里看报纸,年青的领着郑敏之进入客厅。郑敏之:“郑会长你好。我叫郑敏之。”
郑庆义站起来笑着说:“啊,敏之啊,玉花提起你。”
郑敏之很拘束的说:“郑会长,你好,谢谢你让我来见你。”
郑庆义笑道:“见我有何难,吱会儿一声就行,不吱会,也没事,想见就来。我又不是难见之人。不过,你带这礼物就有点见外了。”
郑敏之脸红了,不好意思地说:“听我老婆说,玉花姐爱吃。我就又拿来了。”
郑庆义笑笑:“来就好,啥也不用拿。你随便坐。不要拘束。”
郑敏之这才放松了些,坐到沙发上说:“初次相见,也不知带点啥好。只好带了点果子,略表心意儿。”
郑庆义笑容可掬地说:“好,我收下,下不为例。”
年青的送来茶水,顺便把果盒子收起来。
郑敏之这才彻底放松了,他拿起茶杯,吹了吹上面的茶沫,喝了一口,放下茶杯说:“我听人说,岛村请你喝日本茶。挺憋屈的?”
郑庆义皱一下眉头,随即舒展开来:“日本沫茶还是不错,只是日本货不着人喜欢。不过,慢慢卖还能卖得出去。不少铺子掌柜他们都常来,没事儿聊聊也不错。玉花跟我提起你的事,玉竹,哎——,那个吴敬敏吧。”
郑敏之点点头。
郑庆义又说:“吴敬敏很有见识,能舍弃所有财物跟着你,你就是她后半生的依靠。”
郑敏之深有感触地说:“郑会长说的对,我得好好待她。”
“听说你想进取引所玩玩?”郑庆义先把话题挑开。
郑敏之开门见山地说:“是,我开的小粮米铺叫福兴成,我听说郑会长在取引所游刃有余,我想跟郑会长试试。”
郑庆义:“没问题,不过不能总是赚钱,也有赔钱的时候,到时候的时候,可别哭鼻子哟。”
“这我知道,我也不能全投进去,只拿出一部分,跟着郑会长,先试试,你买我就买,你卖我就卖。小打小闹还行吧。”
郑庆义:“这就对了,有心里准备就行。你注意分析过行情吗?进取引所交易,也不能光跟着,也得有自个儿的想法。到时候的时候,我也有头脑发胀,整错的时候。那可就别跟了。那就盲目了。不行,要有自个儿的主见。这是必须的!”
正说着,年青的进来报告:“有个姓任的掌柜,说是你的老朋友,要见您。”
郑庆义一听说是姓任的掌柜,愣了一会儿也没想明白是谁。
郑敏之说:“是不是任理堂啊,咱这疙瘩就他一个姓任的。”
郑庆义一拍脑门:“可不是咋的,一说掌柜我到不知是谁了,这个老**。让他进来。”
郑敏之站起来说:“郑会长,那我就告辞了。一切都拜托了。”
郑庆义连忙把手往下按按,冲着郑敏之说:“坐下,坐下,你怕他啥呀。听听他说些啥。有好事儿,你就得了。在我这儿,你就随便。”
任理堂一进客厅就摇头晃脑地说:“哎呀大会长啊,拜见你一次真难啊。我得先派人打听清楚,你是否在家,我才敢来。你这里的人都不待见我。见着我像似见着鬼似的。你说你一步也不往平康里踏,有事找你都找不到。还不如年青那会儿,三五天就能见着。哎呀,这不是郑掌柜吗?咋也来这疙瘩来了。哦,你俩现在可是连襟呀。”
郑庆义:“年青的说任掌柜的见我,我还寻思五站新开的铺子里,没有姓任的掌柜呀。你瞅瞅你,小嘴巴巴的,啰离啰嗦的没等人吱声,就整出一大堆来。让人咋答对你?”
任理堂自嘲地说:“还瞅瞅我呢,你这不也扒扯我半天吗。我就这么个人,哦,郑掌柜。你们有事儿先说,我等会儿也行。”
郑敏之站起来说:“任掌柜,别来无恙啊。”
任理堂笑道:“人都让你领走了,我还好得了?说笑啊,玉竹咋样?”
郑敏之:“托你的福挺好的,再有几个月我就当爹了。”
任理堂:“啊。够快的。你瞅瞅,从我这儿出来的两姐儿,都当娘享福了。”
郑庆义:“说你啰嗦真没说屈你。有屁快放。”
任理堂:“红万字会儿的事儿——,我就不说了。你上点心,要是通过了好告诉我。你和天增长咋了?”任理堂本来想说加入红万字会的事儿,见郑庆义一听就变脸了,忙换话题。
听到天增长三个字,郑庆义脸色缓和下来:“我跟天增长有啥?它的大掌柜跟我都在会当副会长。跟他能咋样?”
任理堂:“跟你这么说吧,指定有啥事儿,前个儿来几个小子,说起在取引所买五千火车豆子。不知真假。这几小子不能没来由就打听你以前的情况。是不是针对你下茬子?”
郑庆义笑道:“扯吧,我去大连时,郭宝中跟天增长的人别了一次,都和解了。哦,郭宝中卖两千火车大豆,要买实,中途让我给停了。停了也不怨我呀,是他们大帅东家到了中国街,大掌柜的没敢往回拉。我正好大连有合同,就都发埠头去了。”
任理堂:“我就说吗,一定有点事儿吗。他们吹牛吹的大,说在取引所赚钱像流水似的。说句话就赚钱。也是,郑掌柜你不知道,郑会长带了我几次,买、卖都赚不少钱。说好了啊,再要是跟天增长别起来,可别忘了带着我。”
郑敏之:“任掌柜也在里面玩呐。”
任理堂:“那是,手续费一火车买卖才六块钱,可赚的就多多了。”
郑敏之:“任掌柜说的对。我正跟郑会长说呢,我也进去玩玩。”
任理堂看了郑敏之一眼:“瞅你这人还真不错,当时,我恨不得叫人把你削死。别老掌柜掌柜的,听着别扭。叫我大哥。从玉竹那儿论,我是你大舅子。”
郑敏之:“是,是,大哥,玉竹改叫吴敬敏了。”
任理堂笑道:“哈哈,敬敏。这丫头片子挺有心劲的。”
郑庆义见两人唠闲嗑,就说:“我说任大哥,我和天增长大掌柜一来一往扯平了。别来跟我扯事儿。再说了,取引所就是买、卖的。谁愿意去就去呗,没事别啥呀。那几个老客逛窑子,见着女的就吹,要不赚了钱没地场花。敏之,你就到取引所转转,以我的名义整两把。先看看行情再说。”说完拿起电话要了大连的长途。放下电话后说:“这一阵子外地的挺平稳,不见有何大举动。大掌柜买了五千火车豆子,赚钱是可能的。”
任理堂:“你信他们说的?”
郑庆义听着好笑:“不信咋地,我去问问大掌柜的?”
大连电话接通了郑庆义操起电话,就听里面说:“东家,我是郭宝中,哎呀妈呀,我可是开眼了。梓桐整的好,我都不想回去了。”
郑庆义乐道:“我还没说话,你到说了几个事。别在电话里唠了,赶紧回来。这疙瘩事儿急。你让梓桐把那儿的情况拢拢回来跟我说。”撂下电话对郑敏之说:“五站这疙瘩能有千八百火车的量就不错了。天增长一来,能整到五千火车。这太好了。他家老客多,跟着起哄的也多。不过没啥。我不是也有你们几个老客了吗?”说完,郑庆义自己笑了起来。
郑敏之欢喜地说:“我明个儿就去探探消息。学学咋整的。”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阴。郑庆义虽说不想跟天增长别,可五站能敢进行那么大交易量的寥寥无几,郑庆义感觉有劲使不上。听到大掌柜一气就买了五千火车大豆,这让他有了跃跃欲试的感觉。所以,他开始准备进场,并让郭宝中尽快回来,好参与取引所信托交易。
其实,郑庆义早就知晓天增长在取引所,非常频繁进行买空卖空交易。任理堂一席话引起了郑庆义的好奇心,开始注意天增长在取引所的动向。由此引发了一场意外信托交易之争。郑庆义虎胆包天,竟敢把名头响亮的天增长,当作竞争的对象。
天增长在新市场名气很大,一说是天增长的人,谁见了都会给点面子。这天,魏大掌柜的安排好事项,坐在炕上悠闲自得的在屋内盘腿喝茶水,不时的摇头晃脑哼着两声小曲。捏着小茶壶正嘴对嘴地啜着,正好啜一口刚到嘴里,忽然有个年青的闯进来说:“大掌柜的,督军派人来了,说有紧急公务交给您。”
魏占山手一哆嗦,从小茶壶涌出一股热茶水直入嘴里的,把魏占山烫得,嘴里的茶水一下全喷到地上,嘶嘶哈哈说不出话来。
刚到门口的年青的见状,吓得混身打颤。“啊——,我——。”连忙跪到地上磕头认错。
魏占山这时缓过神来,放下茶壶,把身上溅的水珠抹了一下说:“啥事?那么大声叫唤?”
小年青跪那哆嗦地不敢吱声。魏占山刚要训斥他,一看他害怕成那样,话到嘴边变了,只是说:“起来吧——,啥事?”
年青这才战战兢兢地说:“督军派人来送信,我请他进来,他不进屋,说是非常紧急,必须见您的面。”
“在哪儿呢?”
“就在大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