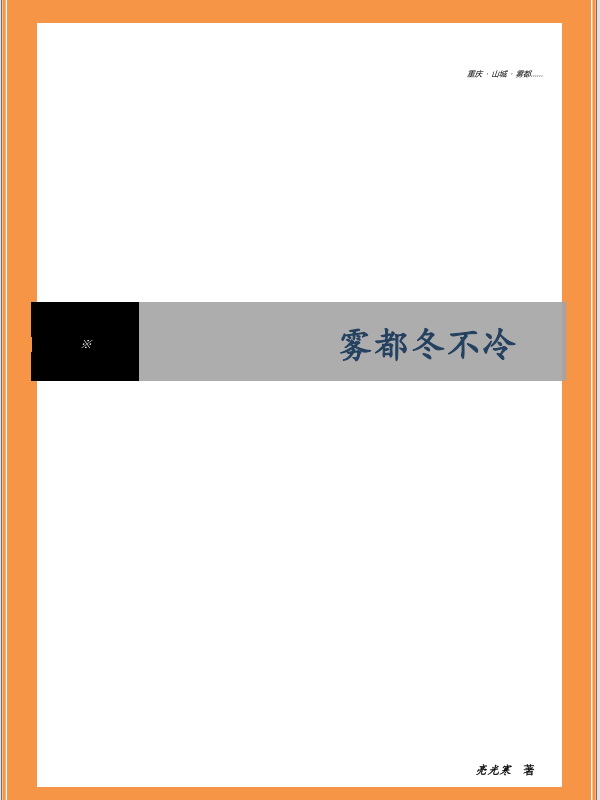被抓来建造陵墓的工匠中,多是普通民众,他们的地位在当时社会是最底层,和权贵人家的丫鬟相比都要逊上两三筹。可别小看这两三筹,中国古代的社会向来以阶级分明著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要是没有什么机缘,劳苦大众很难和婢女走到一起,那感觉就像是一个拾破烂儿的拐了个知礼知性的大学生,真要是有,那简直就是上辈子给佛爷上足了香,是莫大的福报。
由此可以想象,当工匠们一路搜刮到别院之后,见到如此之多的“美食”摆在面前,欲望自然疯狂滋长。在数量差异巨大的情况下,这座别院里的女性,受到了何等的凌 辱,从树下那人的抽泣声中就可以听出。
活葬的女眷一共有七十三人,其中最为尊贵的是韩信的三位夫人。三位夫人性子高洁,为了不受凌 辱,选择了咬舌自尽。
但是她们还是太低估了眼前的这帮饿狼,就算她们身死,也没有逃过“特殊照顾”。
我打断了她,对六大爷说:“你问问,她是不是薄姬。”
一人一鬼磕巴了一阵儿,六大爷告诉我说,不是。她是大夫人殷嫱的通房丫鬟,叫梨儿。
我撇撇嘴,看来侧房只是战场,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不过就算她的身份没有我想得那般尊贵,可也绝不普通。通房丫鬟,可不是一般的丫鬟。
在古时候,大户人家的小姐,一般都有贴心的丫头,身份是上下级,但感情却亲如姐妹。她们,一般都会在小姐出嫁的时候一同跟去夫家,所以也有叫随嫁丫头的。
名头是其次,干的活儿才是最主要的,她们,一般都不做洗衣服做饭这种粗活儿,端茶递水都算过劳了。那她们负责的是什么呢?负责在小姐出嫁之前,做先锋官去检验未来姑爷的“本事”。这么做,主要是为了防止自家小姐名声已去,悔之不及。
如果姑爷功夫尚可,那自然无话可说,但要是不行,事儿就大了。女方可以直接要求退婚,理直气壮的那种。
如果一切照常进行,小姐嫁了过去,通房丫鬟的地位会不减反增,毕竟是睡过姑爷的人,更不可能做那些劳累的活计,那她应做的是什么呢?是在小姐与姑爷交欢的时候,在床边儿服侍,端端茶,擦擦汗,偶尔还能上去掺和两手。在小姐来月事或者是怀孕不便行房的时候,代替小姐宽慰姑爷。与其说她是通房丫鬟,倒不如说是缺了一个名头的小妾也不为过。
我不自觉的干咳了两声,还是古代的前辈们会享受啊,说是娶一个,实际上呢?还带一个,想想大家都是富二代,还有点儿小遗憾。
梨儿的话语声一直没停,六大爷也就照着翻译,如果鬼话能评级,我觉着六大爷这即时翻译的水平起码得上八级。
倘若把匠子们进院儿比作噩梦开始,那么梨儿口中的那只诡异猴子的出现,就是噩梦的终结。
当时别院里乱作一片,哭喊声,呼救声,还有各类靡靡之音响作一片,谁也没有留意那只猴子是什么时候进的院子,只知道它一出现,就有人被开膛破肚,匠子们瞬间就从天堂跌进了地狱。
那只猴子,专挑正在交合的男女下手,梨儿当时正在侧房的床上遭受欺凌,床上的两者,都没有逃过一劫。
六大爷的话一停,而后主动向她问了几句,梨儿的语气有些急促,黑影的波动比较大,看上去像是在比划一般。
“说啥了?”
六大爷:“她说那猴子只有半人高,但是力大无穷,十几个人围着都无法近身,指甲跟刀一样,碰着就皮开肉绽。”
不知道为什么,听他这般描述,我自然而然的想起了巨棺围绕的那口铜箱子,里面的尸骨我看了,当时确实感觉像猴子,连带二大爷那时的模样,我隐约猜到了什么,只不过我没有多嘴,六大爷能问,自然也是有了这般想法。
梨儿最后的记忆就是听到门外急促的脚步声,大批的人在逃离院子,可惜,她却没法谋得那线生机。
千百年来,霸凌她的男人的尸骨一直压在她的身体上,让她分外耻辱,黑子虽说连她的骨骼也一起破坏了,却让她倍感轻松,由此记了一恩。
黑子听得有些不好意思,挠头说也没什么。我冲他翻了个白眼,你个大活人能受得起千年老鬼这份恩情?
“那她想要我们帮她做什么?”
六大爷不急不慌的点了根儿烟,“她想让我们带她出去。”
“什么?带,她,出去?”我都有些结巴了,难不成要在我们这个活人编制里添一名鬼将?
六大爷:“嗯,说是被扣在这儿没法走了,孤零零的一个人,想投胎。”
我心说你可别说你是一个人,早前儿我们还遇到不少水鬼,黑子还被附了身,就是你没往外走,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
王修谨注意的点儿跟我天差地远,“被什么扣在这儿?”
六大爷:“她说她不知道,反正她出不了这院子。”
王修谨左边儿那根纤细的眉毛立马飞起来了,把怀里的罗盘摸出来,里面的指针早就不动了,整个罗盘都是瘫痪状态,压根儿没法使。但他却把罗盘硬生生翻了个个儿,天池朝下,底盘朝上,本来是一块朴实无华的木头底座儿,被他手掌一抹,去除最表面的一层木皮之后,露出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儿,小字成周天状围绕,一圈一圈的往里套,一直套到最中间的位置,空出来一块儿乒乓球直径大小的圆环。
我看那些小字看得脑袋发涨,密密麻麻的起码有几千个,而且特娘的压根儿不是通用字体,简直打破了我对中华文书的认知。
王修谨从包里摸了一个黄铜汤勺,把勺底往底座中心的圆环一放,我轻咦了一声,这不是司南么?!
司南,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是用来当指南针使的,但是勺子把儿只指北,你得倒过来判断。从磁性的运用上来说,这东西和罗盘是有共同之处的,但是从用场上判断,他俩压根儿不是一件东西,可怎么到了他这儿,就万法归元了?
我们三个人一直尾随在他身后,他托着那东西一直在池子边儿上绕,于是乎我就越看那池子越不顺眼,怎么着都觉着古怪,刚想开口说不然咱起个底儿看看,王修谨停住了。
我凑上前,看他在罗盘底座儿上拨弄,那些环绕在汤勺儿周围的一圈圈小字,其实并不是直接镌刻上去的,有少数的几圈可以转动,王修谨调整了几下,而后问我,现在是什么时辰,我看了看手表,早上六点。听完我的报告,他又转了转最里面的一圈儿文字,脚下接着就活动开了。
这回倒是没走两步,几个人就在梨儿藏身的两棵香樟树中间停下了,梨儿还是不敢贴近我们,自顾自往边儿上退了一顿距离。
“就在这儿,往下挖。”王修谨说。
我们的工兵铲早就丢的丢没的没,无奈只能回房找了些铜盆银碗来用。下手之前,梨儿突然磕巴了几句,六大爷说:“她说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不要伤害这两颗香樟,她在这儿这么些年,就它们还陪着她。”
我说:“她看不出来这树已经死了么?”
六大爷说看的出来,可她就是觉得,它俩还活着。
王修谨一听可不得了,就这里,没跑了,赶紧挖。
我跟黑子立马动手了,左右开弓,就算家伙事儿不顺手,那也硬生生往下刨了半米多,直到我的碗沿儿磕到了硬物,发出“乓”的一声轻响。
把上面残留的浮土捧走,我看到了一个件破破烂烂的孝衣。
是个尸体,不过皮肉已经分解了,所以没有漫出来什么味儿,黑子忙活着把它整个儿挖出来,刨到一半儿的时候,边儿上的梨儿突然惊呼,继而大哭起来。
她哭是情绪发泄,可带动的阴风却彻骨寒冷,我说六大爷你赶紧让她停,再吹一会儿我骨头都酥了。
打着手电,钻到坑里,才看到那块儿发着莹莹碧光的青玉。
第一个直觉就是宝贝,在地底下买了这么久,光泽依旧,说是奇迹都不为过,而后一想,那丫头这般反应,多半是认识。
我把它掏上去,交给六大爷,后者与梨儿一番交涉,这才搞明白状况。
她说这玉佩是自家主子的,也就是殷嫱的,所以我们挖到的这具失身,绝对就是殷嫱本人。
可是她怎么会被埋在香樟树底下的?谁埋得?她在这儿,又跟梨儿出不了这院子有何联系?
这一切梨儿都无从知晓,前两个问题我们也无法解答,王修谨倒是给了我们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还是不确定的。
殷嫱与梨儿是主仆,与其说感觉说树是活的让她觉得有伴儿,还不如说殷嫱在这底下让她感觉此地亲切,她出不去,很有可能是这位主子舍不得,毕竟梨儿走了,剩下的,可真就是她一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