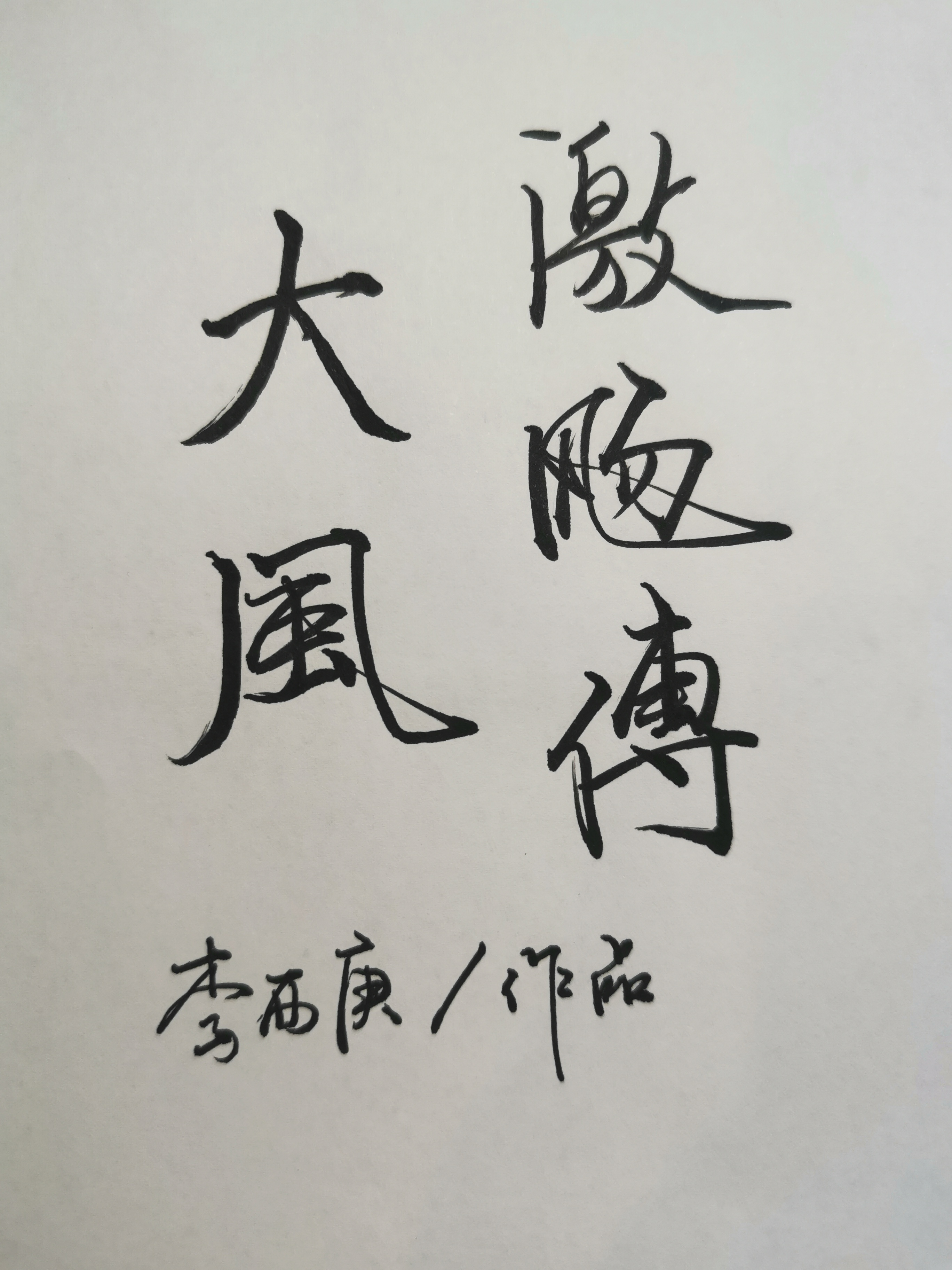慕北陵大惊,箭步冲上前将张辽阔扶起,探指鼻间,尚有微弱呼吸,扣腕细查,五脏皆无大碍,视之胸腹处有两尺三寸刀伤,深可及骨,即刻左手压于伤口,碧绿柔光翁然浮现,光芒似水荡漾,新生血肉,伤口许许愈合。
半柱香过,张辽阔张口咳出浴血,急促吸上几口气后,方才彻底缓过来。
慕北陵扶他到青石台旁坐下,问曰:“怎么会弄成这样?”
张辽阔急道:“大事不好,漠北军出关追击,邬里邬重置四营数万将士不顾,潜逃回关,路遇蒙面黑衣人截杀,属下本想潜回来通报,被黑衣人发现,鏖战几许诈死方才逃过一劫。”
原来他悄悄潜入漠北送信后,恰好遇见邬重邬里大军毕竟碧水关,本想多探些情报,哪知关军兵败如山倒,二人仓皇而逃,遁至扶苏关百里开外时遭遇不明人截杀,适才伤成这样。
慕北陵腾然惊喊:“你说什么?邬里邬重弃军逃跑?”
孙玉英刚刚听见院中骚乱,刚欲前来一探究竟,陡闻慕北陵喊邬里邬重弃军逃跑,瞠目结舌,晃身至青石台前,疾呼道:“你刚才说什么,谁弃军逃跑。”
慕北陵看她一眼,皱眉不言。张辽阔道:“属下不敢欺瞒,亲眼见到邬里邬重带五十骑逃了回来,不过遇到那些黑衣人的截杀,生死不明。”
皇甫方士沉道:“眼下最重要的就是保下四营将士,主将逃战,漠北军士气正盛,恐被屠戮。”
慕北陵道“是”,随即吩咐赵胜马上将这里的事情通知祝烽火,建议其火速赶往扶苏关。然后顾不得吃饭,让皇甫方士好生照顾张辽阔,转身朝院门去。
皇甫方士追上拉住他,贴耳低声说道:“主上莫忘了给赫连阔传信之事,此乃绝佳机会,切莫要一意孤行,只能守关,决不能出关拒敌。”
慕北陵道:“北陵明白,先生放心。”旋即拉来马,与孙玉英,姑苏坤策马出城,直奔扶苏关去。
且说扶苏关外百里之地,有一浅洼地带,多生杂草,草中伏尸数具,皆关军装扮,十余匹战马游荡在草地上,舔舐野草,不停打着响鼻。那尸体中,忽有一具抬起头,满脸血污,衔着一口杂草根,他悄悄巡视周围,见无人声时,艰难支撑起身体,挪至一匹战马旁,蹬马镫上马,趴在马背上朝扶苏关方向逃去。
这边,慕北陵一行人到达扶苏关时已是晌午十分,关内气氛萧肃,校场大营空空如也,仅有百来士兵在前后关门据守。进关楼,见孙云浪正在议事厅观摩地形图,忙上前报道:“属下参见大将军。”
孙云浪回身见他形色匆匆,问道:“你怎么来了,伤势都好了么?”
慕北陵此刻哪有心回应伤势,急道:“禀大将军,属下有紧急军情禀报。”
孙云浪苍目微蹙,道:“什么紧急军情。”
慕北陵道:“今晨属下的从属辽阔前来回报,漠北军出关追击我军,邬重邬里弃军逃跑。”
孙云浪一怔,随即喊道:“胡说八道,此时为何老夫不知,关外有探子不下五十人,皆未有回报者,你那从属是从何处打探的消息。”确如他所讲,从他来到扶苏关后,便排了超过五十名探子出关打探消息,但直到现在也没人回来汇报过。
慕北陵微咦,心想:“不会吧,五十多个探子都没来汇报如此重要的事?”猛想起张辽阔提起的黑衣人,暗地猛惊,又想:“那些探子该不会已经殒命了吧。”遂问道:“敢问大将军,探子派出去多长时间了?”
孙云浪道:“三天左右。”
慕北陵当即笃定这些人兴许凶多吉少,探子所乘战马皆军马中的上品,多为日行八百者,而且这些探子个个都是脚力了得之人,三天时间竟无一人回来报信,饶是蹊跷。想罢撩袍跪倒:“大将军,属下所言敢以项上人头担保,还望大将军早作计划。”
孙云浪听其言真意切,不像是随口胡诌,却猛然注意道慕北陵所讲,他说是他的随从打探到的消息,在此之前他都在扶苏城内,何以特意差人打探大军战事?孙云浪老目微凝,精芒四射,问道:“北陵,老夫问你,你的人为何会出现在关外?”
慕北陵心尖猛颤,暗赞好敏锐的思维。低着头眼珠不停转动,半晌方道:“属下不敢欺瞒大将军,眼下虽邬重邬里指掌关军,但属下任然心系火营,此次战事起时更放心不下纵队兄妹,所以特意派张辽阔暗中跟去,辽阔虽算不得修武大家,但也是斥候出身,对他们或许有所帮助,今日一早便是辽阔拼死来找属下,告知军情。”
孙玉英也道:“爹,北陵说的都是真的,张辽阔回来的时候浑身是血,我也亲眼见过,您还是快想想办法救四营的将士吧。”
慕北陵接口道:“孙将军所言极是,倘若我军被漠北人乘势追击,帅将逃遁,后果不堪设想啊。”
正说时,忽闻楼外“唏律律”马声传来,祝烽火几步入内,赵胜跟在其后,刚进议事堂,祝烽火怒声喝道:“狗日挨千刀的邬重,老夫把火营交到他手上还没二十日,他竟敢弃军逃跑,这次要是被老夫逮到,定要剥了他的皮。”
孙云浪道:“老将军息怒。”拉过一把军椅示意就坐。他不是不相信慕北陵说的话,只是不敢相信邬重邬里会弃军逃跑,想当日徽城之战二人已经当了回逃将,还差点因为这件事身首异处,有道是人贵自知,他如何也不相信二人会第二次做逃将。
慕北陵见其久违出言,心想:“在拖延下去恐怕时间就来不及了。”着急说道:“大将军可是还不相信属下?”
孙云浪抬手阻道:“老夫非是不信你,只是想不通邬里邬重何敢再做逃将。”
祝烽火怒道:“你想知道?那就把那两个王八犊子抓回来,一问便知。”
孙云浪知其怒气正盛,劝慰两句后斟酌分许,说道:“邬里邬重之事稍后再议,眼下最紧咬之事是先将部队情况弄清楚再说。”遂叫来左右,嘱其二人亲自出关打探,顺带看看为何五十探子无一来报。
左右护卫得令前去。
刚走没一会,厅外有声传到:“报……”一士兵连滚带爬跑进议事厅,满面惊恐。孙云浪斥其道:“何事如此慌张?”
那士兵叩头回道:“禀,禀将军,斥候,斥候回来了,正在厅外。”
孙云浪喝道:“还不快传?”
士兵急不可耐,忙道:“他,他……”接连说了几个字,皆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慕北陵目色大变,不待孙云浪出声,晃身夺出议事厅,跳下台阶登时见一人躺在台阶下,浑身血污,胸口起伏不定,俨然出气多余进气。
他跑至那人身前,抬手扣腕,度过一道生力。孙云浪,祝烽火,孙玉英等人接连出来,也见此幕,纷大惊。
那人艰难睁眼,唇齿艰难动气,呜呜碎言,不知在说些什么。
慕北陵扣腕细查片刻,感其五脏皆碎,像是被某种巨力生生震碎,能撑到现在已是奇迹。旋即猛一咬牙,暗道声:“抱歉了。”左掌压至那人胸膛,碧绿水芒轰然暴起,顷刻间没入斥候体内,包裹心脏,而后慕北陵迅速收回左手,生力化作纽带连接心脏和他左手,他左手做捏握状,规律性的握紧松开,握紧松开。
几息后,斥候陡然瞪起眼珠,“嘶嘶”吸上一口大气,精神瞬间恢复。
孙云浪遂疾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斥候艰难回道:“邬,邬里,邬重,逃,逃,跑,漠,漠北,人,追,追……”
慕北陵见其快不行了,心思一动,左掌中水芒再闪,捏动速度也突然加快。
那斥候口角便淌出鲜血,用尽最后一口力气喊道:“快,快,救,救……”话未完,暴口喷出道血箭,脖子一歪,委顿死去。生力纽带随即消失,慕北陵叹口气,敛去生力,伸手滑过斥候面庞,替他闭上眼睛。
人虽死,但所言之意众人皆是明白。孙云浪此时脸色沉凝的快滴出水来,下令扶苏关进入战备状态,亲自拉来马匹,跃身上马子初关门。祝烽火紧随其而去,走前还特意命令慕北陵主持关中事宜,准备迎大军回关。
孙玉英也想跟去,被慕北陵劝下,他道:“你爹和烽火大将军只是去把军队带回来,不会和敌军正面相碰,眼下最重要的是做好扶苏关防卫,以免被漠北敌军乘势攻入关中。”
又道:“扶苏关的防御事项你比我更熟悉,蔡勇不在,只能靠你了。”
孙玉英虽急,但也知事重轻缓,遂带集合士兵去关墙上开启防御机制。
慕北陵独自沿石梯登上关墙,行至中央高台之上。蔡勇修葺关墙特意把这方高台加大几丈。
遥看关外险峰峭岭,烽烟袅袅,似有杀声回荡关前,此一幕与几月前何等相似。然物是人非,此慕北陵已非彼慕北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