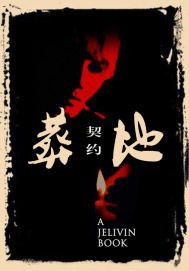李开心依旧站着没动,但谁都看得出他一脸悲怆。我猜想,那两段古怪而真假难分的骨头,应该没那么大的效应,不太可能引起他情绪的剧烈变化;即便那真是从少林前任方丈海亮身上取下来的,也早已没有生命的气息,跟一块随处捡来的冰冷石头差不多。一时之间,根本无法让人联想起海亮和尚的音容笑貌。
很显然,是南宫玄冷漠如刀的讲述,在李开心内心还原了那场遥远的悲剧。
我有点好奇,很想走过去,将两根骨头检起来查看一下。时隔二十年,那上面是否真留有人为的伤痕?但念头转了一圈,又放弃了这个想法。原因是:其一,自己行动不便,走过去得有人搀扶,我不想被人看到自己如此虚弱的一面;其二,朱玲和叶欣仍然紧紧依偎在两边,我不情愿就此脱离她们的体温和气息。
还有第三个原因,想了想,觉得这两段骨头,意义没那么重大。南宫玄的讲述,再上地上的这两根东西,充其量,就是使我的故事更为丰满,更为动听,但并不能提高哪怕一点点真实性。
实际上,我心中的质疑还未完全成形,无厘道长便比我先一步说出了口。
无厘道长哼哼笑了两声,说:“简直一派胡言。两根年代久远的骨头,是不是人骨都没法确定,即便真是人骨,也没法证明,那就是当年从海亮方丈身上取下来的。退一万步说,就算真是海亮方丈的肋骨,上面的划痕,又怎么证明,不是事后伪造的?”
我不得不说,无厘道长虽然身陷重围,但脑子依然清楚,所有这些质疑,都有一定的道理。只要这些疑点存在,当年的秘事,就只能停留在故事层面。听众中间多几个这般脑子清楚的人,再有几张爱八卦的嘴,完全可以将情节反转。
没有人搭腔,无厘道长脸上隐隐有得意之色。南宫玄嘴角挂着冷笑,并无进一步说服无厘道长的意思,连看都不去看他,两眼仍然盯住身前不远处的残肢和人骨,似乎有点依依舍,又有点如释重负。
梦遗大师的脸上,总算表现出一点点变化,眼睛半睁,盯着那两段真假难辨的骨头,嘴角微动,想说点什么却又没有说出口。最终半张着嘴,将脸上各处的皱纹挤得更深更长。苦瓜已不在再是苦瓜,像是满脸松树皮。不知他这是因为伤重难忍,还是情绪真受了这两段骨头的触动。
李开心虽然隔得比较远,但很明显也像我一样,立马捕捉到了梦遗大师的脸色变化。
李开心略微转头,缓缓向梦遗大师说道:“梦遗师兄,你有何解释?”
如果此处是个公堂,而李开心充当状师,他向犯罪嫌疑人抛出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怎么高明。因为原告呈现出来的证据,看起来离奇,却没有太强的说服力,严格来说,并不能当成罪证。梦遗大师完全可以像无厘道长一样,用一连串的反问,而将自己置于被诬陷的地位。听起来反而更加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假如身后的徒众中间,有几个头脑清楚、嘴尖牙利之辈站出来无条件支持,声势就更大了。
即便不狡辨,梦遗大师还有一个高傲的选择:一脸不屑,闭目不言。这符合他的身份和性格,同时又制造了一种真理在握的气氛。
然而,梦遗大师却作出了第三种选择。他既不沉默,也没有力图辩解,而是长长叹了口气,忽然泪流满面,缓缓地说:
“我本不想杀他的。那晚真的是个意外。”
不是辩解的辩解,无异于承认了自己就是杀师的凶手。他说完这句话,眼泪更像泉水一般势不可挡,奔出眼角,涌入脸上的每一道皱纹。片刻间,他脸上所有的角落,都被泪水充满,火光映照下,整张脸就像一块被击碎的玻璃镜。纵横交错的每一道碎片,都显得那么尖锐锋利。
身后的徒众们集体噤声。他们说不出话,脸上的神色谈不上讶异和震惊,更多的是茫然不知所措。瞬间过后,几个最先反应过来的和尚,开始闭目合什,念念有词。
李开心惨然一笑:“果然是你。最让我想不通的是,你居然能将杀师罪孽深藏内心二十年,任谁都看不出一点点负罪和愧疚。你是怎么做到的?”
李开心此话同样表明,他早就怀疑过梦遗大师是凶手,但苦于没有证据,又从对方的言行中看不出任何迹象,让他一直不敢下结论。这让他困扰了二十年,若不是梦遗大师此刻亲口承认罪行,他或许还将困扰下去。
梦遗大师隐忍二十年,在最需要辩护之际,却任凭内心的罪恶洪水般四处奔流,也许是重伤之下让他突然醒悟;也许是,二十年的忍耐已达极限,南宫玄说辞和证据,就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精心构筑的心理堤坝,二十年过去,也已老朽衰败,只需有人撕开一个微小的口子,洪水便势不可挡。
南宫玄得理不饶人,冷哼了一声:“那晚不是意外。明显是精心策划好的。无厘道长当时恰好身在少林寺,而且及时冒充李开心出手杀人,谁能相信那是个意外?”
梦遗大师再不说话。重又闭上眼睛。泪水已停止奔涌,他脸上的玻璃渣子,片片往下掉,最后,只剩下一些零星碎沫,在火光里看起来若隐若现。
进行徒劳辩解的,是无厘道长。事涉少林寺,虽然他也曾是个阴暗的参与者,但毕竟是别家之事,想必触动不了他内心深处的罪恶之根。愧疚是没有的,更别说罪恶的洪水决堤了。所以,他依旧保持着比较精明的状态。继续辩解,几乎是他压抑不住的习惯。
无厘道长:“方丈大师说的意外,是指你那封捏造的信。没有此信,当晚我不会身在少林寺,更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
南宫玄忽然叹了口气:“的确怪我那封信。”
这话偶一听,有点莫名其妙。大家一时不知他想表达什么,包括我自己。因为在此刻忏悔,不但不合时宜,也不像是他的风格。
南宫玄接道:“我不应该显得这么仁慈,只述经过不提证据,仅仅让师父心存怀疑,因而亲自找梦遗老秃驴当面对质。如果我一开始就把所有的罪恶铁证,呈现在师父面前,那么,就不存在当面质问的环节,因而梦遗老秃驴也就没机会偷袭师父。”
原来他不是愧疚,而是后悔当初没有联合师父海亮将梦遗大师赶尽杀绝。
李开心悲怆地摇头:“王兄弟说得对,虽然师父不是你亲手杀的,但你也有罪。从根本上说,是你给梦遗制造了一个杀师的心理契机。而你隐瞒所有罪证,又让师父无法给他彻底定罪,犹疑不定,所以对凶手的偷袭猝不及防。否则,以师父的本事,怎么可能被人一击而死?”
无厘道长心态依然很轻松,哼哼笑了两声:“也许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罪证。一切都是他胡编的故事,目的是达成他的野心。只不过,老天最终没有帮他而已。”
这话试探的味道很浓。铁盒子里的那封信,我逐字逐句都读了好几遍,从里面记录的两桩罪恶看来,留下罪证的可能性相当小。只不过,罪恶之事两人应该真的干过,被人描述的如此精细,不容他们不害怕。因而才无奈受南宫玄的牵制。
多年来,南宫玄一直以此为把柄,要胁少林武当两大掌门,或许都止步于语言信息,并没有真正出示过什么震憾性的东西。无厘道长估计早就嘀咕:南宫玄只不过了解这两桩罪恶,但手上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证据。否则,他怎么能隐忍二十年?
其实,不仅仅无厘道长,我自己也是这么怀疑的。李开心基本不提此事,心思应该与我差不多。
南宫玄冷冷道:“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吧?”
梦遗大师已承认杀师罪名,此刻的无厘道长差不多已成孤家寡人。而且,梦遗承认一切,无异于同时肯定,无厘道长确实暗中参与了当年少林寺的惊天变故。那么,李开心不会放过他,因为他那晚冒充自己杀了师弟梦蝶大师。
失去了少林武当徒众的道德声援,无厘道长快要陷入绝境。于是,他孤注一掷,干脆把水搅浑,否认另一桩阴暗罪恶——也就是秘信所记录的事件。一方面,是为了转移视线;另一方面,如果南宫玄此前真的不过是虚张声势,此刻拿不出有力证据,他就可以义正严词地指责对方诬陷,从而挽回一点点道德优势,获得一些死忠弟子的支持。
然后,以无厘道长的本事,今晚就可能趁混乱脱身,日后再找机会卷土重来。
相信很多人都不希望无厘道长就此脱身,特别是我自己。
我很久没插话,主要是插不进去。信口胡柴我比较在行,说到久远的真实历史,就没有我搭腔的份,只能当个安静的听众。
此时,话题重又回到铁盒子里的那封秘信,及其阴暗内容,我终于有了搭腔的资格。
我清了清喉咙,向南宫玄道:“你伪造武当前任掌门万明道长的信,引发了少林寺的内乱,导致海亮方丈的死亡。如果信里面提到的内容,你根本就没有证据,甚至是子虚乌有,你的罪过就更大了。”
南宫玄淡淡地说:“小子,这一刻,你的激将法纯属多余。”
没待我进一步搭话,他忽然提高嗓门,莫名其妙地朝天喊了一句:
“姑娘,出来吧。轮到你出场了。”
这回我彻底懵了,不知南宫玄捣什么鬼。怎么在他背后,还有人没出场?而且,听称呼还是个姑娘?秀水镇上,有什么姑娘如此神秘,如此举足轻重?
相信所有人都跟我一样茫然。而且,南宫玄这么一喊,面朝天空,于是,没有人知道那位姑娘究竟从哪个方向出场。她不可能真的从天而降吧?所以,大家的目光都只能集中在南宫玄一个人身上。
他在故作神秘?此刻生命都快要走到尽头,吸引目光对他而言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怔怔地看着他。这家伙也转过头对着我,一脸阴笑。我忽然有种感觉,他似乎不是向无厘道长证明什么,而是重新恶意地将我推到了旋涡中心。否则,他此刻不会是这种表情。这感觉让人很不爽,就像我自己有那么一段阴暗过去,快要大白天下了。
不幸的是,南宫玄的目光和表情,就像一根无形而有力的线,将所有人目光都牵引过来了。人们就像是经过排练似的,一起转头,进而一脸讥嘲地看着我。他们以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等着我的答案。
我只不过是一个多嘴的看客,为何关键时刻,却让我来承受众人嘲弄和怀疑的目光?为何我总是在不合适的时机,充当舞台的主角?而且还是迫不得已,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愿这一次是错觉。
这时我左后方传来悉悉窣窣的走路声。不止一个,而是两个。不需转头我就知道,其中一个是女孩子。她的脚步犹犹豫豫,畏缩不前。
我没转身去看后面的人。因为我伤在肩头,无论朝左右哪个方向转动比较大的角度,都会牵动伤口,我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痛得呲牙咧嘴。作为教主加帮主,那太丢人了。我宁愿故作镇定,硬生生忍住浓重的好奇心,双眼抬高,看向黑暗的虚空,对身后的一切不加理会。
我相信,身后的人一定会绕到前面来。因为那里才是今晚舞台的中心。那么,我那份好奇心的满足,只不过推迟了一会而已。
身后两人脚步越来越近,按估算,他们此时该要绕道了。从我的左边或右边绕过去,因为再走五步左右,就得撞在我后背。
然而我错了。他们还在向我靠近。没有杀气,似乎不是为了靠近攻击我。当然,众目睽睽之下,两人也没什么理由要攻击我。而且,攻击不至于走得这么慢。
朱玲和叶欣早已扭过头去,将脖子拉得老长。她们显然看清了后方来客。我从眼角余光里,看到她们脸上没有震惊,只有茫然;她们也没有丝毫恐惧或戒备之色,这就表明来客没有攻击我的意图。
来人最终还是没有绕道。两个对我而言的神秘人物,在我背后两步之外停下脚步。我不再抬头看天,收回了目光。我就算心理承受能力再好,也无法保持淡定。身了朝两边试着扭了扭,然而转头角度无论多大,依旧看不见身后两人的衣角。这让我心里有点着急。
所有人都看清了来客,只有我一个人背对着真相。这就不仅仅是心里不爽,而是涌起一种无法言说的悲伤。
我以为自己的失态表现,会引得前面那帮家伙一脸鄙夷。但我又错了。没有鄙视,没有嘲笑,并非他们忽然有了风度,而是,他们一时之间无法拭去那一脸的茫然。我这才发现,这帮家伙刚才不是注视我,而是全神贯注看我身后的两个人。
这时身后的关键人物——南宫玄口中的那位“姑娘”说话了。不是回答南宫玄,也不是回应众人的目光。她是在跟我说话。
她怯怯地叫了声:
“王大哥。”
听到这个声音,我彻底相信,自己的感觉并没有出错。所谓的证据,所谓的关键人物,确实与我有莫大关系。
因为那个在身后叫我的人,是消失已久的阿红。
我生平第一次亲密接触过的女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