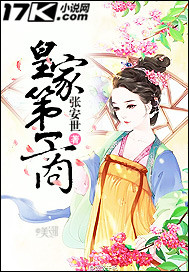喇嘛快步赶到沙子口哨卡的时候,远远地看见张彪一行人站在耀眼的探照灯下接受几个鬼子的检查。张彪转着身子让一个鬼子浑身上下摸,木头一样安静。几个人轮番被检查了一遍,没精打采地过了哨卡。喇嘛在一个雪堆后面喘了一阵气,转身向北边的一片树林走去。
钻出这片树林,喇嘛犹豫了一下,沿着树林北边的一条被大雪覆盖的山路继续往北走,从这边可以绕过沙子口哨卡。
这条路很难走,饶是喇嘛走惯了山路也不时跌跤,浑身沾满雪花,就像一只正在褪毛的白狗。
又一次跌了个四爪朝天的时候,喇嘛干脆躺着不起来了,忿忿地想,我就这么躺着,等雪化了再走,我就不信太阳总不出来。
可是想归想,躺了不到一袋烟的工夫,喇嘛就受不住了,冻得牙齿得得地碰。
喇嘛怏怏地坐起来,跺几下脚,继续往前走。
前面的雪地里突然冒出一个白呼啦的影子,喇嘛一愣,难道鬼子在这里也设了卡子?想跑已经来不及了,喇嘛索性站住了,不怕,老子什么风浪没有见过?个把鬼子奈何不了老子!这样想着,右手悄悄别到身后,想去抽张彪的那把雁翎刀,手背突然被口袋里的一件硬物蹭了一下,好家伙,特别通行证!老子的身上有特别通行证……娘的,喇嘛不禁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声,你这个大彪子啊,刚才你害什么怕?有了这个护身符,你完全可以大摇大摆地通过哨卡啊。
喇嘛正这里后悔不迭,对边那个影子发话了:“干什么的?”
喇嘛打了个激灵,原来不是日本鬼子啊,难道是乡保队的?喇嘛知道,这一带有南京政府下令组织的乡保队,他们听鬼子的,抓到崂山下来的抗战分子就交给驻守沙子口的吉永联队,一旦被抓,一般不会活过当天。前一阵子,喇嘛奉命下山找几个大户联系粮草,亲眼看见几个人赤条条地被绑在沙子口炮楼前面的吊桥上,山田亲自架起机关枪向他们扫射,他们的身体像被打漏了的水桶一般,顺着枪眼往外喷血,吊桥下面的小河眨眼之间就变了颜色。
“打穷食的。”喇嘛不敢怠慢,慌忙回答。
“打什么穷食?八路探子!”那个人双手握着一把枪,颤颤巍巍地往这边靠。
喇嘛感觉这个人有点儿色厉内荏,而且说话的声音有气无力,不像是乡保队的样子,喇嘛怀疑这是一个落了单的胡子,胆气不觉壮了起来:“招子不亮!八路探子等你过来送死?说吧,兄弟是不是‘浪飞’着?”那个人踉跄几步,一下子扑倒在喇嘛的脚下:“大哥,行行好,给点儿吃的吧……”喇嘛大吃一惊,下意识地揪住他的头发将他的脸仰了起来,好嘛,这家伙竟然是刘禄!
喇嘛知道前天上午仰口那边遭遇了董传德的围剿,刘禄应该是漏网之鱼吧?看他半死不活的样子,这家伙应该是两天没有吃饭了吧?喇嘛撒开手,刘禄闷声不响地歪躺在了地上。喇嘛有心想走,转念一想,这家伙在东北的时候对我和传灯也算是有恩,这当口丢下他不合适,没准儿我这一走,这家伙转眼就变成冰棍了……“起来,跟我走,我带你去找吃的。”因为身上带着通行证,喇嘛这话说得底气十足。
这个声音好生熟悉……刘禄将灭的脑子蓦地亮起一点光,艰难地抬起头,一怔,哽咽两声,呜呜地哭了:“亲娘啊,怎么是你呀……”
“别喊亲娘,喊亲爹,”喇嘛拧一把发酸的鼻头,用力架起了刘禄,“你从哪儿来呀,这么狼狈。”
“别说了,别说了……”刘禄回光返照似的挺了挺软绵绵的身体,“仰口厮杀,大禄子七进七出,我是九死一生啊……”
“九死一生那也是给疤瘌周卖命,”喇嘛有些上火,“你从仰口那边过来?”
“不,不是……”刘禄的喉头咕噜几声,蔫蔫地说,“跟你说实话吧兄弟,仰口那边打起来之前我就离开了。本来我想去你们山头找传灯,可是谁知道半路上被董传德的人给抓了……那什么,我,我就给疤瘌周使了个坏,把仰口的情况告诉了他,后面接着就出事儿了。董传德这个人还算不错,放了我……我不敢回仰口了,就去了下街,实指望能在小炉匠家躲上几天,谁知道又碰上了疤瘌周……对了,汉杰,你们家出事儿了,我看见疤瘌周和小炉匠去了你们家,老掌柜的可能已经死了……在这之前我就知道,疤瘌周想逼迫小炉匠去杀了老掌柜的。汉杰你别说我在跟你表功,一个多月前我去见过老掌柜的,我把这事儿对老掌柜的说了……”“慢着慢着,”喇嘛出了一身冷汗,“刚才你说老掌柜的已经死了,怎么回事儿?刚才我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我没亲眼看见……”刘禄痨病鬼似的喘息一阵,嘶啦嘶啦地说,“我看见疤瘌周和小炉匠去了大车店……”
“操你妈,你咋不早说?”喇嘛丢下刘禄,撒腿就跑。
“喇……汉杰,行行好,给我口吃的吧……”刘禄跟着跑了两步,把持不住身子,一个马趴跌在了雪地里。
喇嘛回转身来,犹豫一下,反手拖起了刘禄:“跟我走!咱们一起去下街。”
刘禄吭哧吭哧地喘气:“下街,下街……俺不想回下街了。你就给俺口吃的,俺死也要死在崂山,哪儿也不是俺的家了……”
喇嘛拖着他继续走:“你必须跟我一起回去,我干爹万一真的死了,你必须证明这事儿是疤瘌周和小炉匠干的!”
“我……亲娘啊,刚才我还不如别碰上你呢……”刘禄踉踉跄跄地跟着喇嘛走,就像拖在喇嘛屁股上的一溜鼻涕。
“妈了个逼的,你整天跟疤瘌周在一块儿,为什么不替咱爷们儿‘插’了他?”
“我,我他娘的有那个胆量就不叫刘禄了……”
“疤瘌周现在去了哪里?”
“我也不知道……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一看见他们进了大车店,心里害怕,先‘滑’了……”
“你他娘的‘滑’的可真是个时候!你估计这工夫他会去哪里?”
“难说啊,”刘禄艰难地咽了一口干唾沫,“仰口完蛋了,也许他不会回来了,也许他直接在沧口当汉奸了……汉杰,我实在是走不动了,赶紧找个地方给我弄点儿饭吃……”“你他妈一个胡子出身,我就不信你连自己的口都糊不住,”喇嘛拖着他继续走,“你就不会找户人家进去糊弄两口?”“我敢露面吗?”刘禄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本来在下街我想先弄点儿吃的,一慌,全忘了……赶等来了崂山地界,我他娘的又饿又困,快要变成干巴屎了……在沟底下睡了不知多长时间,饿醒了,有心想要拿枪闯个‘窑堂’啥的,一想,哪儿敢?这边全是乡保队,我身上又没带特别通行证……哎,我给你的通行证还在吧?”刘禄一下子精神起来,“咱们这就去沙子口找家饭馆大吃一顿!”
喇嘛摸了摸口袋,瘪瘪的,冲刘禄翻了一个白眼:“你有钱?”
刘禄掂了掂手里的枪:“这不是钱?”
“去你娘的,说来说去你他娘的还是一个胡子!”喇嘛拖着他继续走,“前面有个村子,我进去‘顺’点儿干粮。”
“‘顺’?还说我呢,贼跟胡子是一个娘养的……”刘禄有气无力地嘟囔了一声。
果然,两个人跌跌撞撞地走了一阵,前面出现一个黑黢黢的村庄。喇嘛将正处在僵尸状态的刘禄抱到一个雪堆后面,叮嘱一声不要随便出来,悄悄往村里摸去。走出去老远,刘禄才在后面幽幽冒了一句:“我一个快要死的人了,能随便动弹?你比我还‘彪’呢……”
不大一会儿工夫,喇嘛手里捏着一块苞米饼子跑了回来。
刘禄已经不能说话了,两只手划船似的扒拉喇嘛拿饼子的那只手。
喇嘛将饼子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蘸着地上的雪,一块一块往刘禄的嘴巴里戳。
走路不行,吃饭倒是刘禄的真本事,不到一分钟的光景,那块饼子就不见了踪影。刘禄的嘴巴搁浅的鱼也似冲喇嘛一张一合,好像有什么要紧的话要对喇嘛讲。喇嘛抓起一把雪,在手里捏成窝头似的一个小团,猛地塞进刘禄的嘴巴。刘禄张口咬住,喀嚓咔嚓嚼了一阵,终于将那句憋在胸口很长时间的话吐了出来:“还有没有了?”
喇嘛没好气地哼了一声:“庄户人家这年头都不富裕,把人家的口粮都拿走了,很不厚道呢。”
刘禄估计暂时也就这么着了,干脆跟了一句:“对啊,孔夫子说,盗亦有道。”
喇嘛抿一把裤腰,又来拉刘禄,刘禄竟然动作麻利地站了起来:“走,咱们去下街!”
这倒真的应了那句古话,人是铁饭是钢……走在路上,喇嘛蔫蔫地想,要是刘禄不在路上遇到我,怕是真的要当饿死鬼了。忍不住冲装模作样打饱嗝的刘禄笑道:“这些年跟着疤瘌周,你没吃几顿饱饭吧?”
刘禄的脸上泛出不堪回首的痛苦表情:“饭倒没什么,脑子遭罪……别提他了,一提他,我这心里就发冷。”
喇嘛站住,前后打量了几眼,点点头:“凭什么做贼似的走这样的路?走,上大路,去沙子口!”
刘禄跟着喇嘛走了几步,蓦然停下了:“不能走沙子口……还记得去年的你跟传灯被抓的事儿吗?那边很危险。”
“危险找不到老子的头上啦,”喇嘛继续走,“现在咱们有护身符,鬼子拿咱爷们儿当兄弟对待呢。”
“当心点儿好啊,”刘禄还在迟疑,“我担心这个证件过期了呢……鬼子经常换通行证,怕的就是汉奸通匪。”
“谁是匪?”喇嘛一瞪眼,接着笑了,“你说的也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我算是草鸡了……那就继续走山路。”
刘禄说声“汉杰是个明白人”,跟着喇嘛重新上了那条小路。
两个人不再言语,闷着头疾走。
月亮被乌云遮盖了一阵,幽幽地又冒了出来,小路泛着蓝幽幽的光,远处的大山也亮着,像一条蜿蜒的银蛇。
喇嘛腿快,渐渐将刘禄落在了后面。
刘禄在后面咳嗽了几声,见前方没有动静,顿一顿脚步,嗖地蹿到了路边的一条小沟里。
在沟里猫了片刻,刘禄探头望望前方,喇嘛的背影已经变成了一个苍蝇大小的黑点。
刘禄叹口气,紧紧裤腰,手脚并用,爬出小沟,沿着白茫茫的一片雪原往崂山的方向蹿去。
接近沧口地界的时候,喇嘛望了望天,晨曦透过云层,隐隐约约地显露出来。回头望望,哪里还有刘禄的影子?走出崂山地界的时候喇嘛就发现刘禄不见了,以为他走得慢,等了好长时间也没等到刘禄跟上来。喇嘛想,也许这小子又饿了,找吃的去了呢,我还是去下街等他吧。快要走到了下街,刘禄还是不见踪影,喇嘛失望了,怪不得大家都喊他叫刘二彪子呢,他可真是“彪”得不轻,跟着我总归不会吃亏,等我回崂山,他不是就有了落脚点地方?在心里呸了一声,喇嘛快步往顺丰大车店方向走去,满脑子都是娘的影子,他担心刘禄说的是实话,干爹死了,娘也许也跟着遇难了……我到底是不是姓徐?脑子里突然冒出这个问号,喇嘛一时不知道自己的根到底在哪里了。
身上揣着“护身符”,喇嘛的胆气很壮,一路疾行,竟然有些大摇大摆地意思。
刚刚迈上下街学堂南边的那条小路,喇嘛就被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吸引住了。几个人从学堂西边的那条胡同里跑出来,一个个脸色仓惶,像是受了很大惊吓的样子。
喇嘛不由自主地迎了上去:“乡亲,发生什么事情了?”
一个脸黄得像贴了一层黄表纸的汉子回头指了指大车店的方向:“徐老爷子家出事儿了……”“什么?”喇嘛的头皮阵阵发麻,难道刘禄说的真是实话?两腿一软,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黄脸汉子仔细打量几眼喇嘛,掩口惊叫:“你,你不是徐家干儿子徐汉杰吗?”三步并作两步过来拉起了喇嘛,“赶紧逃命去吧!日本人连你妈也抓走了……他们说,你是个抗战分子,你妈是个匪属……”“我妈还活着?”喇嘛跳起来,一把揪过了黄脸汉子,“我干爹死了?是不是小炉匠杀了他?”
黄脸汉子懵懂着嗫嚅:“小炉匠?小炉匠怎么会……徐老爷子没死,他也被日本人抓走了,还有你儿子,你儿子也被他们抱走了。”
喇嘛的脑子一下子乱了……
“你还是赶紧走吧,”黄脸汉子掰开喇嘛揪着他前胸的手,“大车店门口全是日本鬼子和汉奸。”
“我凭什么走?老子现在是……”喇嘛晃一下手里的特别通行证,撒腿往大车店方向跑去。
大车店门口果然围着一群人,人堆里有一个汉奸模样的人在跟围着他的人说着什么,然后推开一条缝,走到街门东边,刷刷地往墙上贴一张告示。喇嘛不认识几个字,灵机一动,将帽檐拉低,钻进人缝,将特别通行证在那个汉奸的眼前一晃,拉着他走了出来。简单问了几句,喇嘛放心了,干爹没死,娘目前也安稳着……那个汉奸告诉他,昨天半夜,夜袭队来人想接徐老爷子一家人出门,正忙着收拾东西,墙头上钻出一条黑影,黑影冲着里面大喊,不许带我爹走,我是徐传灯!接着就朝里面开了几枪,然后跳下墙头,一溜烟地没了踪影。夜袭队的人刚要出去追,就被闻声赶到的宪兵队堵在了门口。山田对领头的张彪说,我们刚刚接到举报,这户人家通匪,你们不能带他们走……
原来,这一切都是周五常策划的。
昨天夜里,周五常杀掉小炉匠之后,打定了主意,先去宪兵队找山田,告诉他前面发生的一切,然后把徐传灯参加了抗日武装的事情告发,让山田亲自处决徐正义。找到山田,周五常将事情简单说了一下。实指望山田会直接带人过去抓人,可是周五常失望了,山田沉吟了半晌,抓起电话跟吉永太郎咕噜了一气,阴着脸让周五常离开宪兵队,立刻回仰口。周五常感觉十分没趣,他搞不清楚山田和吉永太郎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在小炉匠家闷闷地睡了一宿,第二天早晨过去看大车店的动静,大失所望,大车店里平静如常,什么也没有发生。
周五常不甘心,又去了一趟宪兵队,没等开口就被山田骂了出来,命令他即刻赶往仰口。
也许是吉永太郎念及徐家曾经收留过他的弟弟妹妹,不忍心动他们?周五常胡乱揣测,好像不对呀,据说吉永太郎为了自己的信仰,连亲妹妹都处决了呢……不行,你们不杀徐正义,就乱了我的计划!徐老爷子,对不住了,既然没人杀你,老子就亲自动手吧!
在小炉匠家闷坐到半夜,周五常翻找出小炉匠用过的一把破撸子枪,贴着墙根往顺丰大车店的方向摸去。
刚刚接近大车店,周五常就愣住了,他清楚地看见张彪带着几个兄弟进了大车店,不一会儿就传来搬东西的声音。
周五常感觉纳闷,张彪怎么会帮徐正义出逃?
皱疼了眉头,周五常也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不管这些了……周五常想,张彪现在也是吉永那条线上的人,不管他此行的目的在哪里,我要是亲自出马阻拦的话,一是容易造成误会,二是万一惹毛了张彪,自己怕是要有麻烦,干脆我冒充徐传灯回来救爹……这样一来,日本人不抓徐正义也得抓了,他们总不能眼看着抗日分子在下街捣乱吧?那样下街可真的就乱了,把心一横,纵身蹿上了墙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紧要关头,山田带人出现了。妈的,山田小鬼子原来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周五常感觉自己闯了祸,趁乱溜了。
张彪见山田横空出现,不敢硬抗,只得敷衍他说,自己侦察到这户人家通匪,想要立个头功,既然皇军亲自来了,那只好让出来了。山田似乎看出来张彪的真实目的,一时又不敢确定,挥挥手让他走了。
“照这么说,这家人一个也没死,都被抓去了宪兵队?”听完,喇嘛问,心中竟然有一丝轻快。
“没死。估计墙头上冒出来的那个人不是徐传灯,徐传灯是不会朝他爹开枪的……”
“老人伤着没有?”
“没有。那把枪太破了,没有准头,一颗子弹崩在张彪的大腿上,一抠就出来了。”
“老徐一家会被送到哪里去?”
“你问这么多干啥?”汉奸警觉起来,上下打量喇嘛,“兄弟你很面熟嘛,你是?”
“你问得也不少!”喇嘛冲他一晃通行证,转身离去。
沿着大街往宪兵队方向走了几步,喇嘛停住了脚步,不行,我不能呆在这里了,我必须去找张彪商量一下,也许他有办法知道干爹和我娘被押在什么地方,一旦知道地方,我马上回崂山通知大哥,尽快派人解救他们。
没怎么费劲,喇嘛就找到了正躺在夜袭队队部炕上发呆的张彪。张彪一见喇嘛,腾地从炕上跳了下来:“你怎么来了?”喇嘛将张彪的雁翎刀放在他的跟前,说:“我来给你送家伙,顺便来找玉生,想让他帮你去接我干爹他们……”“打住!你是不是已经知道大车店发生的事情了?”张彪一把揪住了喇嘛的衣领。
“知道了,”喇嘛不动,任由张彪揪着他乱摇,“你没把事儿办成。”
“我……”张彪颓然松开了手,“啥也别说了……是周五常在捣鬼!我亲眼看见他了。”
“我分析也是他,”喇嘛坐到了炕上,“这事儿你有什么打算?”
“抓周五常!然后救传灯他爹和你娘……哎,操你妈的,我有什么打算关你屁事?你有资格跟我这样说话吗?”
“都什么时候了还论资格?”喇嘛苦笑一声,“你是我的亲哥哥……”
“喇嘛,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娘到底……”
“我真的不知道这事儿,”看着张彪痛苦不堪的脸,喇嘛的鼻头一酸,“我娘也……”一时说不下去了。
张彪瞪着喇嘛看了许久,摇摇头,叹了一口气:“你娘是不会有事儿的,我知道她被押在了哪里,我会帮你想办法的。你知道不?小喇嘛,就是杨文的孩子死了,我亲眼看见山田拎着他的两条腿,把他撕成了两半……”“山田,你好狠毒啊!这么小的孩子……”喇嘛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彪哥,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必须跟我们一起调转枪口跟小鬼子拼命!”
“我是不会听你的吩咐的,”张彪横了他一眼,“老子自己有头脑,谁也别想控制老子。”
“我娘被他们押在什么地方?”喇嘛不想跟他纠缠这些事情了,脑子里全是娘那张满是皱纹的脸。
“你娘跟传灯他爹用手铐连在一起,被鬼子押着往俾斯麦兵营那边去了。”
“俾斯麦兵营?”喇嘛吃了一惊,“你不是说你娘也被押在那里的吗?”
“我娘不在那里了……”张彪的眼圈像是突然被红笔描了一下,“我去过那里,没有人见到过她,也许她真的不在人世了。”
“不会的,不会的彪哥,小鬼子控制你娘就是想通过她控制你,他们是不会杀她的,他们不会那么傻……”
“但愿如此,”张彪的喉头咕噜了一下,“你回去吧,回去告诉关成羽和徐传灯,不用担心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会帮他们处理的。”
喇嘛用力憋回了自己的泪水:“彪哥,全看你的了……我随时会回来跟你联系,必要的时候,我们一起……”“滚你妈的,”张彪抓起自己的大刀,猛地踹了喇嘛一脚,“我张彪做事儿还需要别人帮忙?回去告诉关成羽,十天之内不把人给他送上山去,我砍一只手给他!”
喇嘛倒退到门口,想说声谢谢,说出口来的竟然是一句:“彪哥,一心向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