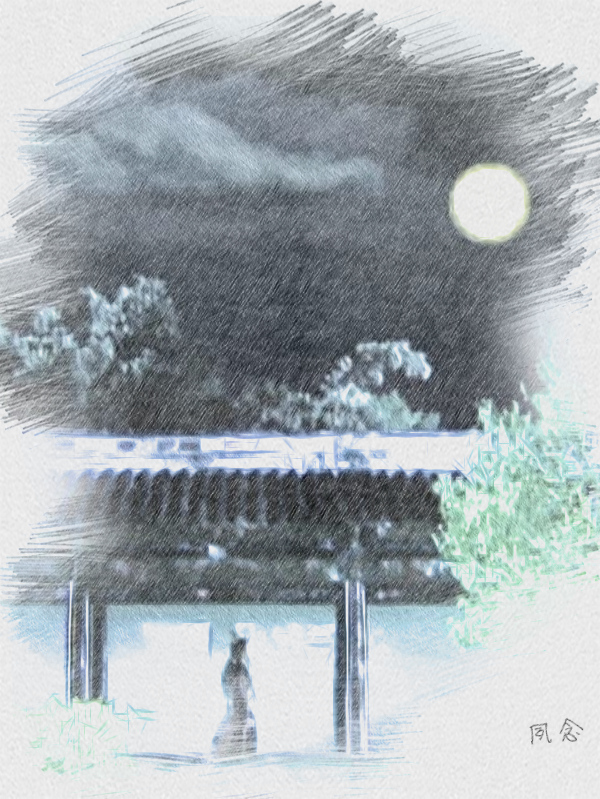第二日,李承祖一见李武便问:“交代你的的事办的怎么样。”李武“嘿嘿”一笑,得意说道:“自然是办妥了,我是亲眼见着那信到了那知州手里。”
“哦,你是怎么做的”李承祖奇怪,你还看到了,难道你是光明正大的送上去的。李武拿出一把弩机往桌子上一放,说道:“我往他边上射了一矢,哈哈,那老小子,差点连屎尿都吓了出来。”
李承祖此时正在喝茶,听到这句话,激的一口喷了出来,他摸嘴说道:“谁让你这么做的?”李武被指责的莫名其妙,抓着头不解道:“公子,不是你让我要把信亲送到那知州手上,还不让他发现的嘛,我都是按照你的吩咐做的。”
“你这是害我,不是让你不要做的太过,你如此戏弄,那老家伙万一恼羞成怒,再带人杀回来可就不妙了。”李承祖有些气这个莽夫,真是个猛张飞,光长肌肉,老闯祸。
刚好乔玉往这里经过,听到他们对话,“扑哧”一下笑了起来,掩嘴道:“好言劝你不听,这下着了道了吧。”
“啊”李武知道自己闯祸了,忙急道:“公子,都是我办事欠思考,这如何是好,要不把人移出城吧。”
“先不急”李承祖此时也冷静下来,他吩咐道:“你去知州衙门那里盯着,如有异动,马上回来禀报,记住了,此次可不要乱来。”
李武哪还敢造次,马上就去办事了。盯了一上午,那州衙门照常办事,该审的审,该判的判,州军也没有调动。
李承祖放下心来,,看来这老大人还是含的住气。下午他们依例要跑马去城外,自从有了上次袭击,他身边都要多带些保镖,因此他还带了李家兄弟和马宝。李忠从马厕里牵出马匹,拉到前门,伺候他上马。
李承祖绕过马身,踏着马蹬上了马,从李忠手上接过马鞭子,道声“走了”,一鞭子抽在马屁股上,那马受激跑了起来,还没走几步。
李承祖感觉眼中忽然有道虚影飞过,接着他下面一轻,人整个从马上栽了下来,这一下摔了个狗爬屎。
李武等人大惊,忙肋住马跳了下来,马宝匆匆上前将他扶起,关心道:“公子,没有事吧。”
李承祖摔的头晕眼花,面上磕青了一块,狼狈至极。对面王府的门人看了正着,都忍不住在那哈哈大笑。
李文上前问道:“公子怎么样了。”
“不碍事,只是这手有些折到了。”由于下马的时候,他本能用手撑地,这个手受力最多,现在还钻心的痛。
李文赶忙把他手拿住轻捏了几下,说道:“还好并没有伤到骨头,亏的这马是刚起步,不过公子你怎么会摔下马来。”
“我也不知,只感到这坐下突然松动不着力,人就摔了下来了。”他若有感触的说道。
几个顺着话,都看那地下,那边上还坠着一个马鞍。马宝走去将它拣起,拿过来说道:“怪事,你们看,这系挂居然断了,这是怎么回事,上马前都还是好的。”
几人看着那断挂都很奇怪,李武拿过看那断口,说道:“这分明是被利器所断,到底是何物。”他们从军多年,多器械这类很敏感。
这时后面一个声音说道:“这马鞍的挂带是被人射断的。”说话的是李忠,他手上拿着一只长箭:“公子请看。”
这是一只红铀杆箭,箭头是精铁打造,尾翼均匀,不是普通的猎箭,李忠指着这只箭道:“就是它将公子马鞍射断的。”
“什么”李武暴脾气犯了:“谁要暗算公子。”那边王府的人还在嘲笑,甚至有的人喝道:“骑不来马就不要显摆,摔死了可怨不得天。”
“你姥姥”李武大怒,声如雷霆:“那边几个守门的,笑你球,满嘴喷粪,快从实招来,你们哪个暗算我家公子,否则你家李爷爷打断你们的狗牙。”
他怒发直冲,钢须倒竖,再加上瞳眼圆睁,直如那怒意金刚,把那些小厮都吓了一跳,都禁了声。
更为冷静的李文拉了他一下说道:“兄弟,勿躁,这肯定不是那些小厮所为,要在人骑着跑的马上射断那鞍带,且不伤人分毫,这射术何等精良,就是你我也不及啊,就那几个废才,有这本事。”
“说的也是”被李文这一说,李武也觉得太高看那几个守门的小厮,他迷糊问道:“伤鞍不伤人,是谁戏耍公子。”
“自然是刘知州”李忠开口说道,他递出两张纸:“这是绑在箭上的,忠先打开看了,一封是信,还一张是兑票。”
李承祖拿过一看,一张是两千贯的兑票,一张上只有两个字“放人”。他将那纸撕碎,恨恨的对李武道:“报复来的太快,忠叔,我可是替你担过了,这样射技术,定然是他从军中找来神射手。”
李武听的羞愧不已,目光血红,两只拳头捏的疙瘩响。“我去杀了那狗官”他脾气一来,就要冲动的犯事。
李文忙一把死拉住自己弟弟,骂道:“兄弟,你就别再给大伙添乱。还是听公子怎么处置。”
李武身体一软,一个有岁数的铁血汉子居然哭了起来。李忠大是头痛,劝了几句,几个人往回走。边走边问李承祖:“公子,钱也收了,接着怎么办?”
李承祖揉着自己脸面说道:“说话算话,我们不做食言小人,钱到了,马上放人,忠伯这事你带人去做,就这样…….。”
李承祖亲自交代,李忠听的额头冒汗,犹豫的说道:“公子,如此不好吧,这一报一回的何时了。”
“他不罢休,我奉陪到底就是。”
```````````````````````````````````````````````````````````````````````````````````````````````````````````
隔日清晨,天刚拂晓,这街面上还冷冷清清,大部分人都还在被窝暖着。只有那些早起的小媳妇,或伺候公婆,或者挑水洗衣服。
打鸣十分,一将民屋开来,里面走出一个清秀的小媳妇,他布衣钗裙,一副妇人打扮。这正是屠户范大肚子的媳妇。
这范大肚子娶的媳妇漂亮,远近的人都经常打趣他,因此也对自己老婆疼爱的紧,平时有什么活也舍不得她做。无奈她老娘是个挑剔的人,硬要喝那易河里的水,还要媳妇亲自去挑。这老婆和老娘谁也不敢得罪,何况这老娘要是不高兴,到时候闹的要休妻子,那可就麻烦了。大宋可是以仁孝治天下,不象现在,这婆婆对媳妇可是有绝对支配权,所谓多年媳妇熬成婆,这媳妇在婆婆之前都是熬的。
所以这范家媳妇每日都要早早起来,步行十几里到易河去为婆婆挑水喝。此时她象往常一样挑上两个木捅,出门去为婆婆打水。
他门家紧邻街中,不远就是易州州衙,平时她每日都要往衙门跟前过。今天她没走多远,越离衙门还有十几丈的路上发现一个很大袋子被仍在那里。
范家媳妇放下挑桶,向四周看了看,这一大早,谁会掉了东西在这里。她想着路不拾遗,看了看想走,但到底忍不住好奇。
这么大个袋子里面装了什么,这小娘们又向四周望了望,见没人,便大着胆子靠近了袋子,看那袋口被用绳子扎紧了,就伸出自己将它解开。
然后她将袋口张开往里一瞧,顿时“啊”的惊叫一声,那袋子里面居然是一个裸体的男子。范家小娘子是他人之妇,哪有这样事情,说出去有违礼教,这人裸身在此,分明不轨。
她脑子一晕,浑然忘了他是被人绑在袋子里的,就尖着嗓门大叫了起来:“淫贼,有淫贼,非礼啊。”
这一声尖叫,在这宁静的早晨是格外的刺耳,一下就惊动了整条街面,这范家娘子声音太熟悉了,本来这范小娘子长的不错,平日就有一些地痞调戏她。她这一喊,平日提防的范大肚子就怒了,抄起跟棍子就冲了出去,那些街坊邻居听到这喊声,也都出来了,提棍的提棍,拿扫帚的拿扫帚,什么秆面仗,棒槌都来了。男男女女好几十人,往那出声地方赶。
那袋子里装的刘公子,他被塞进袋子,自己也不知道被带到什么地方。等到好不容易从见天日,面前却是一脸受惊的女人,还在那尖叫,那嗓子,没半耳膜震破。
他知道自己没穿衣服,本能就缩回袋子,本来还想好言去劝劝那女子,让他给自己抱个信,哪知道这女人喊起淫贼来。
这可苦了刘公子,自己这样子怎么说的清楚。他一咬牙,乘着现在没人,还是跑吧。他爬出袋子开脚想跑,拿知道他脚上连着绳子,这一动差点摔倒。
这一耽搁不要紧,那边大部队都敢来,这一景象落在众人眼里就不一样了,一个尖叫的妇人,一个裸身欲跑的男子。这一副场面顿时让想象力旺盛人有了发展的空间,连衣服都脱的如此干净,摸不是事情都已经完了。
有些不怀好意的人,都把目光看向了范大肚子,那眼力都已经满是笑意,就差没说在嘴上了。
自以为带了绿帽子的范大肚子怒火中烧,拿着棍子大叫着冲上去:“该死淫贼,我杀了你。”
刘公子见一个大汉拿着棍子凶神恶煞冲上来,知道糟了,忙张口解释道:“这位壮实,都是误会,听我解释。”
“我解释你娘个屁”范大肚子,直接一棍子敲在刘公子身上,顿时他发出杀猪一样的喊叫。
平时那些觊觎范家娘子美色的人此时也不是滋味,平日里想占点便宜都不可得,现在好,人家胆大的把花都拱烂了。
他们越想越怒,也高叫着:“打死这淫贼”冲了上去,这些人一加入,其他街坊也都加入进去殴打大军,一时棍棒扫帚齐飞,把刘公子打的抱着头,蜷缩着嗷嗷直叫。
那范家娘子直到此时才清醒过来,细想了下过程觉得不对,她终于想到刘胖子是被绑在那袋子里,知道是自己一时情急弄错了。
一看那么多人都在打那袋中人顿时急了,如果是个淫贼打死了也就算了,反正奸邪都不得好死的,但是如果是打错了,那大家都有官司。
她着急了,扑到人群里,看到自己那卖力殴打的丈夫,冲上抱住他的腰,哭道:“别打了,别打了,弄错了,弄错了,他没有对我怎么样。”
众人被她一闹都停了手,但是看她的眼光都有异样,甚至有人窃窃丝语:“莫不是这人本事好,弄的那范小娘子快活,她舍不得了。”
“什么,搞不好就是那范小娘子的姘头,我说范大肚子那熊相,怎么能收的住她的心。”
“平时看她对范大肚子,还以为是节妇,原来也是个**。”
这些私语都是难听的话,很多都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嫉妒语气。说的那范家媳妇脸色煞白,落在范大肚子耳朵里更是让他颜面尽失。
他一把将他媳妇推倒在地,咆哮道:“贱人,做出这样下贱之事,丢尽了我的脸面,说他是不是你奸夫。”
范家娘子满脸泪水,从地上爬过去,抱着范大肚子腿泣道:“当家的,我没有,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我和这个人根本不认识,他没有把我怎么样,你们弄错了,你们相信我,是弄错了。”
旁边一个妇人冷笑道:“弄错了,一个大男人光着身体在这街面上,你又是这副模样,说出去谁信,难道这男人是疯子,自己把衣服脱了。”
“就是,说出去谁信”很多人都点头附和,范大肚子面色更难堪了,怎么多人指认,自己老婆还一在维护,分明就是有**,想到自己平日对她百依百顺,她却如此对待自己,心中更加委屈。
“贱人,待我打杀这奸夫,再杀了你这个**。”怒的一脚将范小娘子踢开,起棍又要再打,却听到一声喝:“住手,你们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快让开?”
只见几个带刀的兵丁在往人群里挤,原来这边聚了那么多人纷扰,惊动了那边州衙的守兵,他们过来看发生什么事。
等进了人群,那些围殴的人都在说打淫贼。领头的军门分开众人,带人一看。虽然那刘胖子此时被打成了猪头,但这位常在州衙门前站的军门还是认出来了。
他惊叫一声:“公子,公子,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此时胖子相当,浑身不成人型,头上也没了神智,再打下去都要挂了。被这些兵丁扶起,他迷糊的断续道:“你,你们,敢,敢打,本公子,我。”然后头一歪,他就晕了过去。
那军门大吃一惊,马上道:“你们几个,马上把公子抬回去。”他看到这刘胖子身上**,就把他从新塞进袋子,几个一抬弄回去。
几个手下抬走了人,但是刘胖子这身伤不能这么算了,都是眼前人打的,于是他威严转身怒道:“刚刚谁打的公子通通抓回去。”
但是他此时才发现刚刚一群人,此时在现场就剩下几个了,而且手上还没东西。原来,这军门喊出公子时候,狂热的人群就知道要糟糕,才想到那袋子,大家顿时知道乌龙了,机灵的脚底抹油跑了,迟钝的看到人家跑,也跑了。就是刚刚还一副要决裂样子的范家夫妇,此时也一起跑了,只留下几个自认没动手的在那看热闹。
这军门大怒,跑的倒快。他也不是真要抓人,只是要找几个人把这罪交代了,总不能说不知道谁打了公子。
那么现在的人走了,就把在场几个抓起来,他手一挥:“把这些人都抓起来。”几个兵丁就不客气的把几个看热闹的人抓了起来。
几个人叫起屈来:“这位军爷,咱是冤枉的,我们没打公子,都是在旁边看。”
那军门一口唾沫吐道:“看别人打人也不劝阻,还看热闹,也不是什么好鸟,再说了,公子在这里被打,你们都在场,都脱不了干系,有冤到衙门说去,爷只管抓人。”
这群兵丁不由分说,拿着刀枪就开始赶人,这几个看热闹正好都是些小年轻,胆大心粗,这些兵油子也不客气了,稍不听话,就又踹又踢的,此时一个老妇人冲了过来,一把抱住一个年轻小伙子,在那里大哭,对着那军门磕头说道:“军爷,我家小子不懂事,平日胆小,借他三胆子也不敢犯法,您就饶他一回,老婆子给您磕头了。”
她点头如捣米,神色凄惨,让人看之心生怜悯,但那军门却是铁了心,一拨那老妇人,骂道:“老婆子,你家儿子胆小,这样场面还看热闹,唬谁呢,劝你别阻拦爷们公务,不然连你一起抓了。”说完扬长而去,只留下那小年轻长长的叫娘呼唤声。
旁边一干百姓看的唏嘘不已,那些刚刚参加了围殴的人更是暗呼好陷,要不是跑的快,刚刚抓走就是自己了。人群里一个老头子猛拍了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一下,骂道:“小畜生,看到没有,亏的叔公我拉了,要是你刚刚硬要上去凑热闹,你也跟那些人一样,现在都到州大牢里蹲号了。”
那小年轻擦了一下额头汗,心有余悸的说道:“叔公说的是,我还要多谢叔公,刚刚真是吓死我了,这些兵子,怎么乱抓人。”那老头冷哼一声道:“你知道什么,我刚刚算是认出来了,那是刘知州公子,打了他,百姓还有好果子吃,当官的哪个不为自己。”
大家都竖的直,把这话听的清楚,参与的人全都心理大惊,知道闯大祸了,无不在心里求神拜佛,希望不要找到自己头上来。这知州公子裸身被打,兵子混乱抓人的事也就传开来。当即有一位儒生听到此事气愤不已,发议道:“这位公子裸身街头,行为不检,遭打怨不得别人,那些官兵不问原由胡乱抓人,当真是苛政猛于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