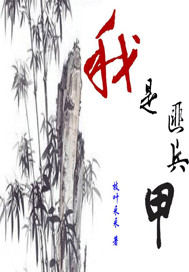一灯如豆,这暗室并没有调的很明亮,摇曳的荧火下,白发老翁凝心神于笔尖,抬臂运腕,自有一股文雅之气。但若是看了老者的笔下之物,大凡儒家门徒都会大失颜面,那上面画着个赤 裸的胖子,捭着臀瓣的近景。
最后重重的落下一笔,老者身形都摇晃了一下。他实在忍着恶心,想他唐唐一老儒,居然给男人画那丑处。他画了这幅画是心神惧累,瘫在石椅上,有气无力说道:“画好了,大王,老朽实在不能再画了。”
李承祖接过画,打眼过了一片,轻松说道:“老丈画技果然不俗,刘公子让你画活了,但是还不能让你走,某还缺两副画。”
老者一听还要画两幅,身体一挺,急了,喊到:“大王,老朽年老体弱,三幅已是两股战战,手臂细软,就是死也再画不出了。”
“哎,老丈莫要惊慌”李承祖安抚他道:“我也知道老丈劳累了,再说今日天色已晚,今日就此歇住,你随我们来,用些饭食,好好歇息一晚,明日完了其余两幅,某家就放了你主仆,决不食言,老丈看如何。”
“这”老头犹豫了下,也只能无奈道:“任凭大王做主。”在这样的处境下,他哪还有什么说话权利,老头是明白人,这事摆明了就是没选择的。
“如此,来人,把他眼睛蒙上”李承祖对旁边吩咐了一下,早等在一边的马宝,拿着一跟黑色绸带,将老头的眼睛蒙扎实。李承祖再跟他耳语,示意他押到柴房去。
将老头带走后,李承祖让李忠收拾东西,他自己把第三幅画装好。然后好整以暇的对胖子道:“刘公子,今晚就要委屈你了,在此将就一晚。”说完他对余人一挥手:“我们走。”
“大王且慢啊”胖子连衣服也不待穿上,就急着叫住了他们。胖子现在是彻底清了,这些匪人肯定不是要杀自己,那他们对自己这些竭尽的侮辱,甚至画裸画,在他看来就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这些匪人是要把这些东西做为要挟之物,用来控制自己。
胖子分析很自信,一般来说也是最合理的解释,他是知州公子,如果是些强匪贼人,要挟控制了他,那在易州地面上干些非*勾当那是轻松的多。这也是胖子前面主动提出做内应的因由。胖子是纨绔,但不是草包,他能混成这样不仅仅是他老爹的地位,象他这些受过教育的官宦之后,比常人就更懂深浅。他认为自己有价值,而画这些裸画,只是这些巨贼比他想象的狡猾,这就是个把柄。
他压根就没想过是有人要整他,他的思想还没达到这种先进地步。只能说他定位错误,或者说李承祖他们装的太成功了。
“大王。小的都在这里关了一天了,这水米未进,能否给我点吃食。”胖子抖着那一身膘,谄媚哀求道,肥脸都挤缩成一团,那本来就细小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缝。
这胖子饥肠辘辘,饿的肚皮都憋了下去,象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挂在那里,生怕李承祖他们把他忘了。
他这一说,李承祖才记起的确是让这胖子饿了一天了,虽然感觉上肥的人比瘦的人更耐饿,但是实际上胖的人要比常人更容易产生饥饿感。
不过看了刘胖子此时象乞丐一样讨要吃食的怂样,李承祖差点没笑出来。费劲憋住笑意,他安抚那胖子道:“行了,少不了你的,刘公子可是贵客,不会让你做饿死鬼的。”
李承祖他们把胖子关严实了,自己等人去饱食了一顿,有让李角给那胖子送了点剩饭剩菜。照李承祖的话说,这就是俘虏,至于胖子合不合胃口,那不在考虑范围,爱吃不吃,他那身膘,反正三天,五天不吃都死不了。
这一夜又在不平静中度过,知州府忙成一团。刘夫人要死要活,把刘知州搞的头大无比。衙门的捕快和州内的厢军都把易州都翻了遍,本来还不想张扬的,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样的大动作,有心人花点银子一打听就知道了,这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出的起价,就是皇上夜宿哪个妃子的寝宫,穿什么颜色内裤也能打听到的。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易州的百姓都知道知州公子让人给绑了,而且更厉害的是,百姓们八卦到,连胖子是去嫖妓完被绑都给发觉了出来。
然后流言蜚语就出来了,国人三人成虎的优点充分发扬,各种版本的绑票经过被加工出来,而其中最主流的是两种,一种是争风吃醋,说某个山贼头目也看上了那水仙小姐,因为胖子包养着,山贼妒狠,就把他给绑了。
还有一种传闻更夸张,更是牵涉到了刘老头,这个版本带着浓重的悬肄色彩,说是知州年轻时候风流了一个女人,结果没有认帐,又娶了现在的夫人。但是那个女子却有了知州的种,于是孤身一人生下个男孩。
十几年后,女人得病死了,临死的时候告诉了那孩子他爹的是谁。而此时孩子已经成为一方巨寇,为了报复知州遗弃他们母子,将他知州这个儿子,他异母兄弟绑票了,目的是逼知州给他们母子一个公道。
这第二个版本,情节曲折,人物,时间都编的完美,有理有据,象摸象样,而且流传的途中还不断加如新元素,知州都被人传成了负心薄幸,无情无义之人。甚至连刘夫人都有些狐疑,四处找知州麻烦。
刘老头肝火大动,跑到衙门躲起来。厢军则把出事前万春楼授了一遍,没有找到什么线索,只好把万春楼老鸨三娘给带到了州衙门。
刘老头太伤脑筋,又后院不宁,真是找不出头绪。只得把自己的心腹谋士全福找来,怒气道:“那个逆子,他丢了倒好,现在倒牵连起老父来,谣言四起,这叫本州的威仪何在,要是让那些风闻言事的走马捅达天听,本州还如何在朝廷立足,耽才,你有办法可行,还请教我。”
全福也忧心道:“学生也担心大人,如今传言者众,想要安抚何其难,强行禁百姓议论更是下下之策,为今之计,只有马上找到公子,如此,这些流言就不攻自破。”
刘老头点点头,赞同道:“本州也是如此想,只是如今毫无头绪,向东不知所终,本州已经令衙役和州军一起搜索,至今还无音信。”
“其实,学生到是可能知道公子在谁的手上。”全福贴过去,跟老头轻轻的咬了一阵耳朵,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阵。
“有这回事”刘老头听后大怒道:“这个逆子到处惹事生非,我都交代了他不要去招惹人家,全然不顾,真是气死我了,不过耽才,你怎么也跟着向东胡闹,给他出主意呢?”
全福拳手告罪一声道:“学生也是碍于情面,再则也没想到,那人年纪轻轻却是行事果断,这回手来的也太快,公子又不听我言,跑去烟花之地,总之,学生是愧对大人。”
“哎,此事也不能完全怨你”刘老头叹息了一声:“我那逆子,都让他娘贯坏了,这些年做了不少勾当,没少让本州头痛,让他吃点苦头也好,只是耽才,你确定是那人所为。”
全福道:“学生也只是猜想,因为公子在出事前只和那人有过节,所以他是最有可能对付公子,派人去他府上搜,学生有8成的把握。”
“还是慎重点好”刘老头想了想说道:“李府毕竟不是一般的乡绅,他的根基,连本州都不知道,贸然行事,落人口实。”
“大人考虑的既是”全福对刘知州是很恭敬,他对他有知遇之恩,是他的伯乐。打心底的折服。
两个人还在继续商讨,外边响起了敲门声,一名厢军指挥使进来报告:“大人,我们已将万春楼的老鸨三娘带到州衙,如何处置请大人示下。”
刘老头听后皱眉道:“耽才,随我一道去审问那老鸨,也好一解我们心头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