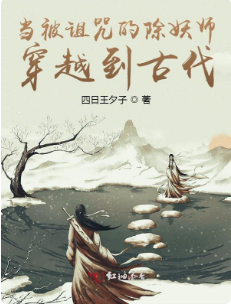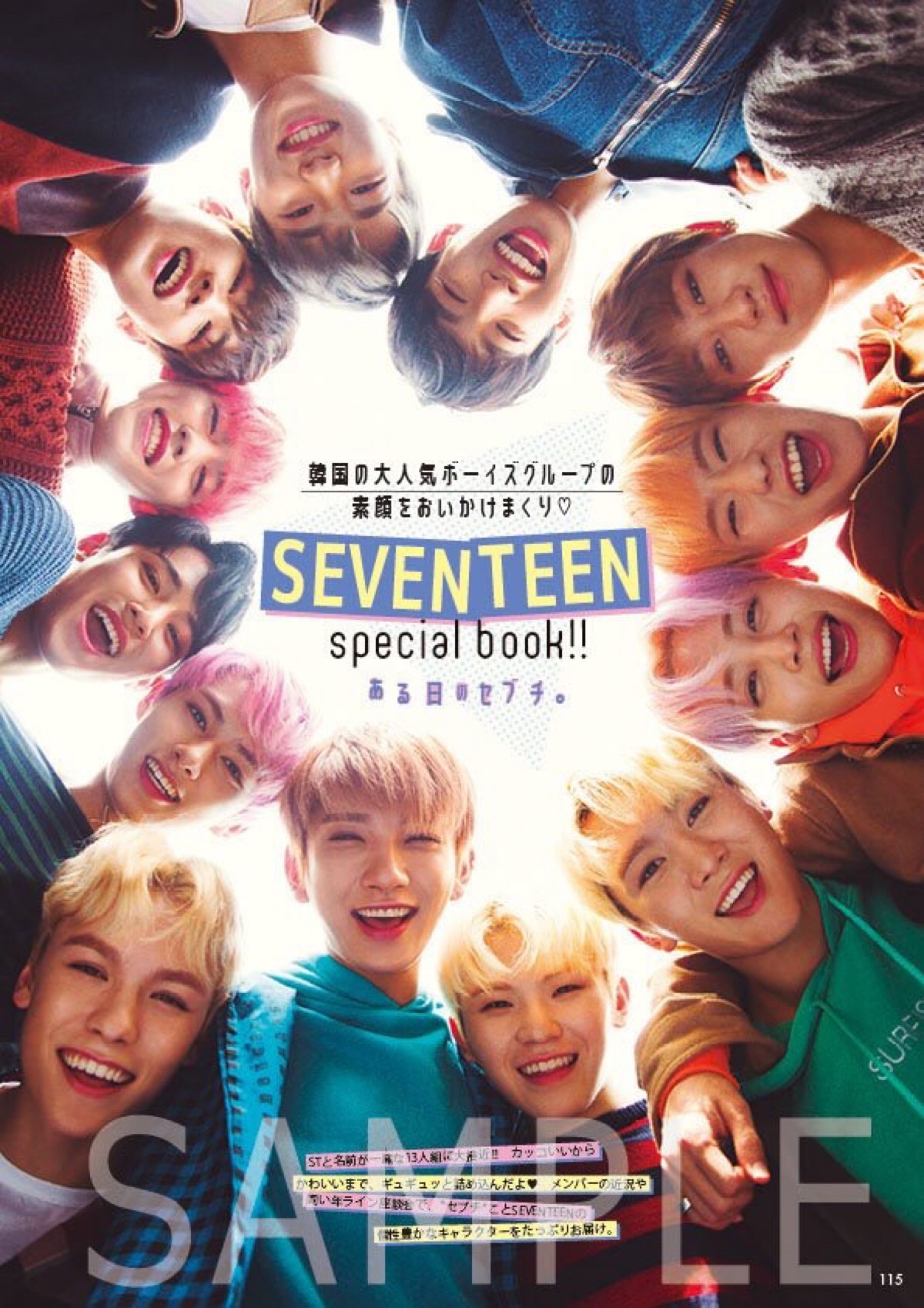“是谁伤了公子”正午十分,李府传来一声声怒吼,却原来三李老仆回来,看到李承祖浑身带伤,一问之下,居然是出门被人打的。
这还了得,三个老仆人是勃然大怒。别人不知道,他们可是清楚的很,自己家小主子是什么人,那可是皇亲国契,正经的当今圣上子侄,当朝大将李继隆的儿子。
老主人把自己孩子交给他们,对他们来说那是荣誉和信任,是要竭尽心力,十万分报答。好好照顾小公子就是他们使命,现在可好,小主子让人打了,这不是抽他们的脸吗。
说句不好听的话,李承祖都没让他爹打过,三个忠心仆属的心可以理解,仿佛受伤的狼。暴躁的李武已经踹上钢刀,只等李承祖指个人名,管他是谁,他就要去和人家拼命。
李忠和李文虽然没有那么冲动,但那挂在脸上的愤怒和痛惜一点不比李武少,一样的咬牙切齿,只是他们的理智让他们更清楚的想了解这事前因后果。
“三位叔伯,我都伤成这样了,也不关心一下。”李承祖无奈的摊开手,乔玉给他上好了伤药,但是他还是躺在自己的床上养伤,这动作一激烈,又痛的直咧嘴。
“公子当心着些”三位老仆看的那个心疼啊,七手八脚的把好动李某某压回了床,不让他乱动。同时看着那四处乌青和伤痕老泪纵横。
李承祖这一身的卖相的确是挺惨,活下在战场上大战了几天几夜的勇将,那身上就没块好的地方,他不是重点被人家照顾,那围殴的人可是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好好拍打了他一通。
看起来吓人,但其实这些都是轻伤,用器械的人都被他想办法挡下来,拳脚则被他咬牙硬抗,打的虽然多,却没一个很严重的。
李承祖不喜欢看人哭泣,特别不喜欢年纪比他大的人围着他哭,这三人一决堤,他就慌着安慰:“三位叔伯,勿伤感,只是些皮外伤,合着内腹有些轻微的震荡,不碍事的。”
“公子总该知道那些动手之人吧”见李承祖说话中气还是很足,证明他的确是伤的不重,这些人也是上过战场的,刚刚只是关心则乱,这一仔细,轻伤重伤他们分的很清楚。
对于这个问题,李承祖没有说,乔玉代他回答了:“那些围攻的人在闹街上暗伏,都穿着贩子的衣服,语气,做势却象一些地痞无赖,出手的应该是地方上恶霸。”
“恶霸”李忠三人皱眉头,沉思道:“我们李府和这易州地面上没有冲突,也从未得罪过这样的人物,难道是公子近日犯了人。”
“胡扯”李承祖辩道:“我和这些人从没有过交道,何来犯人之说。”
“那就怪了”三个老仆满脑的问号:“既然就没有过节,他们为什么伏击公子。”
李承祖白了白眼睛说道:“我怎么知道,莫不是背后有人指使。”
“可是谁又用这样下作的手段”几个人眼睛一亮,也觉得可能性很大。李承祖道:“先不胡乱猜,马宝已经去了衙门,等他回来了,打听一下。”
说曹操,这边曹操就到了。李角开了门,马宝从赶到这卧房。李承祖大笑道:“马宝,我们正等着你,事情办的如何。”
马宝掏出一页纸,上面用墨写满了字,递了过去道:“我按照公子吩咐,向那录供讨要这一份笔录,起先那师爷不肯,我就依言不画押,他急了,以下大狱要挟我,跟他那里闹了回,那白都头把那师爷叫了进去,两个人密谈了回,这师爷才有抄了份录供给我,公子过过目,可有不妥。”
李承祖点点头,拿起纸张浏览了遍,都是些很生涩的古文,好在他的功课也没拉下,其意思还是勉强看懂了,原意还是满符合要求的,也就是说这份录供是没问题。
他向马宝问道:“你可知道那些被抓归的人,州衙如何处理?”马宝摇摇头说道:“只是暂时收押如何处置还不得而知。”
“不过”马宝话语一转道:“我打听到了袭击我们人的来路。”众人听了急道:“当真,别吊弯子,快说。”
被怎么多人催促,马宝不敢怠慢,仔细说道:“我出来的时候,一直想不明白,这些人怎么知道我和公子要路过,又事先换了衣服埋伏。”
他比画道:“恰好,我过后衙的时候碰到两个文书,在那小声说着今日街上聚斗的事,我多了个心,象他俩套话,这两嘶机敏的很,听我问此事,都闭口不谈,我狠了心一人给了他们几吊钱,这两文书才言道,今日那些人是易州城里的一些游手好闲地痞无赖,他们窝在一起,平时干些欺压良善的坏事,也成了一霸,后来他们推了个首领,此人叫林步山,就是那使板斧的汉子,他给这些无赖立了规矩,穷困之人不做弄,专找富人晦气,渐渐也有了些名气,地面上商贩大户也要让着他一些,因他擅使板斧,便得了个绰号“林斧子”。”
李承祖说道:“难道他们是劫富济贫,那天开口一千贯就是为此。”他有摇摇头说道:“不对啊,我明明听他们中人说,是有人指使。”
“公子高看他们了”马宝道:“那林步山是有些江湖义气,但也仅次而已,一样的贪财斗狠,本事也高,还帮带着做些收人钱财,替人消灭灾之事。”
李承祖低下头,沉咛道:“那么,这背后主使之人是谁呢,他必和我有怨,也要相当有钱财。他口中喃喃举着例子,眉头紧皱如锁,一丝明悟在心头闪过,却不敢肯定。
“忠伯,这几日你多跑衙门打听下,看看那些人如何判理”他眼中闪着寒光,低声的吩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