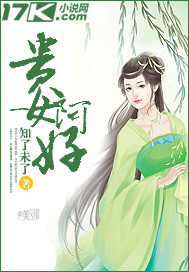“哦?合阳那边传来了什么消息?”得知这个消息,九殿下表现的毫无意外,他们临走的时候,留下了人在合阳,让他们监管王振家人的处置等事,另一方面也是暗中查内役司分司的事情,内役司分司内部必定有问题,九殿下从接触王振就有这种强烈的感觉,让他不敢有丝毫松懈。 前些日子更是将拧六派了过去,这次也是拧六回来送的消息。
“殿下,王爷,跟我来。”蔺蒙开口,九殿下与北疆王爷二人相视一眼,紧随其后,三人兜兜转转,来到了前厅相连的侧厅,这里一般是蔺蒙拿来写写字的地方,环境极为幽静。
“师傅,可是很重要的事情?”九殿下看着蔺蒙小心谨慎的一步一步带领他们走过去,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不会太简单。
“殿下,小六待会就过来,他把所有的一切都带来了,”蔺蒙将房间门关上,打开了另一侧的一个暗门,拧六走了出来,“小六,我把殿下带过来了,你有什么事情就可以说了。”
“拧六拜见殿下。”柠六走到九殿下眼前,随后开口,“殿下,这些是我在合阳分司里面的一棵大树下面挖出来的,请殿下过目。”
柠六将一叠看起来好像是一沓纸的东西递了过来,九殿下接过,走到北疆王身边,在他眼前将那些东西打开。
不看还好,一看九殿下觉得这个世界还真的是疯狂,那里面一张一张的纸全是一笔又一笔的罪证。那里面夹着的有的是信封,有的是票据,还有的看起来应该是当铺的典当记录。一笔一笔,一点一滴,来源以及用处记得都十分清楚,更何况那上面明晃晃的印戳,全都是合阳内役司分司与靳王的交易记录。
“王叔,这是……”九殿下盯着眼前赤裸裸的证据,感到不可思议。靳王为景阳帝的亲叔叔,他为什么会私底下做这么些见不得人的交易,里面还包括很多贡品的买卖记录,全是大笔的金银流入靳王的口袋里。
“小六,这些信件票据确定真实?”九殿下看着柠六,盯着他的眼睛,似乎在探求虚伪,“要是有一点差错,咱们可就冤枉了好人了。”
“回殿下,这些东西全是在内役司分司挖出来的,属下一得手,就快马赶回了黎阳,前来跟殿下汇报,至于真伪,”柠六稍微犹豫,“还需要专人辨别了才能知晓。”
“小六,这次做的好,”九殿下夸赞,柠六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九殿下接着说,“你快马赶来,想必累极,先去吃东西,然后歇息一番。”
“谢殿下。”柠六应道,就推出了房间,还顺带着关上了房门,里面的三个主子,应该有需要详谈,他快马赶了两天多,身心俱累,也是该好好休息了。
“师傅,王叔,这件事情,你们两位怎么看?”九殿下望着阖上的房门,手上捏紧了这一笔一笔记录详细的票据,往手里攥了攥。
“蔺大学士,怎么看?这件事情若是真的事关靳王,那可不是什么小事,靳王手中虽然没有兵力,可是他的女儿却是当今国母,大荆的皇后娘娘,换一句话说,也事关皇家的颜面,一步错,那可是步步错,结果就是万丈深渊。”
“在蔺蒙看来,这件事情我们不宜出手,最好还是避开比较好。”蔺蒙思忖良久,幽幽开口。
“咱们不宜出手,那是要别人出手?师傅可是这个意思?”九殿下心领神会,附和道,再看向一旁站着的北疆王,等着他说话。
北疆王爷点点头,“这件事情,本王与蔺大学士意见一致,确实咱们不适合出手。如今那边的办案权不在咱们手上不说,这些信件的来历,还要一一查明,九殿下手上现今能用的估计暂时也没有那么多的人手,只怕那边还没有解决,自己这里就先遭了灾难,得不偿失。”
“王爷所言甚是,所以殿下咱们现在不能轻举妄动。靳王既然敢私底下这么大笔的交易,对方应该也不会是一个普通人,敌方在暗,事事皆不利于我们。若是咱们暴露得太早,打草惊蛇事小,断了线索事大。”
“嗯,师傅跟王叔这么一说,还请说明白些,要怎么做?”九殿下虚心求救。
“殿下,如今皇上可有下令彻查王振一案?”蔺蒙明知故问,冲他和煦一笑,一点一点的为他解决疑惑。
“众所周知,皇上庑正殿之上亲自下令说要彻查王振一事,师傅会不知道?”九殿下戏谑的笑着,师傅对他的指点还真的是一步一步开始,让他好不自在。
“殿下可还记得皇上当时是让谁去查的?”蔺蒙接着循循善诱,希望他可以自己想明白。
九殿下沉默,大脑在飞速的旋转,“内役司掌司使凡杰大人以及靖律司两位司律使。只是到今天本殿都不曾了解为何皇上会安排两个司来查一件事,岂不是有些大材小用?”
“哈哈,殿下还是入世未深,”北疆王爷爽声大笑,笑够了以后才开口,“殿下,今后跟着蔺大学士可要好好学着,大学士才智双全,智谋无双,可是一个好师傅。”
“呵呵,北疆王爷过奖,”蔺蒙笑着应道,没有多言,再继续说下去,既然九殿下还不明了,他作为师傅,自然要提点提点,“殿下,合阳犯事的可是分司使,直属内役司管辖,也就是说凡杰是他的顶头上司,自己的手下犯了错,主子自然要出面,一为将功补过,二为彻查内役司,看是否还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所以皇上会安排凡杰大人作为主审官,蔺某我一点也不奇怪。”
“那为何还要靖律司两位司律使大人协助?若是为了让凡杰将功补过,彻查内役司,那凡杰一个人足够用了吧。”
蔺蒙不置可否,笑了笑,才说,“靖律司的主要任务是要干嘛?众所周知,就是执法者,是大荆法例最高的实行者,王振一事,触犯大荆律例甚多,牵扯甚广,理应由靖律司出面。”
“那为何还要交给凡杰大人?师傅你倒是越说越糊涂了。”九殿下更加疑惑,不懂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九殿下别急,先听你师傅把事情讲完,殿下再发问也不迟。”北疆王爷虽然明白景阳帝行事的意义,却也没打断蔺蒙再次谈起,如今的九殿下,就需要一个这样谆谆教导的老师,才可以成长走得更稳健。
“皇上指派了凡杰大人一人,然而捎带上了整个靖律司,虽说行事之中,内役司为主,可是靖律司两位司律使大人,办案这么多年,那行事之果断岂是终年不曾接触案件的凡杰大人可以比拟的?谁是主审,怕是有待商榷吧。”蔺蒙说了这么多,九殿下也明白了七七八八,瞬间感觉前途无比亮堂。
“师傅的意思是说,我们将这些资料交给那些审查的大人们,让他们自己去辨识真伪,这个案子咱们这边就不再插手。”九殿下顺着蔺蒙提示的说下去,蔺蒙闻言,笑了。
“那殿下觉得我们应该将其交给哪一方?”这次换蔺蒙追问了,他想知道,说了这么多,九殿下是否有大的长进。
“听师傅所言,内役司凡杰大人行事不如靖律司两位大人果断,而且靖律司两位大人常年办案,经验丰富,应该是给他们。”九殿下皱皱眉头,似乎想通了一样,回答。
“对,殿下所言分毫不差,而且靖律司两位大人,向来是机敏果敢的,以铁面无私著称,交给他们再合适不过了。”
“只不过要怎么给他们,可不能是咱们亲自上门吧。”九殿下说话的时候还不忘自我打趣,“那样的话,咱们就脱不了干系了。”
“是,咱们不能给他,可是有人可以。”北疆王爷与蔺蒙相视一眼,会心一笑,心里早就有了主意。
北疆王爷一直呆到用完午膳才离开,九殿下与蔺蒙二人将他送出府,北疆王爷此次前来为带随从,也未穿战袍,认识他的人知之甚少。
九殿下与蔺蒙二人出来的时候,恰巧碰到了前来看九殿下的子悠大人,他身后跟着的还有锦书与青絮二人。
“子悠大人,多日不见,可还安好?”瞧见子悠过来,九殿下二人顿住了想要进府上的脚步,蔺蒙转身,冲他打招呼。
“蔺大学士无需客气,本官奉命而来,前来看看九殿下。”子悠慢悠悠的开口,瞬间表明了来意,旁边的青絮二人,一个双手抱胸,一个将浑身上下捂得严严实实的,没有说一句话。
“既然是皇上派大人来,那就不站在这里了,子悠大人,两位姑娘,请进。”蔺蒙笑着邀请三人进府中,九殿下一听到皇上这两个字,身上的气场就变了。
“蔺大学士这话是怎么说的,难道要不是皇上让我们来,大学士还打算将我们拒之门外不成?”听到蔺蒙的邀请,青絮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欣喜,反而在挑他的话柄。
意识到青絮姑娘此时心情不甚好,蔺蒙也没跟她对着来,冲她微微一笑,“青絮姑娘,蔺某失言,请姑娘包含。”
“哼。”青絮高贵冷艳的哼了一声,没再搭理他,直接先行进去,九殿下看着她大摇大摆的样子,以及对自己师傅不礼貌的样子,心生不耐烦,蔺蒙暗中拉了拉他的袖子,九殿下才压下想要赶她出去的冲动。
倒是锦书走到二人旁边的时候,替青絮解释了一句,“少阁主最近太忙,冒犯了九殿下与大学士,还请两位见谅。”
“怎么会,”蔺蒙圆场,在前方引路,“锦书姑娘,子悠大人,这边请。”
几个人来到九殿下书房前的院落里,蔺蒙命人收拾了院落,几个人坐的坐,站的站,也是分外和谐。
“似乎每次子悠大人来我皇子府,都是皇上的意思。”九殿下与子悠围着石桌坐下,青絮挨着子悠,蔺蒙没有坐在他们身边,在他们石桌的右后方搬来一个椅子,坐下。锦书一个人在院子里晃荡,没有去他们身边。
“听蔺大学士一说,好像还真是如此。”子悠手摇着折扇,跟蔺蒙想到了一处。
“不知皇上这次是以何理由让子悠大人前来?”九殿下一直未做声,看着蔺蒙与子悠二人交谈,此时提起景阳帝,才忍不住插了一句。
“嗬,”子悠轻轻笑,未及眼底,“皇上说殿下多日未上朝,不知身体近来可好,询问了子悠,得知青煜阁两位姑娘还在黎阳,特命微臣请两位姑娘前来,看看殿下身体如何。”
“哦?他竟然是这样说的了。”青絮在子悠下了朝以后,就被子悠要求在驿站等着,可能还会去一趟皇子府。如今得知缘由,青絮稍显不耐烦,“合着在你们大荆皇帝的眼中,我们青煜阁就应该随叫随到?早知如此,姑娘我就不应该来黎阳,惹得了一身骚。”说着,还不忘找找锦书在哪里,冲她遥远的喊着,“锦书,你说是不是?”
青絮与锦书二人一人穿着粉色云锦缎裙,一人穿着穿着海蓝色云锦缎裙。两人的发饰都很简单,以一只玉钗将发髻挽成。
此时的青絮跪坐在石凳上,身后是一片金黄色的银杏树,手里拿着一个银杏叶,凑近自己的下巴,撑着额头,眉间有着不耐烦。锦书则更加随意,整个身子侧靠在银杏树上,手抚摸着树干,眼睛盯着天上,不知道在看什么,对于青絮的问话,也是由空气送来回答,她说“恩。”
“青絮姑娘,青煜阁医药圣地,诸多人向往而不可得,如今少阁主恰好在黎阳,皇上也难免会更加关注。”子悠对青絮的抱怨恍若未闻,蔺蒙轻笑,忙不矢开口。
这个时候,梓七带人送上茶水,还应青絮的要求拿来了棋盘跟棋子,放在石桌上,才静悄悄的退下。
“殿下如今看来,气色似乎好了不少。”子悠看着九殿下,眼前的人虽然称不上神采奕奕,却也不至于毫无生机。
九殿下打开棋盒,手执白子,将黑子递给子悠,子悠接过,二人相视,九殿下开口,“子悠大人,先请。”
“好久没下过棋了,怕是早已生疏了,九殿下可要让着点。”子悠淡定的在棋盘上落下一子,看向九殿下,示意该他了。
九殿下轻轻点头,在他黑子的旁边落下一子,“近些日子闲来无事,皇上有意让本殿休养生息,如今看来,明日开始,怕是也要忙起来了。”二人手起棋落,你来我往,手速极快。
“如今大荆也是用人之际,掌司使尚有空缺不说,国内能够调动的将领也不多,皇上会如此急忙,也情有可原。”子悠再落下一子,随手合起折扇,撑在膝盖上,注视着棋盘上的局势。
“这倒是个好理由,”九殿下左手放在棋盒里,摸着棋子,半天都没有继续下一步棋的打算,“子悠大人还真是了解皇上,本殿下佩服。”
九殿下这话说的不阴不阳,在子悠看来,似乎有点毫无道理。
“殿下没必要这么说,身为人臣,忠于君事,子悠之本分。”看他不着急落子,子悠也不催促,好脾气的看着棋局,默默的摸索着九殿下的棋路。
九殿下那边,蔺蒙站起身来走到他身后,想看看为什么殿下会思考那么久。
“那边蔺大学士在帮九殿下,看来我也有必要给子悠大人找个帮手。”青絮看着蔺蒙走到九殿下身后,不满的出声。
“恩。”子悠闻言拿起桌子上侍女送来的茶,一饮而尽,侧着头偷偷的瞟着她,“你又打什么主意?”
“锦书,你过来”青絮忍不住笑了起来,冲子悠一个明媚的笑容,高声喊着一直站在那边的人。锦书应,在众人的注视之下,走了过来。
青絮兴趣盎然的看着锦书迈着优雅的步子走到她的身边,锦书开口,“少阁主,何事?”
青絮瞪了瞪蔺蒙与九殿下两人,从座位上由跪着变为站着,瞅准了子悠这边棋盒放的位置,将锦书推过去,“那边下棋两个人,你帮帮子悠大人。”
看着旁边闹腾的两个女子,子悠暗笑,锦书在青絮的撺掇下不知道该如何回绝,子悠开口打破了她的尴尬,“锦书姑娘不妨来看看。”随后转头看向棋局那边的二人,“蔺大学士,九殿下,可以么?”
“呵,切磋,随意就好。”九殿下轻笑,坐在旁边的位置上,将膝上的衣服整理好,两只手搭在膝盖上,随意的说。
“锦书,看你的了。”青絮并不在乎九殿下的反应,拉着锦书,要将她按在座位上。
“少阁主,观棋不语,此举不妥。”锦书反抗着,不在她的位置上坐下,随后话是对着子悠说的,“想必子悠大人也不需要锦书插手,自己可以的。”
“既然锦书姑娘不愿意,子悠我也不好再勉强,姑娘既然说可以,那子悠定不会让姑娘失望。”对于锦书的拒绝,子悠心里早就有了准备,她太过于固执,他也不能勉强。
“殿下这边,蔺某不插手,正如锦书姑娘所说,观棋不语真君子。”青絮眼光微闪,没想到这两个人竟然顺水推舟,心里暗忖。
而锦书,此时想的却是刚才送茶水进来的那个女子。年岁虽小,眉眼之间却可以看到她父亲的影子。当年晨安的忠心,是她最后感到的一点温暖。
四年前景阳帝恪守诺言,没有对当年地牢一事多加追查,想必晨安也是在黎阳几处漂泊,如今他女儿已经这么大,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锦书今日心不在焉,也不知为何。”青絮喃喃自语,锦书刚才留下那一句话就又离开了。青絮跟在她身后,看到锦书慢慢的走到银杏树下,伸手扶上它的躯干。
一旁下棋的三人还在那边继续着棋盘上的拼杀,偶然间坐着的九殿下却注意到了她们二人的动作,眼神逐渐深邃了。
子悠顺着九殿下的目光,注意到了子烨看的方向,眸光一闪,扭头注视一旁树下的二人。
九殿下站起身,将手中的棋子放下,走到她们两个那边,问,“两位姑娘很喜欢银杏树么?”
他记忆中皇姐沁阳最钟爱的两种树就是柳树跟银杏。柳树春起秋落,象征着新旧时序的交替;银杏春绿秋黄,年复一年,代表着生命力的生生不息。当年合阳县县使凡坞一把火烧了当时的合阳县衙,后来选府址的时候,青絮亲手挑的那个地方,那棵柳树。而这里的这棵银杏,更是与她有着很深的渊源。
“恩,银杏果又称白果,驱寒止咳,是很好的药材,我当然喜欢。”青絮的话是以她的角度来说的,也让人挑不出来毛病。
“银杏树在大荆这片土地上万年生生不息,迎春绿,临秋黄,象征着生命的生生不息。”九殿下手指着那棵银杏,淡淡的出声。
这么多年,他仍然记得沁阳当初对他说这些话的样子,她穿着最华贵的湖水蓝的金丝云裳百褶裙,头上戴着大荆最独一无二的百蝶金步摇,眼波流转,柔情似水。
那时候沁阳刚从南疆征战回来,景仁帝给她加官进爵还有封地,南疆六十二城全是她的,另外还有沁亲王府,当时年少的九殿下吵着也要王府,沁阳拗不过他,只好以二十城作为交换,替他求了这座府邸。直到现在,九殿下才明白,当初为了这座府邸,他皇姐付出了多少。
他去北疆时,一度以为这座宅子已经荒废了,谁知兜兜转转,如今的九皇子府,还如当年一般。
这是青絮认识九殿下这么久,第一次看到这么温柔的他,平时的他都是不苟言笑,甚至是懒得废话、跟赫连宸有点相似,孤标傲世的。这个时候的他,不似往常,他的浑身都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青絮不由得对他有了另一种感觉,她觉得九殿下似乎并不像他们往日看到的那样,他只是不会倾诉,不会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