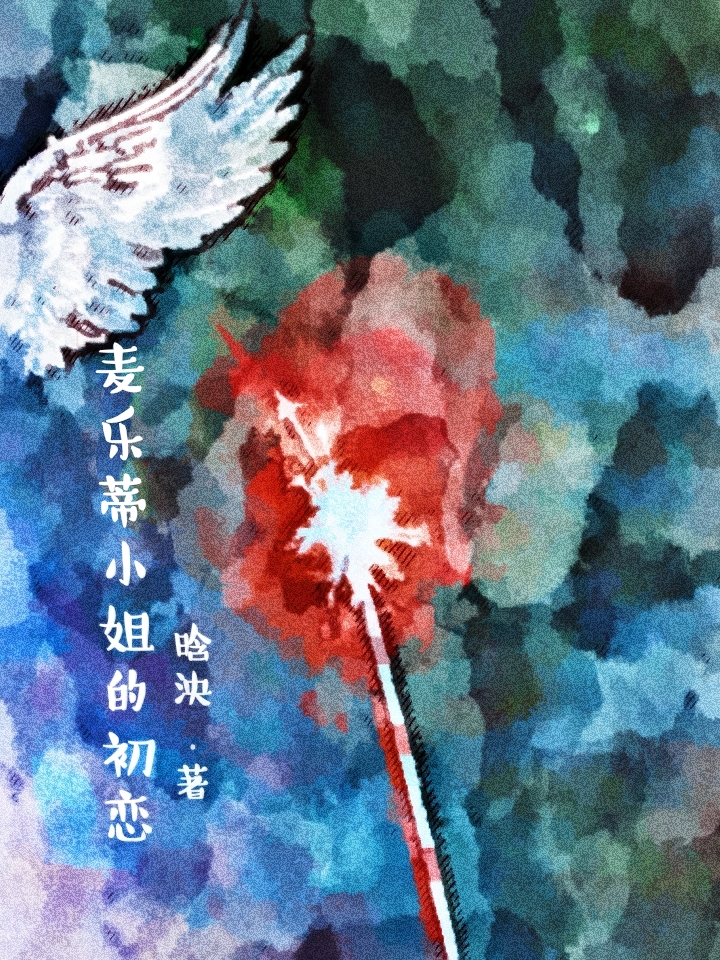“回皇上的话,老臣……军费所缺失的部分被老臣私自截下,用于填补……往年的税收了。老臣认罪望皇上责罚。”苏越伏在地上,整个身子就像飘零的落叶一般,瑟瑟发抖,战战兢兢的等待着景阳帝的处置。
“此话当真?”景阳帝一手划过膝盖,撑在龙椅的一侧,细细地盯着自己的拇指,食指与拇指摩挲着在想些什么就连犴司都不怎么清楚。
“老臣所言,千真万确。”苏越的话语中已经带了哭腔,这话一说更是罪加一等,他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竟然会想到这种办法,且不说军费的挪用本就是一件不可原谅的大事,更何况还是用来填补了税收所缺。
“苏越大人这些年的官还真是没白做,”景阳帝期身距离眼前的桌子只有几寸的距离,表面上是称赞实则将其说的一无是处,景阳帝道:“朕还真的好奇,苏越大人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招是何人给苏越大人说的,竟会如此的不知趣,拆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苏越大人用的倒是不亦乐乎。”
税收是国之根本,苏越竟然胆敢在税收上做手脚,岂不是太过于有恃无恐了?真当天高皇帝远,事情永远不会有败露的那一刻?
“皇上,老臣自知税收所缺是臣的失职,万不得已想到了这样一种方法,以为再有来年便可将其填补上,未曾想还未等到来年,皇上就已如此动怒……”苏越的话里没有一点丝毫要悔改的意思,反而觉得今年被景阳帝发现是因为自己的不走运,着实让景阳帝大开眼界。
“听苏越大人此话的意思,似乎还是怪朕没有给大人时间来讲所挪用的军费来及时补给上,如此说来岂不还是朕的错了?”
“请皇上恕罪,老臣不敢有这个意思。”苏越没想到景阳帝说话竟然这样的直接,一点都不顾及君臣一场,甚至以自我讽刺的意思对他百般嘲弄,苏越的老脸有点挂不住:“皇上,此事也是无奈之举,还请皇上明察。密阳军乃是大荆除边塞外队伍最庞大装备最齐全的一支军队了,每年朝廷都要投进去大笔的银子。然而税收又是大荆的根本,所以老臣一时鬼迷了心窍,竟没想通透里面的利害关系,就此铸成了大错……”
“原来你还知道大惊密阳军是大荆最大的军队,朕还以为你忘了呢。”景阳帝淡笑,眼神似有似无的瞟向苏越身上:“那你可知,一旦军费被抽,可是会多少军士就此面临随时可能丢掉性命的危险?苏越大人你在满足自己的一己之私的时候,可曾想过你诺大的密阳城,也是靠将士一步一步打下来的。若没有了他们,你何来做这个密阳县县使,甚至是你的儿子、你的夫人,有朝一日是不是也会死在他人铁骑的践踏之下。”
景阳帝的话一针一针的刺向苏越,让他难堪的同时,也让他遭受着最诛心的折磨。景阳帝不给他一个痛快,反而将他的恶行一笔笔、一件件由他自己陈述出口,由他自己分析其中的利害关系,让他在认识自己失败的时候,还要同时了解到自己的愚蠢。
“一支庞大的队伍,为何要因为你一人的愚蠢,而承担所有的罪责?”景阳帝继续说,似乎是没有了让殿内人再开口的打算:“这些年以来,大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确实是这数百年来,得以一见的盛景,苏越大人可曾为其出过几分力?”
“密阳的军队最初是谁操练的,朕想苏越大人心里应该是清楚的。”景阳帝利眸瞬间扫向苏越,冰冷的神色让跪在地上的苏越抑制不住的发抖,就连求饶的声音都不敢有。他总觉得这件事情不会那么简单,景阳帝如此大费周章,竟然还提起了密阳军,让他怎么能不慌张。
“皇上,老臣知罪。老臣自知罪大恶极,恐杀之也难以平皇上之愤怒……”
“你说得很对,确实是杀了你都不能解了朕的心头之恨,”景阳帝居于高位,如今他对待苏越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的简单,然而就是想要慢慢的折磨他,直到他精疲力竭,再无反抗的机会:“方才苏越大人提到了密阳税收,那么也跟朕说说,苏越大人你是何时打上税收的主意的?”
景阳帝的质问苏越紧跟着就想反驳,景阳帝摸了摸自己的袖子,继续说:“莫要在大殿上逞谎,就算你说朕也是不信的。你既可以用军费补了税收,又怎么会放过在税收上动手脚的好时机?那么你到底是将税收用在了何处?竟让你敢冒如此之大的风险,在军费上动手脚。”
“皇上,”苏越痛哭流涕,然而景阳帝已经不知道有几分真有几分假了:“老臣糊涂,前两年因为爱子的要求,想要在密阳新建一栋花苑,老臣当时实在是无路可走,才动了税收的心思……”
“无路可走?”景阳帝冷笑,睨着他说:“朕倒是看苏越大人的路挺多的,又怎么会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为了一座花苑,苏越大人就将眼神瞄向了朕的税收,你说你该不该死?”
“老臣……该死!”这话听起来就像是苏越咬着后槽牙说的,景阳帝不知他竟会昏庸糊涂到这个地步,然而还不止……
“你该死?那你所谓的爱子呢?”景阳帝轻笑,每当他笑起来尤其璀璨的时候,那就是有人要倒大霉了,苏越心里就有这种感觉,他听到景阳帝说:“用税收来为自家儿子建花苑,这主意倒是好的很啊。今年的税收用明年的军费来补,然后再用来年的税收将军费补上,周而复始……”
“皇上,老臣知罪,可是均与老臣的儿子无关,他是无心的……”
“上梁不正下梁歪,朕看你这副样子,不难想象得到,你那儿子该生成哪副样子。”景阳帝看着他死到临头竟还如此大胆的给自己的儿子求情,心里顿时一股气涌上了心头,开始跟他算起了账:“朕听说苏越大人所谓的花苑占地面积将近百顷,竟比朕的御花园还要大上不少。其间珍禽异兽甚是多,密阳的贵族甚至还可以在里面进行秋猎,嬉戏玩闹。园中池子众多,苏越大人将其一一沟通,内外相连。建筑散落在山水之间,山嵌水抱之姿甚是好看万分。朕还听说,只你那个花园每年需要从外县运来的花木所需要的费用竟比朕从国库下拨给密阳军队的军费还要多……”
景阳帝每说一句,苏越的头就要低上几分,直到最后整个人都快钻到了地里面。大荆园林建筑有规格的要求,帝王皇室自是不必说,凭借自己的权势将整个大荆缩移描模在宫苑之中都可以。然而他们这些大臣王爷那就是万万不行的。沁阳身为一执掌重兵、雄踞一方的亲王的时候,所居住的院子自带的花苑也不过百顷。而他只是一个县使,还不是他自己修建的,是为了他儿子,岂不是更加的说不过去,礼法不容?
“……”苏越跪在地上,整个人瑟瑟发抖,一言不发。他那座园子建造的时候都没有用自己的名字,而后更是为了避嫌用自己儿子的姓名,在其不远处修了一个大概十多顷的园子。到时候就算查下来,那一座大的只要没有人说是他的……那不也是没有关系?
可是现在景阳帝的话每一句都再告诉他,他所谓的障眼法早已经被他识破了,现在到底是抵死不认那座园子,让他去查了,给自己一些时间。还是就此认下,少受一些皮肉之故、心理折磨……苏越在考量。
“苏越大人可曾常去看过那栋园子长什么样子?朕这里还有更加令你想不到的消息,苏越大人想不想听?”景阳帝将事实继续往下扔,想要看一看苏越可以坚持都爱什么时候:“朕还听说,苏越大人所建造的那栋院子竟然不用五年就建好了,年前腊八左右才刚刚竣工,苏越大人可否告诉朕,这可是真的?那么方不方便告知一下苏越大人所找的工匠主持是谁?朕刚好想在黎阳北郊那边开一处离宫别苑出来,既然你家工匠这么速度,要不要将其介绍给朕,朕也好看在他能力出众的份上,给其加官进爵,这不也是苏越大人的积德的大好时机?”
“回皇上,微臣不知,微臣不知。所选人手均是小儿一手所选,物材石料等也都是他一手置之,老臣实在不知道,不知道啊。”
景阳帝没想到有人竟然可以不要脸到这种地步,自己的儿子竟然也成了他的挡箭牌,听着他一句一句将自己从里面摘清楚的话,景阳帝心头阴霾更甚,笑容也更加的浓烈。
“如此说来,这都是苏越大人的‘爱子’一手置办的,与苏越大人并无半点关系的了?朕方才所说均是冤枉了苏越大人。”景阳帝他越生气,就会更加的爱笑,脸上的笑容越深厚,心里的想法与不满就越重,这些都是长年来跟在他身边的老臣所了解的。
然而这个苏越大人就比较有意思了,他身为县使,并没有太多的机会能够觐见景阳帝,对这个皇上的心理摸不透不说,更是对他的一些小习惯都不怎么了解,看着景阳帝脸上的笑容,他的心里还有些许的侥幸。
“回皇上,老臣……不知!”没有人知道他是用了多大的力气,才下定决心将自己的儿子最终推了出来。他是官吏,景阳帝所说的一条条一件件都是可以株连九族的大罪,方才景阳帝已经说了会因为此事他的妻儿……
“如此甚好,苏越大人真是不让朕失望。”出乎意料的没有迎来景阳帝的批评,反而获得了景阳帝的赞赏。苏越默默地从地上抬起头来,偷偷的看着坐在龙椅上的人,一霎那就望见了景阳帝深邃的眸子,里面有很多他看不懂的情绪。
“皇上……老臣自知在税收、军费上有渎职、失察甚至是滥用之责,但请方才皇上决定网开一面的份上,不要追究老臣妻儿的责任。小儿是商贾,这些年也累积了不少的收入,然而老臣教导不严,竟没注意到他私下里盖了那么大的一栋花苑。其僭越之行,老臣不能替其开脱,然皇上金口玉言……臣愿将其双手奉上,归为国有……”
在这样背步步碾压的情况下,还能迅速地在脑子里,形成这样脉络清晰的一番说辞,对于苏越的恨子不成器的悲愤言语,甚至是将那花费大量金钱、时间的园子大方地献上,又急中生智给自己儿子安上了一个“商贾”的身份……不得不说,单凭这些说辞,景阳帝如果不将其先收押,而后查清楚再行处置的话,确实是有点说不过去。
“苏越大人还真是大方,如果朕所估计不错的话,每年单凭院子内花卉的采购,就要有数万两黄金,就这样轻松的一句话奉上,苏越大人心里就不会觉得不服气,觉得自己亏了?”
“皇上,钱财乃身外之外,如今老臣已经朝不保夕,不知道还能保护自己的孩儿多久,如果这样能够保得他一条性命的话,区区一个园子又有什么舍不得的。”
苏越完全是将自己自己定位在了一个好父亲的位置上,景阳帝看着他自导自演了这么样的一部大剧,心里由衷的为他的演技感到叹服。如果不是景阳帝事先早已经掌握了部分真相的话吗说不定还真的会被他这种大义凌然的行为所感动。
“好一个钱财乃身外之物,苏越大人此时的大度让朕心里甚是欣慰……”景阳帝话里话外都不表露半分自己的情绪,顺着苏越想要得到的结果,一点一点的向他所要引导的方向说下去。
“谢皇上明察秋毫,纵使让老臣粉身碎骨,只要能保住老臣孩儿的一条命,老臣万死不辞。”俗语继续发挥着自己杰出的演技,想着如果再不给他一个正常的反应,待会的突然转折,怕是会把苏越直接吓死在大殿之上。
“苏越大人,朕有一句话想说,”景阳帝伸出一只手撑在跟前的几案上,手背顶着自己的下颌,另一只手放在自己胸前,微微皱眉含笑道:“方才朕所说想要在黎阳城北郊开一所园子的话,并不是在偏苏越大人,你的那所那么庞大的园子既然建造的如此之神速,想必那工匠技艺必定是极好的,如此能人岂有不被大荆重用的道理?”
“回皇上,造园所用之人均是小儿一手挑选的,就连人老臣都没有见上几面。老臣的小儿认识,据说此人性情淡泊,喜爱隐逸自由的生活……”
“苏越大人,此人可是叫董贤?”景阳帝不想再听他继续闲扯,已经浪费了他太多的时间:“据朕所知,此人却是一个贪财好色之徒,若不是手上有些技术,可能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
“皇上……你……”苏越的侃侃而谈被景阳帝泼了一头的冷水,脸色顿时如同调色盘一般,异彩纷呈:“皇上,董贤……跟老臣……”
“苏越大人不用着急着撇清自己与他的关系,朕已经差人要将他送回黎阳,不日后就到,到时候到底实情是怎么样,你们二人当堂对峙便可。”
“皇上,老臣不认识他……老臣不认识……”
“唉,”景阳帝叹气道:“苏越大人,朕并没有说董贤跟大人熟识,想要请其来黎阳,也不过是为了北郊建造离宫而来,苏越大人为何看起来如此的慌张,莫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景阳帝一边说,一边注视着苏越变化无常的脸色,心里却在想着,这个人已经活了这么久,多活了这么多年,已经算是便宜他了。
“回皇上,老臣……老臣不曾……”苏越此时被景阳帝唬得一愣一愣的,完全是跟着景阳帝的思维在走,说了什么,被问了什么,他已经说不清楚了。
“苏越大人当真不认识董贤么?”景阳帝再次逼问,话语间已经多了几分杀意:“那么几年前在密阳一男子说当时的国舅苏沛与苏拧为叛军之亲,凭借自己的身份的便利,不知祸害了多少个年轻女子。而后被告进了官府最后却无罪释放之事,你这个密阳县的县使大人应该知道的吧。”
景阳帝说着看着苏越骤然变苍白的脸色,扔不忘在他内心深处最恐惧的地方捅上几刀:“苏家的人当时因为沁亲王殿下的谋逆扰乱之举,纷纷卸了官职。回了老家密阳,本就是走投无路之举。多少的人对其肆意的侮辱谩骂,甚至是欺凌,你这个密阳县县使都好像不曾看到过一样,置若未闻。”
景阳帝说到这里,没有继续说下去,缓缓的舒了一口气,像是要将这些年的积郁,以这样的方式全部都吐出去一样说道:“苏家女子多数被欺凌、被侮辱,苏拧多次击鼓鸣冤,然而最后仍旧抵不过你这个苏大人的一句‘无罪释放’。他曾是你至亲的表兄,为何你竟会对其残忍到那种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