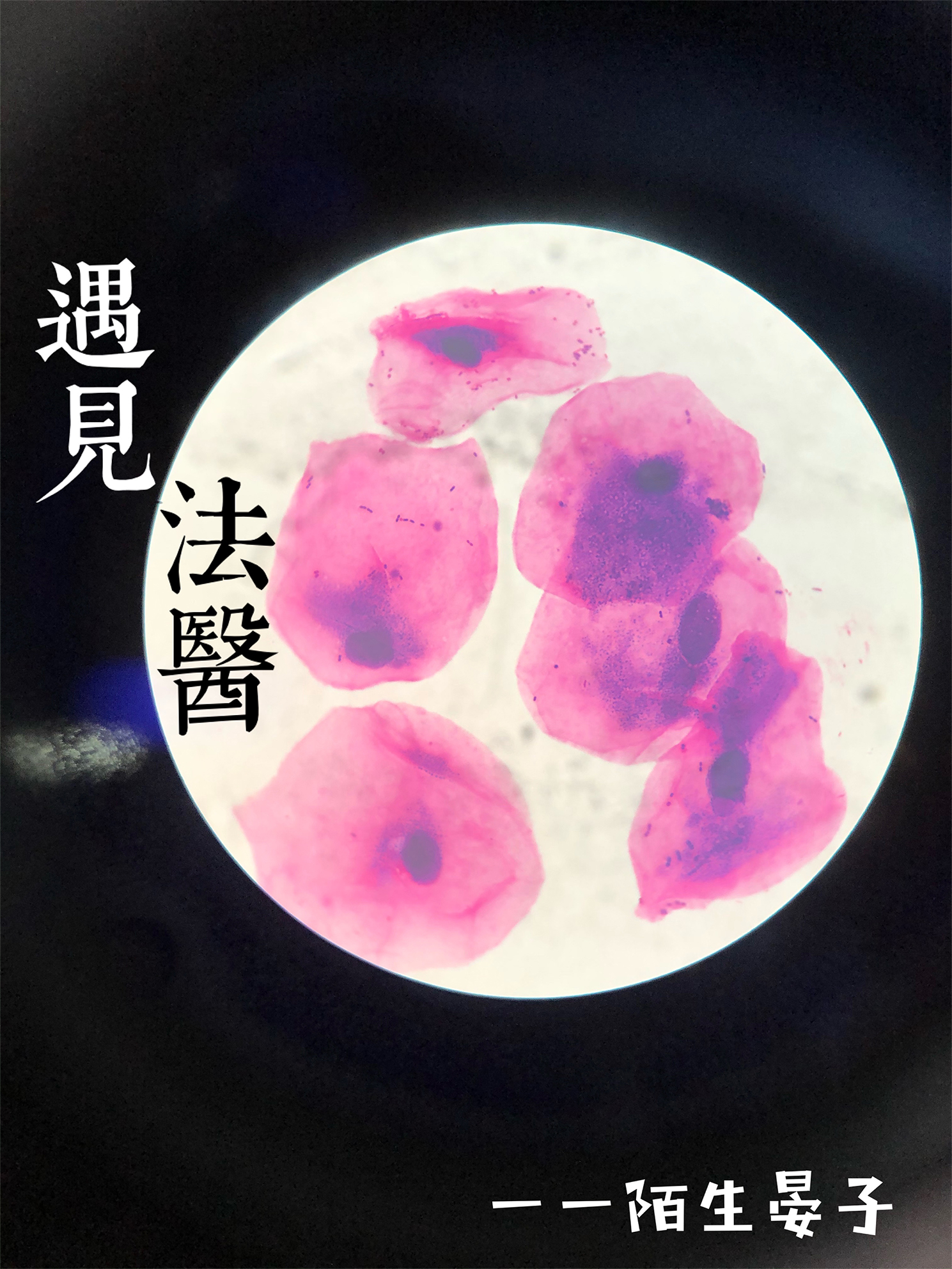晚膳时间已过,崇阳宫灯火通明,景阳帝被淹没在无边无际的奏折之中。从傍晚时分晚膳过后,子悠等人离开,景阳帝就命人将御书房的奏章搬到了崇阳殿,就此一头扎了进去。
“皇上,皇上,”犴司轻手轻脚的走到景阳帝跟前,轻声唤道,景阳帝头都没抬一下,“皇上,靳王爷已经在偏殿了,靖律司两位大人正在赶来的路上,皇上可要……”
景阳帝仍旧低着头,在奏章上写写画画的,“让王叔在偏殿等一下吧,”随即抬了一下头,手中的毛笔被他置于空中,“朕想与地牢相比,王叔怕是更愿意待在朕这偏殿了吧。”
森冷的声音激的犴司一阵发抖,旋即开口,“皇上刚才敏妃娘娘来过,托奴才给皇上带了宵夜,皇上也忙碌了许久,也该吃点东西了。”
“敏妃来过了?”景阳帝落笔的动作一滞,倏尔转头,兴味地看着犴司,也不再着急着下笔,置于一旁,“那她为何不进来?”挑眉看着犴司手里带着的食盒,“你可有拦她?”
犴司被景阳帝的问话吓得手一抖,食盒都差点掉在地上,慌乱之中急忙无措的回答,“回皇上,奴才怎么有那个胆子,皇上恕罪。”
“瞧把你吓的,朕只是问你一声罢了,”景阳帝就伸手要去拿犴司手中的食盒,犴司吓得往后退了一步,景阳帝看到他的动作,瞪了他一眼,犴司才怯生生的将食盒递了出来。景阳帝接过以后,将其置于眼前,未假他人之手,自己将它打开,继续说,“以后若是她再来,无他人的情况下,直接让敏妃进来便是。”
“嗻。”犴司在旁边看着,轻声应道,心里却在默叹。这都是主子,可是也只有重华殿的这一位才能让陛下放下手上的事务,转做其他事情。景阳帝对敏妃的喜爱他们都看在眼里,敏妃娘娘也是个贤良淑德的美人,能得景阳帝喜爱并非全无道理。
只不过就是苦了落华殿跟朝凤殿的两位了,进宫这么些年,与之陪伴的除了无边无际的寂寞,也就只有这周而复始的日出日落与花开花谢了。
“犴司,出去看着点,靖律司两位掌司使大人来了即刻前来禀告。”景阳帝拨弄着食盒,欣赏着里面各色各样的点心。
“嗻。”犴司应声,走出了崇阳宫。
大殿又恢复了平静,空无一人一般,景阳帝看着那被合起来的殿门,随手将食盒往一边一推,郁结在他眉间积起。刚才的食盒仿佛变成了毒药一般,让他避之不及。
许久之后,殿门再次被开启,犴司再次前来,“皇上,司律使大人已到偏殿,是否需要传二位大人过来?”
“宣。将王叔也带过来吧,这么久了,别再睡着了。”
邹闫与许褚二人一前一后进了大殿,靳王在皇御司侍卫的押解下,五花大绑的被带了上来。
“皇上,本王冤枉,皇上明察。”邹闫与许褚二人匆匆忙忙地被景阳帝从府内叫来,还不知道是因为何事,靳王爷的突然开口,也让二人连一个行礼的机会都没有。
“王叔,今日是地牢没有坐够么?”景阳帝脸上的厌恶显而易见,怒极将手上的奏章的“啪”的一声甩在了地上,“王叔可要仔仔细细、原原本本地将这些从头到尾的看一遍,再好好想想要不要跟朕提冤枉二字!”
“皇上,皇上……”靳王被侍卫甩在了地上,俗话说“虎落平阳被犬欺”,他在这一天之内体会了遍,昔日的所谓的“至交”现在都恨不得离他远远的,更没有一个人愿意出面为他求个情。此时竟然连侍卫都如此苛责他,手段粗暴至极。
“王叔,想要说话前还是先过过脑子,不然朕害怕王叔没有那么多的脑袋被朕拿来砍!”
“皇上,本王……”靳王在地上试着爬了好几次都没有东西可以支撑他站起来,反而在挣扎的时候将自己推入了那一堆所谓的证据之中,面色惨白的逃到一边去,“皇上,这都是假的,凭空捏造皇上也信么?”
“证据确凿,王叔却说是凭空捏造,此言竟然出口,朕该佩服王叔事到如今还如此有胆子么。”景阳帝讥笑。
“事到如今,本王也不想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解释什么了,”靳王如今看着还是那一个人,可不知道从哪里又与早朝时候略有点不同,就连刚刚上殿时候的张皇失措,似乎一刹那都不知踪影,“皇上您已下令将本王押解入牢,证据确凿却不急着给本王定罪。皇上心里在考量什么,本王虽然不能尽数知道,可心里还是会了解的七七八八。”
“王叔如今还能看的这般透彻,实数难得,”景阳帝不知道又从那成堆的奏章里发现了什么,从其中抽出了一本,“啪”的丢在书案上,“只不过若是在事发前有这般心境,现在也落不到这步田地了吧?靳王叔,您说呢?”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既已回天乏术,本王也只好认栽,人命本就在一朝一夕之间,生又何妨,死又何惧?”
“那王叔不妨直接认个罪,将私下里所做的勾当一五一十告知,岂不是可以少受些皮肉之苦?”
“皇上这是打算将本王跟那玩意儿一起埋葬,长眠于地下么?”靳王嗤笑,“皇上可是会那般的肯定,本王会将那东西带在身上,等本王人头落地的时候恰好留着跟本王同眠么?”
“王叔这好像是将早朝时候痛哭流涕的样子完全抛之脑后了,”景阳帝嘲讽,早上他张皇失措只差屁滚尿流的样子还历历在目,此时却又跟他摆起了谱,“王叔如此说,可是觉得自己手中还有朕千方百计想要得到的东西,而它还刚好可以作为与朕谈判的筹码是么?”
“皇上,为何不理解成为是本王的请求呢?”靳王冷笑,无神的眼眸转向那个他心里恨得咬牙切齿的人,“本王既知这一次凶多吉少,皇上如今没有将本王当即发落也不过是因为忌惮本王手里的九军令,九军令一日不在皇上手里,皇上都会睡得不安稳,本王这话说的可对?”靳王从地上爬起,瘫坐着,不看任何人,双目无神好像已经没有了灵魂。
“王叔,你……”景阳帝倏尔坐直了身体,靳王早朝前后表现差别太大,即使是景阳帝他有心收回九军令,靳王爷有意上交。可是景阳帝却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放松了警惕。未到最后一刻,就随时充满了变数,他丝毫都不能放松。
“皇上,本王只求一件事,若是皇上答应,不止罪行本王供认不讳,九军令本王也双手奉上。”靳王仿佛看到了希望一般,目光灼灼一下子焕发了生机,景阳帝不由自主的会去想他是不是又在演戏,又在装。
“王叔可是在说笑?证据确凿,即使王叔否认又如何?最差的结果无非是零口供定罪罢了,王叔可是黔驴技穷了,竟会想出如此荒谬的想法?”
“皇上何不听本王说完呢,毕竟当年一事还有先帝牵涉在内,皇上可是都忘了?”靳王缓慢的提醒着景阳帝,景阳帝眸子突然间变的十分凌厉,“王叔请说。”
“皇上,本王知道你不喜皇后,宫里常常冷落于她。皇后她虽然没跟本王说过,可本王自己的女儿自己清楚,她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本王作为她的父王又怎么会不知。”靳王喘了一口气,“本王这些罪证一出,自知免不了诛连。可否皇上念在皇后对皇上痴心一片,本王又将九军令双手奉上的份上,保住本王的女儿?”
靳王这时候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王爷,他只是一个父亲,自知死到临头只求给自己的女儿一条生路。
只不过他的态度变化的如此之快,又是为何?
“王叔说这些不觉得晚了么?罪名昭昭,每一条都是株连九族的大罪,早知道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四年前,先帝弥留之际,曾允诺九军令在本王的手中一刻,就有一个向皇上讨要恩赐的机会,现今先帝既已驾崩,这话可还算数?”靳王痴痴一笑,毫不意外的景阳帝拒绝了自己的请求,他只好提及了多年以前的往事。
“……”景阳帝看着靳王,目光晦暗不明,一直没有开口。
“邹闫大人,许褚大人,现虽皇上主事,只不过先帝之言可还算数?”等不到景阳帝说话,靳王改变了目标,一旁听的浑浑噩噩的邹闫、许褚二人被波及,二人沉默。
“自然是作数的。”许久,景阳帝才开口,一声似有若无的叹息在空气之中飘荡,“王叔如今是想要求这个恩赐了?”
“皇上,事情既然因合阳一事而起,本王甘愿接受处罚,临行一言,只盼皇后可以有一个好的归宿。她既已经嫁于皇上,成为皇上之妻,本王只希望皇上可以给她应有的尊荣。”靳王如油尽灯枯一般,虽还有些人气,却无半点生机。
“应有的尊荣,王叔可是指什么?”景阳帝反问道,手上拿着刚才抽出来的奏章,缓缓打开。
“皇上知道的,难道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