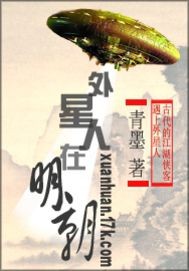两打手得令,随即一面挽起了袖子,一面缓缓朝长风靠近。
长风见此,一时近乎张皇失措,便想着对方人多势众,若要硬拼,定是吃不了兜着走,为今之计只有想办法从二人手下溜走。
然还未等长风想出溜走之法,二人之手便要朝他伸来,他亦不甘束手就擒,只得以自己向曾鸿宇学得的三两招功夫抵抗。却是片刻一不留神,便被身后的一人死死抱住,难以动弹。方使出全身力气拼命挣扎,不止地使劲抬脚欲踹那其余一人,却怎么也踹及不到。
便在这时,他身前那打手竟抱起巷子边的一箩筐,猛地一下朝他头上框去,霎时间,他只觉脑袋一阵晕痛,眼前一片漆黑,欲要将头上箩筐取下却被人重重按住,使不出一点力气。忽地,又被身后那人猛地一推,扑通一下趴倒在地,接着便是数不清的拳打脚踢。
他尽力地蜷缩着身子,强忍着浑身的疼痛,欲要奋起反击,身体却已疲软之至。这感觉就如濒临死亡一般,连呼吸都急促到了极点。
好在吴子远虽十恶不赦,却也有所畏惧,怎敢闹出人命。他觉得至此也教训得差不多,方命两打手道:“好了,今天便到此为止。”
二人得命,先后停了。
吴子远这便缓缓行至长风身旁,俯下身子,一脸得意地道:“怎么样?这受皮肉之苦的滋味还不错吧?莫要担心,这仅是第一次,后面还有许多机会。但凡哪日爷爷心情不好了,你便又可享受这滋味了。”说罢方立身,对两打手摆手示了示意,“兄弟们,咱们走!”于是带着二人一同离去了。
听得吴子远已离开,长风这方慢慢地将头上的箩筐拿开。此时已是浑身疼痛无力,连起身都显得十分艰难。
忽地扭头间,竟感觉自己脸部有一丝尖锐的疼痛,不禁一怔,忙伸手摸了摸,竟觉其痛感愈发尖锐。经这疼痛感和手上触觉,便知脸部被划出了一道小口子,一时既觉心疼,又觉痛恨。只咬着牙,紧握着拳头,心中却满是吴子远那恶霸一脸得意的表情,此刻恨不得一拳打上去,将这世间败类打得鼻青脸肿,打得跪地求饶,如此方能解心头之恨!
这般想着,竟见自己全身上下沾满了灰尘,忙使劲地拍了个遍,却怎的也拍不净,心中愈发躁怒。而此时夕阳将尽,只得缓缓回家去。
终于至了村里,便去湖边洗了把脸,又用沾水的手将全身上下的灰尘拍了个遍,这方敢回家。
至家门口,身上之疼痛也散去得七七八八,唯脸上的伤痕,怕被爹娘瞧见。这便忙又仔细地检查了一下自己衣裳,全身性地拍了一遍,方作出一副无事发生的样子,朝屋里走去。但见李氏正坐于堂屋的板凳上做着针黹,便呼了声:“娘!”
“哎!回来了?”李氏随口回道,抬头间,却见了长风脸上的伤口,当下一焦:“你脸怎的了?”说着放下手中的活,去看长风脸上的伤。
长风笑着摇了摇头,道:“没事。就是回家之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划伤了脸,擦点药酒便无碍了。”
李氏细看了长风脸片刻,自是心疼:“你看你,怎的这般不小心呢!这下倒好,给脸上添上一笔,多不好看啊!”
“怎的啦?”殳鹤亦突然间从房间里出了来。
“长风的脸被划伤了,我得赶紧给他找点药酒擦擦。”李氏说罢,便忙转身匆匆地去后屋了。
殳鹤行至长风面前,打量一番,竟是瞬间看出端倪,只小声问:“怎么回事?在外边与人打架了?“
长风听罢一怔,忙道:“爹!你莫要开玩笑,我乃一文弱书生,如何会干那般事!况且,你以前何时见我打过架?”
殳鹤仍然不信:“小子,你瞒得了你娘,瞒不过我。我一见你的头发和衣裳便觉有些不对劲,若不是你主动干架,便是被别人欺了。都这般大了,在外头安分点,莫要去惹事!”
长风忙“嘘”的一声道:“爹,你小声点,莫让娘听见了。——我得赶紧去整理一下。”说罢当下回了自己房间,关上门,只从柜中找出一件干净衣裳,换上了,又好生理了理头发,这便拿上脏衣而出。但见堂屋内,李氏已抱着一壶药酒正往一杯中倒,便故意道:“摔了一跤,衣服上沾了不少泥土灰尘,所以换了下来。娘有空帮我洗洗。”
“哎!放在盆子里吧!”李氏一面倒着药酒,一面答应道。
长风这方出门在盆架上拿了一洗衣用盆,将衣裳放于其中,又去厨房掺了几瓢水,如此衣一沾水,尘土自是不拍自散了。不由安了些心,便回堂屋中擦拭药酒去了。由此一来,这事便瞒过了李氏。
第二日恰好乃燕来书院休假之日,长风便未去书院。而他早便与彩苓约好,每月这日在湖畔见面,然此次心中却存好些顾忌。
所以这日一早便在院坝头立着,不停望向那湖畔,看彩苓来了与否。一时终于见彩苓出现在湖边,却见她也忍不住朝自己这面望来,心中一阵欣慰,便当下朝湖边去了。
这日长风脸上之伤已变成一道长长的黑色伤疤,在阳光的照耀下,竟变得十分显眼,故还未行至,便一眼被彩苓看见了。
“长风哥,你的脸怎么了?”彩苓走近心疼地问。
长风笑道:“昨日放学归家,一不小心在路上摔了一跤,划伤了脸。”
彩苓眉头微皱道:“怎的这般不小心呢,现在可还疼?”
“不了,既已结疤,便没了疼痛感,唯偶尔有些痒,如那蚊虫叮咬一般,想挠却下不了手。”
彩苓当下想起家中有一种金疮药,乃她爹于药店买回,大小伤口皆是适用,且效果极好,便想着将其拿来与长风擦拭擦拭,遂道:“这般,我回家为你拿点药,你在此地等着我啊。”说着便要朝家奔去,却被长风叫住了:
“哎!你想回家拿什么药啊?”
“金疮药!”彩苓回罢,又转过头,朝自己家奔去了。
长风这时想让她不必去拿,却是欲言又止,只因见她一股劲地要回去,想是已然叫不回,不禁一声轻叹。
未几彩苓又是奔着归来,待至了长风跟前,方一脸喜道:“长风哥,你看!这是我家必备的金疮药,你擦了它,伤口很快就能愈合的。”她一面说着,一面将药瓶递向长风。
“谢谢你啊!彩苓!”长风说着,接过了药瓶。
“没事,跟我还客气什么?赶紧擦些吧!”彩苓笑道,又思及长风自己擦拭当有些不便,“不如我来给你擦吧?”
“不用,还是我自己来吧。”长风笑了笑,谁料方一语毕,手中的药瓶便一眨眼地被彩苓抢了去。
“来吧!”彩苓当下将瓶塞一拔,便做好为长风擦拭的准备。
“这……不太好吧,”长风甚是犹豫,“若被人看见,好生尴尬……”
彩苓见了长风反应,竟觉他好似在刻意排斥自己,心中顿时生起一丝不悦。然她却又万般讨厌这种感觉,故当下又连忙将这不悦压制住了,只“哎呀”一声道:“有什么尴尬的?你我认识已不是一天两天了。”
长风表情透着些难堪,“我是怕被别人看见,以为……”
“以为什么?”彩苓忙问。
“以为……我俩在谈情说爱……”
在彩苓看来,自己与长风不正是一直在谈情说爱吗?尽管各自嘴上皆是未说,但心中却是清楚明白。此刻见长风说这般言语,一时竟生心伤,只当下将身子一扭,满口怨气道:“我有没有与长风哥谈情说爱,难道长风哥心中还不清楚吗?”
长风之所以会突然对彩苓心存些芥蒂,全然起因于那日乜子诚与李氏发生的口角之争。
尽管这事已过去约一月,但两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仍在他心中荡漾,好似就发生在眼前一般。所以他也怕,怕将来李氏真的会不答应自己与彩苓的亲事,到头来让彩苓徒增悲痛。所以他想,与其使彩苓将来受伤,倒不如现在便与她保持适当距离,不再有男女之念,如此倒也省了些事。
可是,他此时见彩苓对自己生气,心中竟生万般不忍,像心间瞬间失去了什么一般,几分难受。故当下也顾不得什么将来,顾不得什么父母之命,只得歉声道:“对不起,彩苓,我不该说那样的话,害你生气。其实,我对你的心意从来没改变过,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你就莫再生气了好吗?”
彩苓聪慧,又岂会不知长风心中所怀顾虑,然她也顾不得那般多,亦不想顾那般多,只知自己如今与长风在一起,心中便觉甚是满足,何必去想将来如何。此刻听了长风这话,便是扭过身一笑,略带些委屈道:“傻瓜,我又未曾怪过你,你想自己擦拭便自己擦拭吧,都是一样。”说着将药瓶递与长风。
长风却是笑着看着彩苓道:“怎的?你不愿帮我擦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