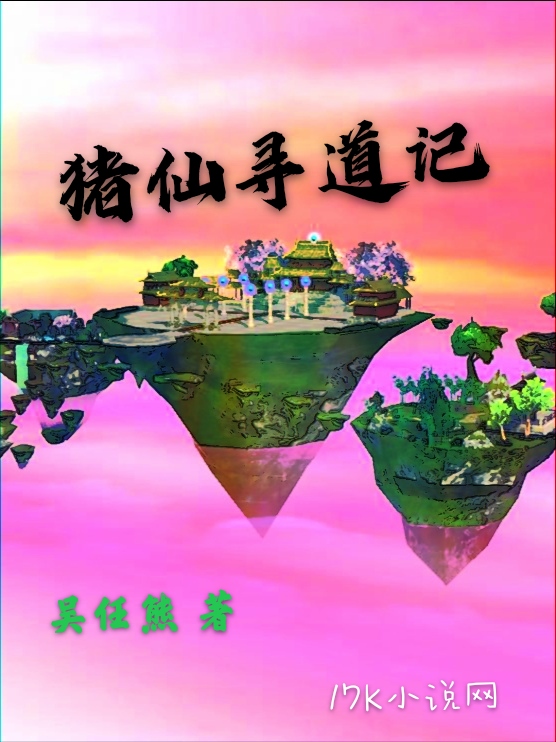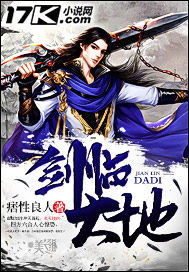彩苓不敢对乜云多言,生怕他提说起今晚这事,只故意打了个哈欠,道:“大哥,我先回房休息了。”说罢,便要朝房间中走去。这时却忽听得耳边传来乜子诚的声音:“彩苓!”
她心中一个寒战,忙停了下来,朗声应道:“哎!”
却听得乜子诚道:“回来了就好,早些休息!”
“哎!知道了。”彩苓朗声应着,一时间不由松了口气,庆幸乜子诚未提今晚的事,忙回房间去了。
然而她心中有预感,今晚这事乜子诚迟早会向自己提起的。
果不其然,第二日一家人正用着朝食,乜子诚便对她道:“丫头,昨晚的事可不能不了了之啊。老实承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彩苓本端着的碗又只得缓缓放下,语色小心吞吐道:“昨晚……我是……翻墙出去……同长风哥看花灯的。”
乜子诚听了当下便生怒火,直斥道:“死丫头!我就说嘛!这门锁着你怎么可能出得去,原来是翻的窗!还好我在街上撞见了你,如果不这样,你定是还要翻窗进屋,是不是?”
此刻的彩苓不敢抬头,亦不敢多言,只得乖乖认起了错来:“爹,我知错了……”
乜子诚接又责道:“你想没想过,你连窗户不锁便离了去,若是被盗贼发现,钻了进来怎么办?再多的东西也不够他拿啊!”
彩苓被乜子诚这般一说,眼睛竟不由得模糊了。换着平时他爹这般的语气,她顶多也就听着,甚至会斗上几句嘴。而今日,许是因有大哥大嫂在一旁,加之心中确实觉得有些不该,所以心生愧疚。
钱氏见此,不免心疼起女儿来,便对丈夫道:“好啦!人家彩苓也只是与心上人看了一下花灯,况且她又是知错,你何至于这般喋喋不休!”说罢又抚了抚彩苓的头,柔声道:“没事,你爹只是关心你,莫往心里去。快吃饭吧,凉了便不好吃了。”
乜子诚见女儿眼眶泛着些许泪光,自是不忍,便想自己语气却有些重,方不再说。故而这事到此也便罢了。
另一头,对于昨日的欢乐,长风仍是深深地沉浸在其中,便如一切尚在眼前,在耳边。一书生秀才,写诗当是他记录这难忘夜晚的最佳方式。于是便于这日提笔作了一五言律诗,诗曰:
元宵夜
春风携月暖,璀璨万重灯。
焱海龙鱼舞,星池凤雀鸣。
谜奇开笑靥,水雅引欢声。
莫意烟花醉,明眸最动情。
长风读着自己的诗,回忆着与彩苓相伴的画面,心中之喜难以言说。可诗歌再美,也仅是三言两语,哪能描得尽那些美好的故事与情感。
然而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因元夕一过,便是燕来书院开学之时,昨日一别,不知何时方能再与她见面。接下来的日子当少不了思念。
开学之日,长风早早便与村上书生乜永浩一同去了燕来书院。
至时,书院里仅不到十人,因学室未开,皆在院中候着。遂两三成群,欢快摆谈。长风乃本届新生,自只与永浩相识,便唯有与他默默站于一道。
不久,又一名清瘦书生前来,他举止洒脱,见了乜永浩微微一笑,眉宇间透着几分友善,拱手道:“乜兄来得够早啊!”
乜永浩忙拱手回道:“哪里哪里,张兄来得也不晚啊!”
那书生见了长风,并不识得,便好奇问:“这位兄台当是新生吧?我以前好像从未见过你。”
长风拱手回道:“正是。在下初来乍到,以后还请兄台多多关照!”
“兄台贵姓?”
“在下姓殳,名长风。兄台你呢?”
“在下姓张,单名一个波字。听殳兄口音,倒不像是本地人士,莫非你是从外地迁移来的?”
在此以前,长风从未觉得自己口音与本地口音有所差别,却未想到今被张波听出了不同来,顿时一阵惊讶:“张兄好耳力啊,竟能听出我乃外地口音。实不相瞒,在下老家在许州,去年由于战事,全家人不得不迁来本县,以寻个安定的栖身之所。——诶!在下自我感觉自己口音与本地口音无甚么差别,兄台又是如何听出这不同来?”
张波笑道:“兄台听自己口音自然听不出什么不同,但换着是旁人,这差别就显而易见了。”
长风听了却也似懂非懂,这其中道理当乃“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便只得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
这张波与永浩乃是多年同学,关系不错,但也算不上十分密切。张波性格张扬,又颇具诗文才气,因而常于众人面前摆弄文采,却也不傲,故多得他人欢迎。而永浩性格内敛,寡言少语却也极易相处,常抱书自啃,才气不比张波。
三人谈话间,院中书生又添不少,气氛逐渐浓厚起来。
“夏兄!你可算来了!”张波忽地扭头呼道。
只见得又一位书生朝三人行来。这书生长得不同一般——平常所见书生大都一个瘦弱之形,而他却透着几分健硕。
那书生一面走来,一面不慌不忙地拱手应道:“张兄、乜兄,别来无恙啊!”
张波这便指着长风道:“这位是我方才结识之友——殳长风,本期的新生。”又指着那书生对长风道,“这位是夏杓,我多年的好友。”
长风忙对夏杓拱手道:“原来是夏兄,幸会幸会!”
夏杓亦回了一礼,“幸会!幸会!”
身为文人,见面都喜好说些客气之语,长风此刻倒也不例外,只笑着对三人道:“在下才疏学浅,又初来乍到,以后还请三位仁兄多多指教啊!”
“诶!”张波拍了拍夏杓肩膀,“说向他请教倒是可以,说向我请教,那便有些闹笑话了。就我肚中所纳之书,还不及他夏杓一半呢!”
夏杓斜了张波一眼,道:“张兄,这便乃你的不是了,你的才华乃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般说便过于谦虚了。”又对长风道:“殳兄可千万莫听他胡说,他可是文采华丽,少有人及!——就于作诗而言,信手便可拈来,丝毫不必犹豫,且句句悦耳,受人称赞呐!”
长风一听张波喜好写诗,瞬间如得知音:“原来张兄亦乃才华横溢之人,失敬失敬。实不相瞒,在下亦喜好舞文弄墨,常作些诗词文章。但一直皆是孤芳自赏,无处觅得有才之人指点,胸中常怀孤独之感。今日能识得你们二位,以后再也不怕无人鉴赏我的诗文了。”
张波笑道:“要说诗文方面之才气,我倒是有一二两,可要说博学多识,我便真不及夏杓兄了。从古到今的书,他能看的皆已看遍,不仅如此,他还时常写些策论文章,可谓是针砭时弊啊!”
长风听了笑道:“二位皆是有才之人,何必你推我让呢!”
四人正摆谈,却忽地听见耳边传来书院童子声:“众同学注意!请整肃仪容,一刻钟后行拜师大礼!”
童子语毕,众书生纷纷整理起衣冠来。
待一刻钟过去,众书生便在童子引领下步入学堂,对桌上名号入座。
说来也巧,这长风的座位竟与夏杓张波二人的座位是紧挨着的,皆在一列,长风在中间,夏杓和张波则分别在其前后。
此刻终于见教书先生之面目——乃一位年过半百的老者,虽发须皆有些泛白,但却颇显精神,当是知识赋予他无穷力量。
拜师礼始。随童子一声令下,众学子双膝跪地。先拜至圣先师——孔夫子,九叩首;再拜教书先生,三叩首。
接着便是向先生赠送六礼束脩。
所谓六礼,即芹菜、莲子、红豆、红枣、桂圆。芹菜,寓意勤奋好学,业精于勤;莲子心苦,寓意苦心教育;红豆,寓意鸿运高照;红枣,寓意早早高中;桂圆,寓意功德圆满。束脩,肉脯与礼金。
拜师礼毕,同学互拜,以示互敬互助。如此所有礼节皆已完成,便进入正式开课之时。
元宵刚过,课上自然免不了元宵之话题。教书先生问众书生道:“可有人写过关于元宵之诗?”
此对长风倒是一个极佳机会,他可将所作《元宵夜》念与众人分享交流,写得好与不好,众人当也有个评判。当下便举手示意,得先生允许,方起身吟那诗。初吟时,但听得有同学交头接耳,却不知其讥赞。待吟完,竟闻得满室的称赞之声,甚见有同学忍不住拍手叫好,心中不禁甚悦。
教书先生这便捋了捋胡子,连连点头道:“甚好甚好!文辞俗华并兼,恰到好处,且刚柔并济。刚者气势恢宏,柔如见月光,实为难得之作。”
第一次受到先生夸赞,长风自是激动不已,就如那千里马遇上伯乐一般。
此刻那张波竟忍不住想调侃两句,当下起身朝长风拱了拱手,笑问:“敢问殳兄,这明眸是指何人之明眸啊?”
众书生听了,不禁纷纷而笑。“动情之明眸”自然是指心上人之明眸,此不言而喻,因而无须回答,若要回答,便只能说出那心上人的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