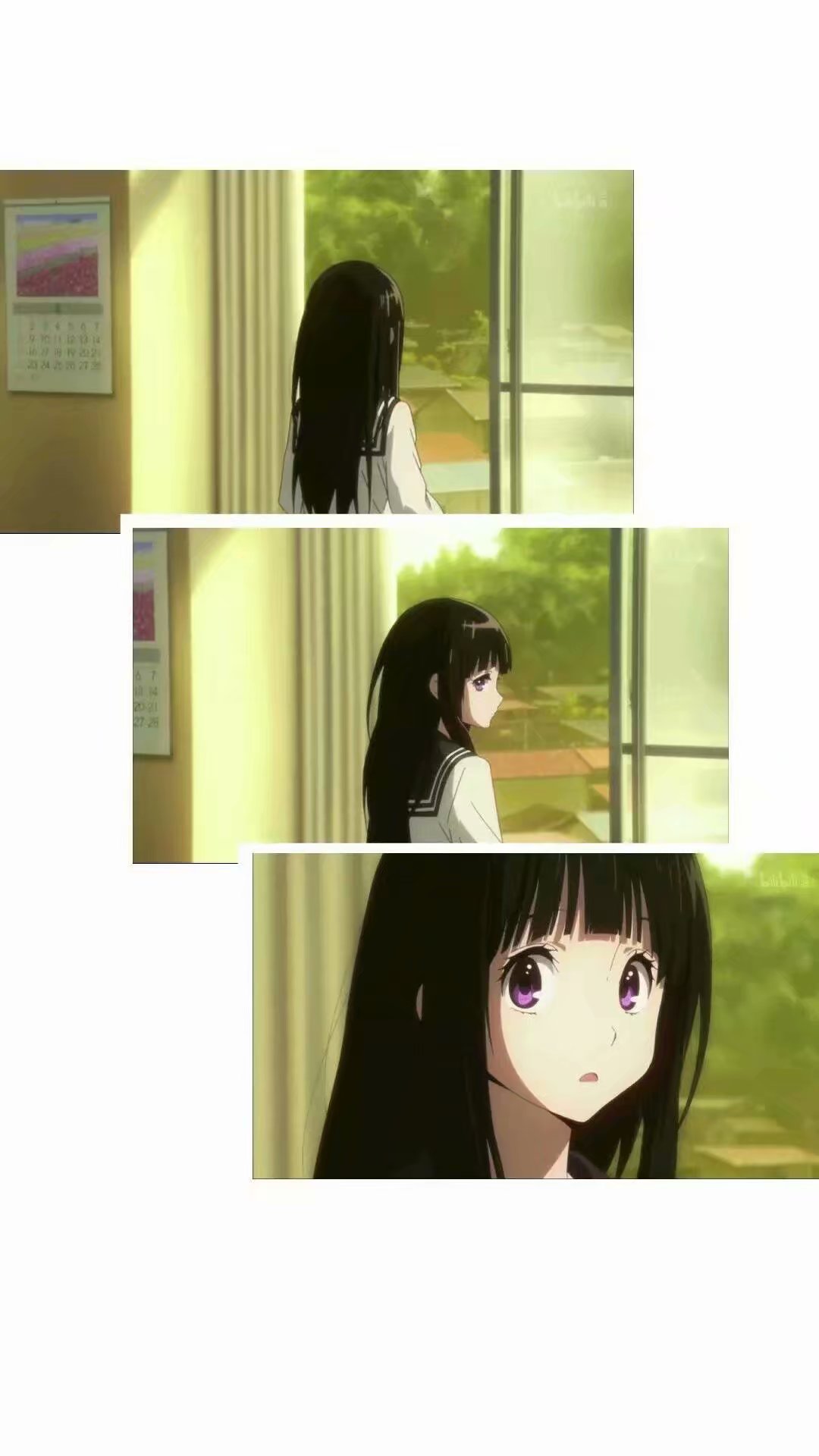“是,是!”林梅连忙点头笑着称是,“嫂嫂啊,以后一定和永浩好好相处,再不会让他受欺负了。”
倩凝并未理会,便行至黄氏及永浩跟前,对永浩道:“弟弟,方才大哥大嫂的话你可听清楚了?”
“嗯,清楚了。”永浩带着些孩声点头答道。
“清楚了便好。以后啊,倘若他俩食言,你还来找二姐,二姐便是拼了命,也要为你讨回公道。”
“谢谢二姐。”
这时,永浩的两位叔叔亦是赶来了,方至门前,见倩凝和永浩两姐弟竟是双双出现在屋中,不免又惊又喜。兴奋之时,便不禁问起这其中缘故。
倩凝方招呼两叔叔同黄氏坐下,又吩咐随从去准备些茶水来,永恒听了,竟是抢先去了。倩凝这便向两叔叔解释起事情其中的来去来。
因彩苓毕竟乃一外人,管不得永浩的家事,故从来开始一直是在门外瞧瞧听听,而一家人自然也无暇去招呼于她。既见永浩与她嫂嫂之事已被倩凝妥善解决,亦是心安了,方才觉不便多留,于是转身离开了。
时至这日,永浩失踪这事终究算是有了个较好的结局。因被倩凝说了一顿,又被逼许下承诺,故这日后,不光永恒,就连林梅也在对待永浩上有了些变化,不敢像从前那般对待一仇人般。可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林梅本就一自私心眼,要从根本上改变她对人的看法怎的可能,故她心中对永浩的偏见及厌恶仍未有所减轻,只是学会了隐忍,没有以前那般过分表露罢了。
※∽※∽※∽※
因与曾宏宇算得上是志同道合,加之又是口头上的结义兄弟,故长风隔三差五便要去曾宏宇家,时常除了谈论些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外,亦少不了闲谈轻聊,打发打发无聊的时光。尽管相识不久,二人关系却不是一般的好。
这日长风又如往常一般去到曾家,见曾宏宇的面色倒显得有几分激动,不似平常。方一打开门,他就一面将长风往院子里拽,一面道:“长风,来来来,我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
“重要的消息?什么消息?”长风疑惑道。不过他也大体能猜到曾宏宇要说的是什么——应是与当下形势有关的消息,因为他知道,曾宏宇一向最关注这些事,而且得知消息往往也是最快的。也许是因他毕竟出身于将门,有许多灵通的人际脉络吧。
曾宏宇未急着回答,只将长风拽至院中石桌旁,相与坐下,方才道:“大消息啊,你可知道,本月初一,宣和皇帝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即位了。”
“康王赵构即位?”长风语色透着丝丝意外。
“嗯,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继承的皇位,改元建炎,不过未改国号。”
长风对此甚是不解:“可宣和、靖康二帝不是尚在金人手中为俘吗?如今靖康皇帝尚未退位,赵构岂能于此时继承皇位,这不是……谋朝串位吗?”长风说到最后不由得压低了声音。
曾宏宇却是一脸的镇定,道:“于理确实有些不合,但也是无奈之举。金国从汴京撤军后,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然而由于张邦昌原为宋臣,后降金,开封军民对其憎恨有加,一大部分旧宋朝臣也要求他退位。万般无奈之下,张邦昌方以孟太后之名,下诏书立赵构为帝,赵构焉能不受。难不成还要继续任由一张姓之人坐拥政权?那样岂不是无异于改朝换代?”
“也是。”长风细细想了想,“不过这赵构即位……也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以前倒听说过一些有关于他的传闻,说他天性聪明,知识渊博,记忆甚好,每日能读诵书籍千余言,博闻强记。若真是如此,想来这赵构也应是一位明君,将来光复大宋,许是指日可待。”
“可贤弟你又可曾听说,”曾宏宇语色忽转,又显露出一丝忧色,“在金兵第一次包围开封府时,赵构曾以亲王身份在金营中短期为人质。后来不久,金兵再次南侵,他奉命出使金营求和,却在河北磁州被守臣宗泽劝阻留下。金兵再次包围开封,受命为兵马大元帅,宋廷令其率河北兵马救援京师,但他却移屯北京大名府,继又转移到东平府,避触金兵锋刃,也不知心中打的是什么算盘。”
“你怀疑他是因心中恐惧故意见死不救?”
“倒并非是我这样怀疑。你不妨去听听,天下人凡议论此事者,十有八九都是这般说的。以前,人们还以为他纯粹是因为心中恐惧,现在看来,他未必不是蓄谋已久。否则,他怎么可能保全自己,坐拥天下呢?”
在长风看来,曾宏宇这话亦有些合情合理,然而身为一介布衣,为政者的心思如何猜得透。即便猜透了,亦是无法印证。故他也无心思去管赵构心中究竟是如何想的,只作起了假设来:“曾兄,假如……我是说假如,你现在是当政者,为了大宋,你会如何做?”
曾宏宇不假思索地道:“自大宋建国以来,重文轻武已成了一项既定的治国之策,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武将数量严重缺乏且并无实权,尽管士兵为数众多,但却少于操练,并无可观的战斗力。而金乃游牧民族,个个身强体壮、粗野豪放,如狼似虎,相对于我大宋士卒,用以一敌十来形容金兵决不为过。故若换着是我,定然会首先从改变‘轻武’局面着手,更多地启用武将,加强对士兵的培养,进而提升我大宋将士的战斗力。”
长风倒是多忧了一步:“曾兄所言不无道理。可问题是,我大宋历朝之所以‘重文轻武’,原因在何处?想必是在为政者的眼里,只要武将的权力还在,便无时无刻不存在威胁。而倘若这权力过大,功绩过于显著,这威胁便更是显而易见了。故要改变为政者‘轻武’之念,恐怕并非易事。”
“你的意思是,不应当‘重武’?”
“并非如此。”长风摆了摆手,“我的意思是,‘重武’虽是必要之策,但真的实现起来无疑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说,在眼下这般危急的形势下,为君者需要对臣子怀有充足的信任,而且要善于识人,亲忠臣、远小人。唯有如此,方得复兴之道。”
“贤弟啊,”曾宏宇听罢一声感慨,“你思考问题总是存有诸多顾虑。我身为一介武夫,只知道以武治武、以兵敌兵,眼下金攻宋,而宋节节败退,危急存亡,所以在我看来自当振兴武力、兵力,这才是当下的关键啊。”
长风见曾宏宇似以为自己不同意他的观点,便当即解释道:“曾兄以为你我的观点相斥,其实不然。曾兄尚武,自然更倾向于从‘武’的方面去看待和分析问题;而我乃一介书生,自然更倾向于‘文’的方面。两者虽有不同,但也恰恰可以互补啊,并不矛盾。”
曾宏宇听罢细细一思索,片刻方才顿然大悟,当即猛敲自己的脑袋,“贤弟所言甚是啊,确实是我看问题不全面了。这其中的道理可谓是‘不以乱世废文,不于治时废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