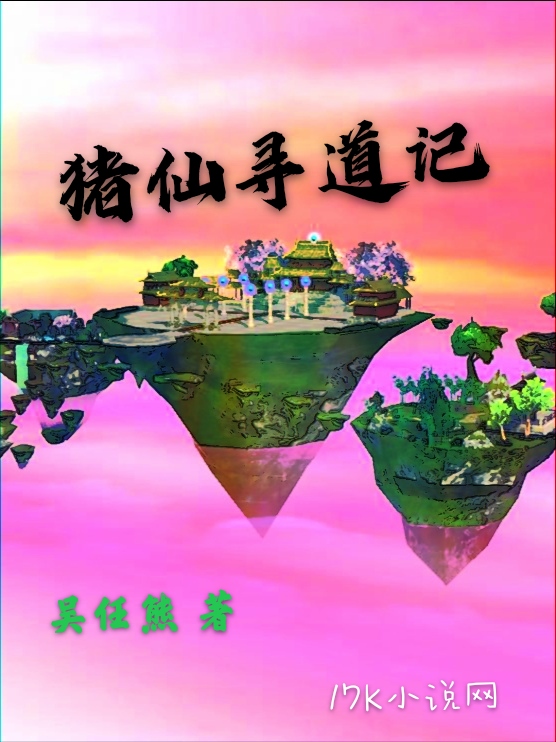“不可。”李纲摆了摆手,努力鼓足了气道,“辞职一事必由我亲自向陛下禀明,方显诚意。再说了,我好不容易克服艰难险阻,抽身来得这朝堂,岂能轻易言退。若此一去,恐怕便不能复返了……”话还没说完,又是捂嘴咳了起来。
“那你再坚持一会,相信陛下就快来了。”郑刚中和言说罢,方又回过了身。
这般片刻,终于听得太监呼道:“跪——!”自然是高宗上朝来了。
众大臣当即皆屈膝而跪,拜道:“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爱卿平身!”高宗行于龙椅上坐下,抬手命道。
“谢皇上!”
自约一月前辞职后,李纲便没来上过朝,即使是三日前被高宗授予招讨使,他也因身体之故,仅是上书以表辞意,并未来上朝亲奏。故高宗今日见他终于来,意外中透着几分欣喜,不过这也全是他意料之中的事。
“李纲大人,你今日总算上朝了。如何,身体可好些了?”
听得高宗呼唤,李纲早已从列中出了来,既见圣上相问,忙拱手以略带嘶哑的声音回道:“不瞒陛下,老臣眼下已是病入膏肓,恐怕是命不久矣啊……”
“命不久矣?”高宗惊中又带半分疑色,“一月前不是还好好的吗,眼下怎就恶化成这般地步了?”
“唉……这都是命啊……”李纲叹息道。
“可曾多找几位大夫看过?”高宗问。
“自然是找了,诊断的结果都一样啊……”
“大夫说,你所患是何疾病?”
“心疼病……”李纲话还没说完,当下又咳了起来。
高宗见他咳得撕心裂肺,脸红颈涨,连止也止不住,后背也不由丝丝发凉,便知其病不是装出来的。片时待他终于平静了下来,方才道:“爱卿可否要紧?若是要紧,朕这便传太医来给你看看。”
“谢陛下好意,臣并无大碍。”李纲忙拱了拱手,“臣今日来,便主要是为招讨使一事有请于陛下,还望陛下恩准。”
高宗一声轻叹,淡淡道:“爱卿之意,朕懂。你是想要让朕撤回圣令,不再授予你招讨使之职,可是如此?”
李纲当即屈膝跪下了,重重地道:“陛下英明!陛下委以重命,于臣本乃天大幸事,无奈臣体染重病,虽有心受之却已无力行之,实感痛恨至极。然臣命该如此,亦无回天乏术,还望陛下恕臣无能之罪,体恤臣垂暮之躯,收回成命。臣感激涕零,宁死不忘陛下恩德!”说罢便是重重的一叩首。
高宗听罢亦是感慨,只道:“爱卿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如今既是身体有恙,朕哪还敢有丝毫相逼。故便允了爱卿之请。”
“谢陛下!”李纲深深一拜。拜罢方起身,回了列中,其间又忍不住几阵巨咳。
这时见秦桧又出列,奏道:“陛下,既然李大人因为身体之故,已辞去招讨使一职,不如便让张俊将军代之。毕竟张俊将军方才打了胜仗,士气正盛,且眼下又无他任,正好前去,相信定能不负使命。”
秦桧口中说的这张俊便是后世列为南宋中兴四将之一的张俊,他于一月前被高宗派往福建一带镇压乱党,不过半月便已将乱贼剿灭,近日方才凯旋归来,故而位在朝列。
但见这时秦桧方一话毕,张俊忙已出了列,拱手铿锵道:“陛下,臣愿领命前往。”
“好!”高宗当下便喜了,“既然如此,朕便任你张俊为荆湖南、北路招讨使,命你即日前往剿灭乱贼,不得延误。”
“臣——领旨!”
此刻的长风倒是舒了些心。一是见李纲终于辞去招讨使一职,可以安心养病,不必再为朝廷之事操心劳碌,惶恐不安,二是见眼下终于有人前去剿灭荆湖乱贼,由此一来,远志与青云的大仇当不久便可得报,那时二兄之灵自可安定,自己和爹娘的心也可少了一结。
然而他心中的愁亦是不可避免的。想那李纲乃自己的前辈,为人一直是刚正不阿,处事严谨认真,故心中对他甚为敬佩,以其为学习之表。而在宋金之事上,其亦与自己一样,持主战观点,共同与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没少争斗,可谓战友。然而今日见他,却见其形容枯槁,咳喘欲绝,昔日雄姿不复存在,不由担心其身体垂危,故而心生叹惋。
※∽※∽※∽※
董庭殊前日说要给若柳弄一个放琵琶的架子来,倒也是言出必行,第二日果真便命人去街上买了一个回来。
这日他尚在管家房中书桌前翻阅册本,便见那上街的家丁已回来了,家丁禀道:“管家,琵琶架子已给您买回来了,是要送到若柳丫头房间里去吗?”
“哦,不用了,待会我亲自去吧!”董庭殊笑着道,忙又问:“对了,那东西放在何处?”
“就在门外。”家丁回道,一手朝门外指了指。
“就放在那里吧!”
“哦,好。那还有什么事需要吩咐小的吗?”家丁又问。
董庭殊听了细细思索一番,方道:“诶!你去看看若柳丫头现在哪儿,她若有空,便叫她来一下。”
“哦,好。”家丁应罢,随即转身而去了。
这般未至一刻钟,便听见又有脚步声进门来了。抬头一看,却见是方才那家丁与若柳来了。
“管家,若柳来了。”家丁带若柳至了房中,躬身禀道。
董庭殊见此,忙起身笑逐颜开地朝若柳行去,道:“若柳,你的琵琶架子已经给你买回来了。来看看可还要得。”说着方朝房外而去。
若柳则紧随之。
待至了屋外,只见那院中放着一两尺来高的棕漆三角形架子。董庭殊方忙行去将其提起,转身展示与若柳看,“便是这个。你可满意?”
若柳只看了一眼,便躬身柔柔回道:“管家一番好意,奴婢怎敢挑剔。”
董庭殊见此一喜,当下又道:“走,咱们去试试看!”说罢当下又忙朝丫鬟寝房那面行去。
若柳听了只得随之而去。
此刻的她心中不由生起好些诧异——这诧异其实在昨日就已出现些许了,眼前这身姿挺拔、面容俊美中透着成熟感的男子不是普通身份,而是堂堂一管家,地位在殳府中自不必说,可随时使唤府中上下的下人。而今,他竟会对自己一个普普通通这般丫头关心照顾入微,这自然叫人有些难以理解。莫非是自己的某个方面勾起了他的喜爱?或者是他对每个新来的下人都会有特别的关心照顾?
这般思绪纷飞着,未几,便已随董庭殊至了丫鬟寝房。
只见房间里,她的那把琵琶仍如昨日一般,静静地搁靠于墙边。
董庭殊这便将手中的架子展开,放于靠近琵琶的一处,当下又双手小心将琵琶拿起,轻轻放于了架子上。
既见眼前这乐器已安置好,他似乎瞬间松了一口气,待静看了片刻,方笑着扭头问若柳:“怎么样,还可以吧?”
“嗯。”若柳点了点头,露出一丝羞甜的笑。
“你满意就好。这啊,就叫做美器配美架,相得益彰啊!”董庭殊说着指了指眼前二物,却见若柳笑而不语,便顿了顿,“没什么事我便走了,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来与我说。你也忙你的去吧!”说罢便扭过身,负手将出门去,待走了几步,却又忽地停了下来,回头道:
“对了,我身为这府上的管家,每日需处理事务自是不少,故时常无暇去整理我那管家房,一直以来都显得有些杂乱。所以我想着,自明日起,你便每日抽些时间来为我打理一下。便主要是帮着摆放摆放书籍,打扫一下地面什么的。没问题吧?”
若柳听了,却无半点犹豫,当下便恭敬答应了:“管家安排,若柳自当遵从。”
“好。”董庭殊只道了这么一字,便又转过身,离去了。
既是管家吩咐的事,若柳自是得照办。故自第二日开始,她便每日都会去一趟管家房,帮着打理打理,往往先是为董庭殊整理书籍纸笔等物,而后再是打扫打扫房间。
在殳府中,身为下人是不得随意进入主子或是管家、管事房间的,要么房间的主人在,要么房间主人不在,得到允许的。每日,若柳往往都是在同一时间去管家房,除非因有他事忙过来时,才只得另改时间。
董庭殊考虑到自己时而有事在外,怕若柳来打理时因见房中无人而不敢进入,所以便对若柳定了个小小规矩——若自己在管家房内时,若柳自然而然可以进去打理,若自己出门不在,然又准许若柳进入打扫时,自己便会在离开前将门大开着,以示若柳可以进入。若柳便照着这规矩行事,倒是方便了不少。
在遇董庭殊在管家房而若柳又恰恰来房间打理的时候,其情形往往是这样的——
通常一人在书桌旁翻看着册本或是挥笔写着东西,而另一人便在一旁小心地整理摆放着各种杂物,互不言语,倒是安静。有时董庭殊遇上闲暇,便会随口与若柳闲聊几句,但因若柳为人沉静,不善言辞,故往往都是这边问一句那边答一句,对话短暂且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