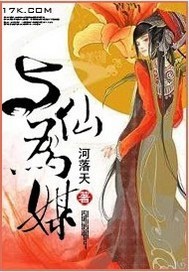夜里,烟雨遥从前面的舞楼,慢慢地踱回到后院,自己居住的小香楼里。她拾着裙子走上楼梯,向右拐了几步,推开门,进了卧房。
她坐在了梳妆台边,桌上的铜镜,映照着她如画的眉眼。她抬起手,开始拆解头上的发饰,心里却回想着白天皇宫里的比试,安陵对扶初国的第三局,和局。
她微微陷入沉思,神情恍惚,纤纤玉手拿着一支步摇,停顿在了半空。突然,一声不算轻的响动,惊回了她的思绪。她猛然回头,临院的一扇窗户大开,凉凉的空气涌进了屋来,有一个人,正蜷缩着半蹲在地上。
当那个破窗而入的不速之客,悠然而又傲慢地慢慢站起身后,烟雨遥眼中的诧异飞逝,不免意外。
她镇静下来,上下把人瞧了一遍,问,“你受伤了?”
狼半斜着眼睛瞥着她,摇头,不咸不淡地说,“没有。”她不过是发丝有点儿乱,身上沾了些灰尘和干涸的血迹而已。
烟雨遥冷静地看了她一眼,放下手中的步摇,起身去关窗,回身的时候故意说道,“你该赔我的窗子钱。”
谁知道狼却冷哼,“哼,我该塞给你脱衣钱!”她故意把塞字加了重音。
烟雨遥倏地红了脸,红得像和晚霞亲了嘴,妩媚又娇艳。她心里想,这个人,真好不知礼!
她坐回到梳妆台前,面朝着人,一本正经,“来干什么?”
狼便理所当然地回了两个字,“休息。”
烟雨遥挑眉,看着狼不管身上的狼狈,自来熟地直接躺上了她的床,“你是怎么弄成这副样子的?。”
狼把手臂枕在脑后,眼神瞬间晦暗……
白天的时候,她带着满心的杂乱、无从梳理的情绪离开了逍遥王府。她没心情再进宫,府门外抢了拉马车的马,就在路上发泄狂飙。
后来,她也不知道到底过了多久,等她无意识地放慢马速,让马慢慢地走回了住处后,已经是日当正午了。
小巷子里,烈日底下,她骑在马背上,逐渐眯起了眼睛,面前的场景,让她简直难以置信。院门踹飞,院墙倒塌,院子里那颗树在燃烧,几间屋子门窗俱毁,里面桌椅破碎,屋顶的瓦,碎了一地,分明像遭了烧杀抢掠,到处狼藉。
她一直在用理智平息、压制的怒火,瞬间冲破阻碍,火山爆发一样,冲天而出。失去了克制,滔天愤怒,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更要汹涌猛烈。
她任由情绪大肆倾泻,像个阴曹地府里来的猛鬼,周身席卷起黑暗风暴,勾魂索命的骇人气势侵袭每一个角落。
她阴寒狠厉的目光,狠狠一扫,说出口的话,平静异常,“我人都出现了,你们再躲着,还有意义吗!”
话落,十几道蒙面黑衣身影,纷纷从残破的屋内窜了出来。狼冷冷地盯着他们,相互对峙中,她忽然跃下了马背,一步一步走进了院内。
然后,就近,她轻易解决掉了一个人,夺下兵器,提了刀,举起便砍……
什么叫杀人,手起刀落,捅了心,切了肺,开了膛,破了肚,抹了脖子,斩了脑袋,这才叫杀人!
一场怒战,厮杀喊叫,血肉横飞,狼残忍无比地解决掉一个又一个蒙面刺客,生生杀红了眼。
没过多久,该死的人,就都死了……
狼握着还在滴血的刀,站在血迹斑斑的废墟里,看着满地的尸体,失神地站了很长时间。她抢来的马,早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这里,只有她在站立。
忽然,她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
她眼睛动了一下,四周看了一眼,神智大半恢复。她把手中的刀扔开,顿了顿,还是上前查看了最近的一个尸体,然后对着空气说,“收拾好。”
狼走了,她走后许久,杨明和王铭之才敢慢慢出现,她的样子,确实吓到他们了。他们互相对视一眼,都不由得叹了口气,这里的位置偏僻,周围也没住其他人,平常根本不会有人路过,就算有人,现在也绝对不敢冒头,所以,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慢慢清理。
狼漫无目在临近的小巷子里穿梭,理智回归后,她自然知道自己现在的样子不适合出现在别人眼前,但又不知道自己能去哪儿。她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忍不住自嘲,因为她意识到,她堂堂狼王,竟然无家可归了!
可她根本从来就没有过家,她的家在哪儿?她真正的家,在哪儿?
她绕着圈子走了半天,找到了一颗歪脖子树,跳上去,待到天黑后,她才选择来了烟雨遥这儿。
“知道是谁干的?”
狼嘲讽地勾唇,不阴不阳地说,“可能是我让他们输得太狠了,面子上挂不住了。”
烟雨遥就明白了,她也明白了,以这个女人的性格,是绝不可能就这么轻易放过那个始作俑者的。所以,她垂眸眨了眨眼,假装别有深意地问,“这么说来,今天晚上算是我收留你了?”
狼侧眸瞥着她,“你想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这是否算你欠我一个人情了?”烟雨遥扬起声调,淡淡揶揄,不过倒也真存了一份希冀。
狼登时不客气地冷嗤,“我也可以去窑子里找个姑娘陪我睡。”
烟雨遥又红了脸,温柔的脾气差点儿消失,险些冲上去掐人,她又气又无奈地嗔道,“你这个女人,百无禁忌,口无遮拦,什么话都说的出口!既然寄人篱下,睡上了我的床,难道就不懂低头?”
这次,狼干脆直接转过身,面朝里,不理人了。
烟雨遥愣愣神,然后被气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