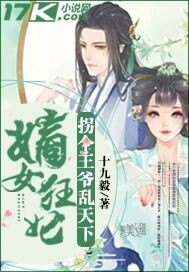离百越信陵一事已经过了月余,自上次别后,墨叔若对宴绝的踪迹一无所知。
她旁敲侧击想从墨公那儿得些消息,可仍旧无所获,此后无精打采,闷闷不乐数日,偏偏这时又传来了百越候和百越敬的死讯。近来因为饮食不常、休息不足,忧心忡忡的她终于病倒在床。
消息说百越敬在回闽越的路上被数名黑衣人围截,最后中箭身亡。百越候受百越郗一死的打击,俨然只剩了半口气,这次连唯一的后人都死了,终是连半口气都没得剩。
病中她一直在纠结百越敬的死是不是宴绝所为,导致胸口郁结,连喝了数天的水药。
直至这日墨公来看她,她坐在床上,靠着床栏结结巴巴问:“爷爷,你信么?敬表兄和百越伯伯的死……”
墨公熟练地削着苹果,顿也不顿道:“你是说外界传闻是天目峰所为?”
“难道不是么?”
他停下手中动作,终于抬起头来看她,叹息般:“你百越伯伯身子向来不好,年过半百又受如此打击,转眼间去了也是常事。”
或许是觉得自己不能劝服自己,她只能将问题一股脑丢给墨公。
“那敬表兄呢?”
墨公忍不住痛惜,一边摇头一边开口,“闽越人险,那帮老想着夺位的富贾商臣,乘机行事也是必然,可惜了敬儿……哎……反正,依爷爷对城主的了解,他断不会做这种卑鄙之事的。”
她低了头,皱眉想了会儿——“爷爷……”腹稿打了一大堆,吸了口气,“墨家,是不是真的想摆脱天目峰的控制。”
墨公眼神闪了一下,表情却没什么变化,“如果协商得好,两方也并不一定要起干戈。”
她抬起头。
墨公拍了拍她的肩头,“爷爷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话题一转,却打笑道:“如果他不是天目峰之主,倒是一个值得你托付终身之人。”
她尴尬地瞪大眼:“爷爷!!”
墨公哈哈大笑,“爷爷虽然年纪大了,可眼睛还没瞎,你想什么,我还能不知道。”
她结结巴巴道:“哪、哪有!不跟你说了,我累了,睡觉!”说罢翻身一滚,裹了被子包得跟毛毛虫似的。
墨公看着她小小一团的身影,眼中浮出几丝心疼。
“墨家虽以正道自居,但有时候也会身不由己做些违背良心的事。倘若墨家脱离天目峰,我想你日后也少些为难。但你大伯性子强硬,也不知往后会生出些什么事来,依靠着天目峰,说不定又能有益于你。”不知思绪走了几个来回,半晌才缓缓道:“爷爷从来没打算瞒你……”
墨叔若悄悄从被子中露出一双雾气迷蒙的眼睛,愣愣望着墙壁。
“墨家终是我放心不下的……也是苦了你……若不是当年你爹爹出事……”
墨叔若掀开被子扑倒在墨公膝头,早已是泪水横流。
“爷爷……”
墨公轻抚着她的发丝,眼神慈爱,“爷爷年纪大了,不知何时会撒手人寰,但凡是能想到的,爷爷都帮你做完……爷爷能给你的不多了……”
“乱讲……”墨叔若直起身来,哭的声音都变了,“叔若在世孤苦无依,还要爷爷亲择佳婿,看着我出嫁,安享晚年……”
墨公笑而不语,表情里多的是无奈痛心。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也不得不去深想。
“来,起来。”伸手扶她回床上坐着。墨公也不再说些丧气话,打笑道:“说起择婿,也不知是谁前些日子说要陪着老头子我,怎么这么快就变卦了,嗯?”
“爷爷!”墨叔若又羞又恼却又无可奈何,直气得跺脚。
墨公乐得羊须胡打颤,慢慢止住笑来,“不与你玩笑了,说说正事吧。半个月之后是城主生辰,我也想不到要送个什么,墨家数你主意最多,贺礼你就替爷爷好好做番准备,毕竟是城主上任第一次礼会,马虎不得。”
“我?”
墨公道:“我近日要去百越一趟,少说也要十来天。墨家上下事务你要处理妥当之外,去天目峰祝寿的事,也全权交与你。”
说难不难的事,礼物嘛照历届城主的依样画葫芦送就是,可这上天目峰,旧地重游不说,还得见宴绝。上次闹得不欢而散,她真的是不知道该用什么心态去面对。
“我会处理好的,爷爷放心吧。”一边应允墨公另一边却是一筹莫展。
墨公深感欣慰,“叔若果然是长大了……”五年前狠心送她去天目峰,到底是对的。他起身要走,墨叔若打算相送,又被他按回床上,“不必起来,好好歇着吧。”
“是。”
临到出门前,她忽然出声,“爷爷……”
墨公停下步子,回过头来,正看见她一席雪白中衣,跪在床上朝他扣头。
墨叔若头磕在被子上,重得抬不起来般,一边泪水肆意,一边哽咽着,“只要叔若在一天,必保墨家无虞。”
墨公表情半似疼惜,叹了口气,“好孩子……”
***
墨公离开顷安城后,墨叔若准备的贺礼也差不多在收工阶段。据墨氏旧账上记载,每一年墨家赠送的贺礼都是些奇珍异宝。到了她这里,却不想再送那么些劳什子,耗费物力财力不说,也没什么新意,再说了,毕竟是天目峰城主,哪会稀罕这些俗物。
墨叔若孤身步出墨家大门,直去东市的首饰店。那尚在柜台后算账的掌柜一见她,赶紧迎了出来,“大小姐来了。”
墨叔若负手一笑,“我的东西做好了吗?”
掌柜的笑容满面,连连点头,“是呢,您稍等我这就去取过来。”
见他去向拐角后门,墨叔若无趣地扒拉着柜子上摆放的各种金钗步摇。不到一会,那掌柜拿着一个锦盒出来,递给她,“大小姐,这玉石都按着您的要求,做了内部镂空,在表层抛光打磨,无论设计还是玉质都堪称一绝啊。”
看着他竖起的大拇指,墨叔若惭愧,“大师傅家的技艺在八国之内都是超群出众,我这小女子可不敢得这一绝。”
两人相视而笑。
墨叔若打开盒子,将一枚白玉扳指拿起来,转身对着门外的阳光打量。
如掌柜的所说,这枚扳指确实设计独特。
阳光下,戒指晶莹剔透,内部镂空曲折如流水。轻轻一晃,内置的一颗镶金珍珠跌跌撞撞滚动,就有清脆曲音从戒指里传来。
墨叔若原想着宴绝目不能视,再精致的东西他也看不到。所以专门设计了这个小玩意。这玉本就奇特,有异于常,能发音。加上刻意雕刻弧度,音调有了不同,珍珠滚动撞击,就有了独一无二的曲子。随身携带,无聊之余还能拿来玩耍,甚是有趣。
付完尾金,高兴离开了店铺。
此时正值酉正三刻,太阳正准备下山。街头人烟稠密,买办居多,生意来往,大都是为锄禾归家的丈夫准备晚饭吃食的妇人。学堂刚下课,有钱家的孩子买了糖葫芦坐着牛车慢悠悠晃着,也有的嬉闹着一溜烟去了,消失在巷子口。
墨叔若闲庭信步,腰间铃铛丁玲作响,东瞧瞧西看看倒是好生自在,却不知暗地里有人已经跟了她好几条街。
待她路过巷口,那人终于出手一把将她拽了进去。
墨叔若惊得头皮发麻,还没站住脚,拉她那人失去重心,顷刻间两人都摔在了地上,还是墨叔若当了肉垫子。
“好痛……”
趴在她身上的人虚弱出声,“墨姐姐是我。”
墨叔若惊魂未定,看着眼前这个十来岁的少女,“小瓷!你怎么……”
女孩朝她做了个噤声动作,低声道:“不要出声,你跟我来。”两人从地上爬起来,做贼般往更幽暗的地方走去。
少女虽然生得高挑,身体却瘦弱如纸。墨叔若搀扶着她,“小瓷你怎么了,脸色怎的如此惨白?”
她摇头,“我没事,去那边坐会吧。”
两人停在巷子里一座破土地庙前,在青石板台阶上挨着坐了。
“墨姐姐,我实在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只能来找你。”
面前的少女声音虚弱,抓着她的手却十分有劲。
墨叔若轻拍着少女手背,以示安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不要着急,慢慢说与我听。”
花瓷转头,看着墙角的破沙袋,瞬间陷入了一段难以自拔的回忆中,“我自生来就有隐疾,所有人都说我活不过十年,可十岁的时候我活得好好的,所以就没把病的事放在心上。爹爹也以为我的隐疾已经去除。但没想到的是,就在三个月前,我察觉自己的身体有了异样,有时候莫名其妙听不到声音、看不清东西。一开始我以为只是累了,但渐渐的,会不自主就昏睡过去,手脚也不大听使唤,我突然意识到那个隐疾不是说说而已……”她抓住墨叔若的手,浑身发抖,“墨姐姐,我好害怕……好怕突然有一天就那么死掉了……”
墨叔若看着她痛苦的表情,感同身受般泪水盈眶,“小瓷……”
“你离开天目峰不久,爻卿东也到了结业末,我借机向爹爹秉明我要出岛。我知道他是不会愿意的,所以用了谎言骗他,我说我喜欢东东,想跟他去渝江,爹爹就应了。”她抹了把眼泪,自顾自继续讲述,“离开天目峰后,我的身体已经不大好,在渝江一躺就是两个月,整日昏昏沉沉的。我的身体我自己再清楚不过,我怕我熬不长了……”
“瞎说什么!”墨叔若打断她,将一双红肿的眼睛投向黑下来的天空,深吸口气止住眼泪扶她起来,“走,我们先回墨家,我给你找最好的医师。”
花瓷拉住她,边哭边摇头,“我到顷安来找你,已经做好最后的打算。东东以为我回了天目峰,爹爹以为我跟东东好好生活在一起,多好啊,我会就这样活在这世上,我不想他们知道我死了……可是……”她声音忽然急促,情绪起伏不定,拼命抓着墨叔若,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眼泪豆大颗滚落,“墨姐姐,我好想见爹爹,想见他最后一面……你带我去见他好不好?让我偷偷看他一眼……”
看着面前十几岁的小姑娘,墨叔若有些想哭,奈何太难受反而哭不出来,只能吸吸鼻子点头,“好,我答应你,我带你去见他。”
三日后,墨叔若领着众人上了前往天目峰的船只,一踏上船墨叔若就神情恍惚的掉了队,只身一人四处游荡,不知道在船头站了多久。她担心小瓷的身体,可又答应了不会告诉玉华扶窨,原本为着宴绝而纠结,现在却尽都抛之脑后。
“墨姐姐。”墨叔若回头看去,少女捂着大红的厚披风,慢慢行来,“你在这做什么?让我好找。”
墨叔若伸手拦住她,将她扶坐在旁边的木箱子上,“船头风大,怎么不在船舱内歇着。”
“没关系,这几日我的身体已经大好,你不必担心。”
墨叔若点头,又道:“你找我做什么?”
花瓷道:“我睡不着,又没事做,所以想找你说说话。”
这么一说,墨叔若倒也是有很多疑问未解想找她要个答案。“小瓷,我问你个事。”
她疑惑,“什么事?”
“四年前天目峰青顶一事你可还记得?”
她似乎想起什么来,结结巴巴道:“当时我年纪小,记不太清了。”
墨叔若看着她的眼睛,“那你只告诉我,他的眼睛是不是那时候开始看不见的?”
她别开头,“我不知道。”
“你不用瞒我。”墨叔若苦笑,“他的眼睛……是因为我造成的是不是?”
四年前,宴绝受任上雪顶练习御寒诀。墨叔若那时年少不懂事,只觉得喜欢一个人就要时刻看着他,所以没事就喜欢偷偷跑去雪顶,躲在石头后偷看他练功。有一日傍晚,她正待下山,身后不远处忽然蹿上来十几个铁抓手,她好奇去看,悬崖下竟然有一群黑衣人攀着石壁正往上来。墨叔若吓得七魂少了六魄,拔腿就往宴绝的方向跑。
宴绝那时正在专心练功,忽然被打扰,硬生生吐出一大口血来。
墨叔若扶着他坐在地上,急得满头汗,泪水直落,“你怎么样?有没有事啊?”
宴绝闭目打坐运功,只觉丹田疼得厉害,看来需要休息段时间才能恢复了。睁开眼看着身边哭得惨绝人寰的少女,他拍拍她的肩头,“别哭了,我没事。话说回来,你怎么在这里?”半年前有过一面之缘,他倒难得还记得这个人。
墨叔若回过神来想起正事,赶紧拽他起来,“快走,有危险。”
宴绝懵道:“什么危险?”
话音刚落,不知哪忽然蹿出来一群黑衣人,瞬间将他们团团围住。
天目峰叛乱的事从来不少,又因为宴绝是内定少主,五宫七府的杀手有很多都是不服的,有人想杀他不足为奇。
那夜的杀手已经是拼死一搏,能力自然不容小觑,就算宴绝没有受伤也最多险胜。可惜,宴绝被墨叔若打扰,丹田疼痛使不出全部功力,又加上要保护她,硬是拼了个两败俱伤、玉石俱焚。
宴绝被砍了三刀,眼睛也被黑衣人撒的毒药损害。墨叔若替他挡了一箭,整个膀子都没了感觉。
一时雪顶归于寂静,黑衣人都死了,宴绝也昏迷不醒。墨叔若忍痛爬起来,将宴绝背着往山下去。
去往北山的路上恰巧遇见正准备归家的花瓷,墨叔若松了口气,整个人摔在了地上。
“爹爹师弟你怎么了?你不要吓我,你流了好多血……”她又去摇一边的墨叔若,“姐姐,姐姐你怎么样?”
“……救他……救他……”
“什么?”花瓷贴过去,边哭边点头,“好,好,我一定找人救他。你放心,爹爹师傅很厉害的,他一定可以救爹爹师弟。”
一口气没喘上来,墨叔若慢慢闭上眼睛,苍白的脸更加没了生气。
“姐姐,姐姐!”
她一番晃动,倒是让宴绝恢复了意识“小瓷是你吗?咳咳……”
“是我,我是小瓷。”花瓷哭的满脸鼻涕,“你坚持一下,我去找爹爹来救你们。”
宴绝闭着一双满是鲜血的眼睛,抓着她的臂膀叮嘱,“不要告诉师兄……不要告诉任何人你见过她……倘若师尊知道我的眼睛变成这个样子跟她有关,她必死无疑。”
“为什么?爹爹师傅不会那么心狠的。”
“小瓷!你一定答应我,听到没有!不能说,谁都不能说!”
“好……我答应你,我发誓谁也不告诉。”
从记忆里回过神,她没有再否认,“墨姐姐你不要自责,爹爹师弟从来没有怪过你。”
她笑得凄苦,“就算他不怪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见他了……”
自那以后,墨叔若没再与宴绝见过面,四年时间里,虽然偶有遇见,她也只是万千素人中的一个,并没有交集。她嘴巴很紧,他也伪装得很好,这四年都没让人发现他已经看不见东西,彼此相安无事。
“墨姐姐,你是不是还喜欢着爹爹师弟啊?”
墨叔若无言。
说什么喜不喜欢,早就是生命里忘不掉的人啊……
花瓷道:“我知道的,你肯定还喜欢他。就像我喜欢爹爹一样,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什么……”墨叔若惊得眉头一皱,“你喜欢玉华扶窨……”喜欢那个可以说是她养父的人?!
“我知道这种事,任谁都不会接受。”想来已经是经过无数阻拦,自己都看不开了。“我是喜欢爹爹,我想每天可以陪着他,小瓷没有要求其他什么,可在别人眼里,为什么就变成天理不容?”
墨叔若叹气:“你喜欢谁不好,为什么偏偏喜欢他?在世人眼里,他就是你父亲啊……这样的死道理,你的感情又怎么会得到认可呢。”
“可是我就是喜欢爹爹嘛……”她说着说着又哭起来,一个本该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却因为这种种际遇,变得多愁善感。
墨叔若紧紧握住她的手,只想这力道能安慰支持她,“既然那么喜欢,离开他难道不痛苦吗?”
她抹着泪,“我离开,不只是因为身体,我也不想自己的感情让爹爹困扰。”
墨叔若满腔心疼,“小瓷啊……”
“一想到有一天爹爹知道我对他的感情,我就好害怕……倘若他不再见我,到时候我该怎么办?天目峰的人又会如何看待我们?我是无所谓,却不能连累爹爹听那些闲言蜚语。可是……我……”
她憋得满眼泪水,说了半天也只能发出个颤抖的“我”字。
墨叔若伸手抱住她,轻轻拍着她的后背,“我知道……我知道的小瓷……”
花瓷靠着墨叔若的肩膀,抓着她的袖子满是无助,“我只是想像以前一样留在爹爹身边罢了,为什么只是因为我的感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该怎么办,墨姐姐我该怎么办?”
“傻瓜……”墨叔若将她撑起来,抹干脸上的泪珠,拿着她的手盖在她自己的胸口上,“你已经做过一次选择,可是现在,你心里好受吗?”
“如果换做姐姐,你会如何抉择?”
墨叔若站起来走了几步,望着大海发呆,“每个人对爱都有不同想法,我的爱,注定只配隐藏在黑暗中。但如果非要我选……”她愣了愣,坚定道:“我会告诉他。”
因为年纪尚小知道的不多,迫切需要人指导。她跟着站起来,“可是爹爹师弟说做人要多为别人着想,如果我告诉爹爹之后离去,岂不是给爹爹徒增烦恼。”
墨叔若转身走近她,“他说的没错,我说的也不全对。小瓷,感情是自己的,你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该听取外人的误导。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你。”
“谢谢你,墨姐姐。”
爹爹师弟说的对,因为爱他,所以更应该为他着想,不能因为自己的感情,就去改变他的人生。可是……既已到了生命尽头,为何不能放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她想告诉他,想说她如火般炙热的感情。那并不可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