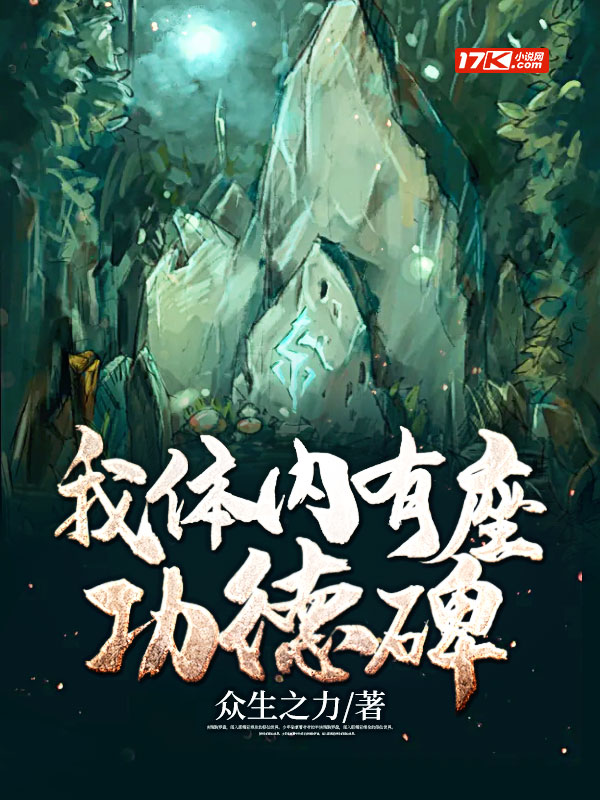一连几日,庄府的人如同困在热锅上的蚂蚁,自老太太起,至大爷庄顼,老少三代人病的病,伤的伤,晕的晕,可苦了下头当差的仆众,日前能胆大心肥赌钱吃热酒,这会儿谁也不敢怠慢偷懒。
那夜事发,四位老爷借口去祠堂焚香向祖宗祷告,实则去议事厅议论对策。他们几番议论后,终决定以庒琂卓府案为首要,看如何应对媛妃宫中的事故。遂而,急差人去请宗人府下头一名叫连城的老官员,意向他打听,再贿赂一二,讨个对策。那连城老官儿昔年与庄府有些旧情,得过庄府的恩惠,如今得了庄府的请,连夜驾马车来庄府,谁料,在府门外,被庄顼横冲直撞奔出来,惊吓到马车,那大爷庄顼被马踹飞了。连城老官儿与庄府下人送庄顼回东府,茶也未曾吃一口,便托有事,再也不敢停留。殊不知,这老官儿害怕出人命,上头因此查下来,一连几宗事务罪就此连根拔起,可不祸害了自己?庄府四位老爷自然不好留他,再者大爷庄顼伤得着实不清,赶着让大夫来瞧才是正中之重的要紧事呢,商讨卓府案对策的事就此作罢。
那晚,秦氏从昏迷中醒来,也不管什么老太太这边或追究子素那些混话了,一命守在儿子旁边。她见到儿子伤得那个样子,面目全非,手脚断的断折的折,七魂已没了三魄,怕是挺不过几日要亡人的了。秦氏哭哭啼啼,昏昏醒醒,一整宿真心没合过眼,养过精神。次日一早,丫头子们端来汤粥,她才吃一小口,便又昏过去了。
与此同时,北府也不安宁,道是为何?
原来北府还有一宗灾星祸害,包藏许多日,今日才显露出来给人知晓。那曹氏的侄儿曹营官因说对经商无兴趣,曹家人让他跟庄府三少爷一同赶“秋闱”应试,三爷庄玳恰是病重,这曹营官便自己去考了,可这人无实才学,在考场上作弊被抓个现形,提在牢里,此事二老爷早已知晓,却按下不给曹氏知道,这日,曹家人来寻儿子,这一桶破,曹氏才知侄儿被关起来了。
往日里,曹氏对侄儿曹营官可谓如待亲儿一般,让他亲近西府三少爷庄玳,一同作伴习学知识。如今,发生这样的事,她真真怨恨自己。于是,曹氏哀求二老爷无论如何也要将侄儿救出来,即便花多少银子也使得。
二老爷庄禄道:“都是你往日惯出来的孬东西,不学无术,如今祸害了他自己,连累他祖上不说,我们也要被牵连的。你代他求我,我求谁去?且不说救他无望,自家府里,满大庄府的人头还不保呢。”
曹氏被丈夫一通骂,再也不敢吭声,紧接,用尽法子打听,看有无法子救侄儿,再又去安慰曹家娘家人,总之,北府接二连三的事,没一件舒心的。倒可怜篱竹园娜扎姨娘的孩儿,便无人再关心,她整日以泪洗脸,无人可求,无人可助。
因实在不甘心,娜扎姨娘去找二老爷庄禄,看怎么寻回儿子,不料,庄禄忙里忙外,没一会子空闲,府中的乱事如麻,自己还得往外照顾生意。
这日,娜扎姨娘在二老爷那边,得个老婆子指示,那婆子说:“如今姨娘求谁也不中用,唯独去西府求三太太吧。现如今,到底是二太太指使盗了小爷呢,还是琂姑娘盗了去,谁也说不清楚。可琂姑娘到底是西府的干女儿,三太太是抵赖不过的,横竖找三太太要去比谁都管用,三太太还是郡主身份呢,不怕不担责不给你找的。”
于是,娜扎姨娘领着意玲珑,气煞煞的赶去西府。
而此时的西府,相对东府与北府要平静许多,郡主与三老爷庄勤只应对庄玳的病和老太太的病便了,至于子素指认庄璞与大奶奶苟且之事,他们当是没发生,毕竟,东府没责怪,自己若讨庄璞的不是,真是做实庄璞做了对不住兄长庄顼的事了。俱没提及庄璞那事,所以暂且相安。
娜扎姨娘到来之际,郡主与三老爷庄勤在屋里对坐,郡主向老爷庄勤提议,想将庄璞送去娘家王府里,叫王府约束管教。
庄勤不愿意,说:“自家儿子管教不当,现出大丑,赶去别人家,庄府还有脸?万万不能的。”
郡主道:“若是你我能管束,怎会有今日之耻。老爷知道的,璞儿那性子,谁管得了?老爷在,他忌惮收敛三分,老爷不在,他便是大王当道,不是出去乱晃,就是在府中捣乱。老爷真是责怪我,我也无话可说,终究璞儿是我们的儿子呀,岂有不管不顾之理?玳儿现这样了,好不好得了,谁都说不准,老太太也昏迷着,真不知往后还发生什么大事呢,就怕我们府里自此以后,安宁不得了。”
说着,郡主哭得了起来。
庄勤道:“自古慈母多败儿,往日我疏忽管教,你也得使出威严才是。我日日入朝公务,谁有那功夫天天守着他?再者说,二十好几的人了,比不得小孩子家家,真是太不懂事了。我看,不管不要也罢,让我们活多几年,轻松几年。”
郡主哭道:“如此说来,老爷连亲生儿子也不要了是么?”
庄勤被郡主这般问,一时无言,甩袖走了,说去看老太太,尽量逃避。
郡主趴在炕头,哭得个肝肠寸断。当下,宝珠、绛珠、玉屏等丫头谁也不敢来劝,正好,外头小丫头来,细声报说北府娜扎姨娘跟意姑娘来了。
听得,郡主才收住哭声,抹去泪水。转眼,娜扎姨娘等人进来,主觉地端礼。
郡主无心招待,爱理不理,冷冷的。
要知道,娜扎姨娘与府中娘儿们不同,拐弯抹角说话自然不会,只见她端完礼,便开口道:“请太太让琂姑娘还我儿来。”
郡主既伤心又生气,这会子听她寻儿,真真当头一棒,她紧紧的盯住娜扎姨娘看,稍后,厉声道:“是你的主意还是二老爷的主意?”
娜扎姨娘道:“谁的主意有什么关系,不见的是我儿子,我自然要寻他。”
郡主道:“莫非我偷了你儿子不成?”
娜扎姨娘道:“太太没偷,可太太的女儿琂姑娘是偷了去。”
郡主发出一声冷笑,也不知气糊涂了还是故意推脱,道:“我还听说是你们北府二太太偷呢,怎不见你去找她?你我也听说了,她把琂姑娘放走了,如今找我,这不是栽赃与我么?你们北府安的什么心,就你们北府有孩儿,别府里没孩儿了么?”
郡主看到娜扎姨娘如此关爱自己儿子,一时联想到庄璞和庄玳,自己万般伤感,才不假思索说出这席话。
娜扎姨娘可不管,仍旧道:“我们老爷太太不管,但我得管,我找不着,必须得找太太你来要。谁叫琂姑娘是你女儿。”
郡主怒道:“强词夺理,分明得理不饶人。你找人,我也想找人呢,这会子,我找谁去?你也不看看,府里都闹成什么了。我若是你,回去好好等着,该回来,必定回来的。”
娜扎姨娘道:“要不回我孩儿,我天天来。”
说毕,娜扎姨娘冷冷端一礼,一阵风似的转身走了。
如此神奇的人物,让宝珠、绛珠、玉屏等丫头好奇,跟出去瞧几眼,因见娜扎姨娘离去,这才回来回复,说:“篱竹园的姨娘走了。”
郡主气疼了脑仁,连忙揉太阳穴,扬手示意:“都出去吧!”
此刻,郡主再也不想多思考,多说一句,心里面,不住回念一句: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郡主来来回回念这句话,那偏房叫凤仙的犹犹豫豫的进来了,想必听见了。凤仙提着一盒子汤粥,来心疼郡主,伺候郡主的呢。
到了里头,放下盒子,端出一碗碧云精米粥,一碟子酱肉沫,一碗寿参汤。
凤仙暖气地道:“太太,活活精神,吃些吧。”
是的,这几日,一心照顾病人伤者,劳碌个日日夜夜,郡主不曾好生吃一顿了,歇一觉。
凤仙是郡主带过来的丫头,后来给三老爷做了偏房,别人眼里她是姨娘,私底下,仍旧是郡主的奴仆。
凤仙自主的拿起食物,喂郡主。
郡主吃几勺,便没了胃口,推着说不吃了。
凤仙道:“南府的在寿中居守着,大姑娘也去。老太太那边,伺候的人手是够的。太太趁个空儿,自个儿保养歇息应当的。”
郡主叹息道:“这会子,谁管得谁?我就是有心替老爷孝敬老太太去,如今你也看到,一个个的成什么样了。”说罢,郡主流下眼泪。
凤仙眼眶也红了,抹了抹,又道:“北府里头出了几桩事,怕比我们头疼的,太太不需知道,由着他们去。东府里头,大爷情形不太好,大奶奶被推那一下,后来大夫瞧过,确实是有了,现如今,大爷和大奶奶两个都在床上,大太太茶饭不思,病歪歪的,都可怜见的呢。太太啊,府里指望的怕只有你了,怎么着你也得挺得住才行。”
郡主道:“这些话我们关起门来说还可,到外头,你可别胡说,叫人抓个嘴短。你看北府东府那样,我们西府何尝是好的?我现如今能吃一口两口,可这肚子半口儿也放不下。”
凤仙安慰道:“到底,我们还有二爷不是?太太不为别的,也要为二爷保住身子呀。”
郡主一听凤仙说二爷庄璞,猛然来气了,道:“你休要提起那不孝子!老爷都不管了,我们该远远打死了扔到阴沟里喂狼。”
凤仙微笑道:“到底是太太十月怀胎生下来的肉,说的是气话。谁不管都成,太太可别那样想。”
有凤仙三番几语安慰,郡主心里舒畅许多,又多吃几口汤粥,精神略好些。
尔后,郡主打起精神,问东府如今怎么样,想过去瞧瞧。
凤仙却不建议过去,说:“子素那丫头胡言乱语,只怕大老爷和大太太心里怀恨,太太你如今过去不合时宜。何不等过几日,缓了下来再去,或问清楚子素,别让那事伤了东西两府和气才好,我看我们二爷人活泼些,不至于做那些大逆不道的事来。”
郡主点点头,道:“我也这般想,亏你冷静来劝我。”
凤仙笑道:“五丫头也关心太太,又怕打扰太太不敢来,我让她伺候她三哥哥去了。”
话说,凤仙姨娘的话里,不光关心郡主,还关心自己亲生女儿五姑娘庄玝,若府里有个好歹,到底,庄玝还得郡主这个嫡母照应才行。
郡主道:“你和五丫头有心了。”再思想一会儿,道:“如今,子素那丫头还关在刑房?”
凤仙道:“大爷出事后,大家赶着看大爷去了,南府的作了主,仍旧让关去刑房。这会子,必定在那里的。这丫头嘴巴贱,活跟疯狗似的,真不知琂姑娘当初怎就看上她。”
郡主便不说了。
再过一日,娜扎姨娘仍旧来讨要孩子,仍旧说那些不敬的话,说完走人,郡主只听不表态。后来,郡主吩咐说,娜扎姨娘再来,便说她往王府去了,而娜扎姨娘哪肯死心,非要见了郡主说了那些话才罢休。
不得以,郡主出来见娜扎姨娘,又听她哭泣唠叨乞求,反反复复,各自精神相互折磨。郡主恨得心痒痒的,却一点儿法子都没有,想跟自己老爷诉说委屈,老爷还一味责怪她,责怪庄璞,一味逃避不理会。
郡主也想过,实在难受就收拾收拾回娘家王府避几日,可又想老太太现状不好,她避回王府,以后会给人留话柄说嘴,西府的孩子们如何抬得起头脸?
这一日,郡主实在按不下火气了,打算去见子素,务必要她说个清楚明白,或让子素自个儿跟娜扎姨娘了断,别牵扯西府麻烦,更不可牵扯庄璞,叫他们手足情断。
岂料,见到子素,又是另一番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