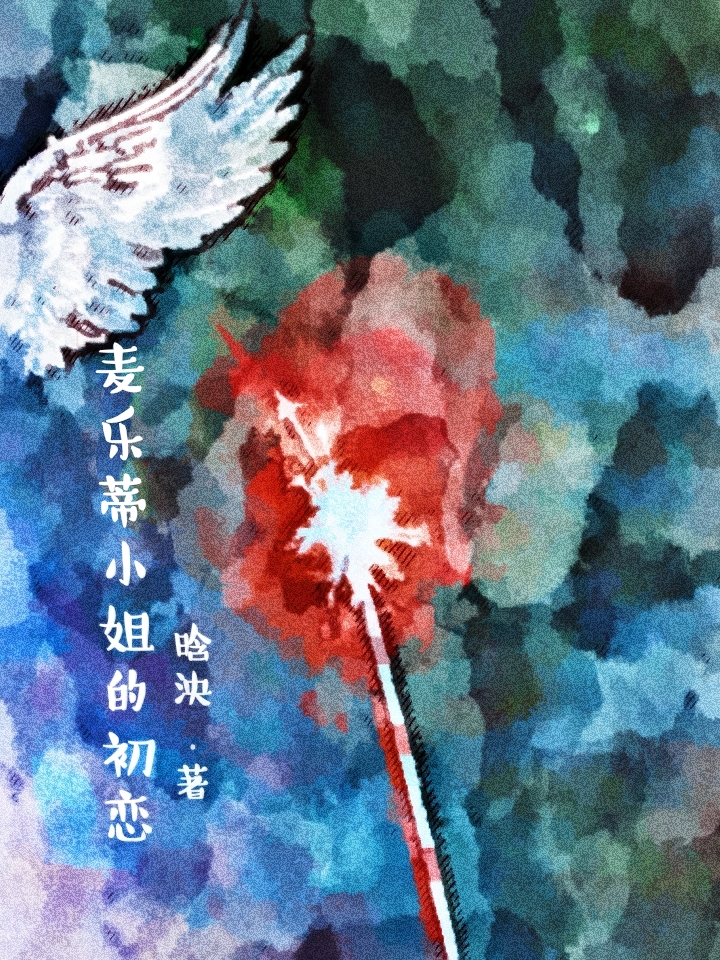一股刚刚刮来的让人非常有舒适感的暖风未消,地处奇缘山下的荷塘村人便又似乎陷入了寒冬。
一大早,妻子轻手轻脚地走到躺在床上的丈夫柳岩山身旁说:
“哎——我对你说,今个我不能再去干集体活儿了,肚子实在地撑不下去了,你我都几天没正经的吃一顿饱饭了,难道真的要等死吗?我必须瞒着队里去到野外找点儿野菜、树叶子或其它能饱腹的来煮熟了哄哄自己的肚子吧!”
翻来覆去也睡不着觉的柳岩山愁容满面地望着妻子说:
“都是我这该死的不争气,偏偏这个时候又得了病,不能为你分担忧愁,我死了就算了事,省得牵连了你,到时候你去找个好男人嫁了,我也心安理得了。只是,可惜,你的肚子里还怀了我的孩子,我即便是死了也是个罪不可赦之人呢!”
妻子不忍地用手拥了一下自己的丈夫,娇妮地说:
“不许你大早上说这些不吉利的话,我去去就回,找点儿好吃的就来喂你,有我在,就饿不死你,这儿的孩子还等着你挣饭吃,等着你好好的疼爱他呢!”妻子苦笑着摸摸自己的肚子就步入门外。
岩山妻挺着个大肚子从村边的小路偷偷地顺着一条小沟走到村西头。
她瞅瞅正在农田里一群干活儿的人们,生怕被在那儿领头的组长望见,那是要扣罚工分的。
她左右寻找,好歹搜寻到一线生机。
她迷迷糊糊的望到乱七八糟地趴在地上的,顽强地攀爬在树干上的忍冬的长蔓。可是,走近一看,它那没被寒冬冻坏的绿叶早已被别人抢先采摘得干干净净的了。
一阵冷风吹来,她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此时只见一道金光和一道银光,嗖地一声从忍冬葀子里向她扑来,陡然,似乎有两个滑溜溜的东西神奇地钻入她的怀中,又酥酥好像拱进她的肚子里。
“啊呀,难道是我中邪了?”岩山妻一阵子恐慌和胆怯。
“大白天的,是我多疑了吧?走吧,别疑神疑鬼的了,还是得顾自己的肚子饥荒啊!”
她不由自主的懊悔地叹了一口气,又望着远方的一片发绿的洋槐树走去。啊——洋槐树上只要是伸手能够采摘得到的枝桠上刚露头的嫩芽子,也是早就被别人採摘光了。她泄气地喘了一口气,可怜啊,俺想用树叶子蒸熟充饥哄骗自己肚子的希望还是破灭了。
然而,她心中偶尔泛起了一丝甜意——对啊,就是在这个地方,那是大部分忍冬刚露花蕾而又有一片忍冬花期正盛的时候,也是自己新婚不久,大概就是去年比此时晚一些的这个时候,她的丈夫柳岩山拽着她,在开满金银花的花丛中,疯癫地摘花。
白银般的花儿,香啊,香得使人醉!他采几朵,在自己的手中仔细的观赏,花儿啊,真美——雅秀,芳香。
“哎——看看啊,这花儿就像是你,多美啊,花儿比人人如花,媳妇如花醉芳华。你美了,我醉了——”柳岩山一下子把新媳妇抱着,亲吻了起来。
转眼间,银花变成了金花,满藤蔓上的金花黄啊,黄得像金子。
柳岩山又是非常兴奋地拉着妻子,说:
“你看这银花金花相伴相依,真如你我,你我真是醉一回啊!”他一边采摘,又一边对着被她羞红了脸蛋的妻子,说,“我去找寻最好的金银花采摘,采摘后晒干,卖给医药公司,卖来的钱给你做件花衣裳,让你更像个美人,美得像貂蝉,像杨贵妃。”
岩山妻被她的丈夫夸得无所适从,浑浑而飘然,只是不住地笑,差点儿笑出了声。
柳岩山望着面前如花似玉的新媳妇,突然把采摘下来的金银花抛洒在地上,又是忍不住地把新媳妇抱着亲吻了起来。
集体干活的社员正在远处大田里种庄稼,男的女的,一齐望着这对男女,双手拍着屁股,大声的豪爽的野蛮地笑着,哈哈哈,大白天的,两口子真是不害燥啊!哈哈——哈哈哈!
“让他们笑吧,笑死就没有工分了,咱不管他们,我俩只管我们自己的,我今天让你怀上了,你明年就给我生个娃,生个双胞胎,女的:一个叫金花,一个叫银花;要不生两个男的,一个叫春风,一个叫秋硕,我俩的愿望一定能实现。”柳岩山放开了新媳妇,不停地望着她,说,“人家都说这奇缘山下有神仙,金银花有灵气,当然了,我和你在这儿相拥相抱,也一定会感动了神仙,染上了灵气的,如果是真的怀上了,那么我俩的孩子也一定会有出息,一定会了不起的。”
“你个作孽鬼,真是太不地道,看看你,又是亲,又是抱的,满田满地的人你就不怕人家笑话,等不到天黑了,活活的被你给羞死了!”
“明媚的春光啊,你我何必不把握当前,把握当前的最美时光,难道你就不懂得沧海无情吗,我俩能美能醉就是非常值得的。”
“美什么美啊,醉什么醉啊,你把俺羞死算了,赶回怎么面对这些社员群众啊!”
去年,也就是在去年的那天夜里,柳妻就是在做着这样一个美梦。醒来,柳岩山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朦朦胧胧中,她看着柳岩山那高大挺拔的身躯,品尝着她那粗野蛮横的男人味,他也是觉得自己的男人真是好样的。
岩山妻从那天夜里起,真的就怀上了柳岩山的孩子。
柳妻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会儿的伟大创造性的时光,创出的成就和收获,处处好吃的东西堆成山,人人可以放开肚皮吃饭,过得是有史以来的幸福生活,做梦也没曾想到,现在一下子变成了挨饿了呢?家中的盆盆罐罐都是空的,整个的几间破屋子里连一粒粮食都没有,自己每一天都瞅着干集体活儿休息时的空子,在大田地头上或是沟洼里挖野菜摘树叶子充饥。
美梦怎么也替代不了眼前的现实,这种艰难的日月,让俺这一家子怎么熬得过去啊。
她一阵苦一阵甜的思虑着,想什么呢?有用吗?她想不下去了,肚子里不让她想啊,此时的肚子里翻肠挂肚的咕咕的直叫唤。
她移目远近,找呀找呀,看不到树上的绿叶子了,还必须在地上寻找能填饱肚子的野菜。
巧了,她望见了,在前边的一片荒芜了的土地上,她果然找到了一堆叫羊蹄青的野菜。可是,那些大棵子的还是已被别人抢先挖光了,眼前只剩下一些用手都揪不着的小棵子了。怎么办呢?田野里萧条冷落,别的绿色又没有,她只有低着头用小铲子找寻着那刚从土地下窜出头来的能用手捏得着的小棵儿挖。
她刚挖起一棵,抖了抖上面的泥土,便毫不犹豫地把这毛茸茸的一株野菜塞进了自己的嘴里,美极了,其实是饿极了——泥土味夹杂着一股清香的野菜味,泥沙在上面,她全然不顾,菜叶上的茸毛她也全不在乎,她实在的饿呀!她粗略地啄噘着,卷了卷舌头便咽下肚去,肚饥好下饭啊,可这不是饭也必须骗骗自己啊,她在这四五天之内肚子里没有一次是填饱过的,时不时的都是在饿得干咕噜的。
冬天,她偷偷地在生产队集体收剩下的大田里拣起的发了霉的山芋干不舍得吃不舍得吃就吃没了,自己菜园子里收的青菜也早已吃光了,她一急燥,就在两间草房子里左寻右找,像找魂似的,想找找是不是那儿还忘记了点儿好吃的?然而,坛是空的,缸是空的,去年吃公共食堂时偷偷攒点儿煮熟晾干了的山芋干子也早就吃光了,没指望了,实在的没指望了——
仔细想想啊,挨到了麦收不就有了希望了吗?她望着那一片片生产队的大田里的麦子稀疏疏的长得没有一扎高,她不由得又叹了一口气,看起来麦收的季节也没指望能吃上饱饭了。她和自己的男人偷偷在山坡下开荒种点儿麦子,在家前屋后开荒种点儿青菜,全被当成叫做“什么主义的尾巴”的被铲除了。你说,还能指望什么呢?
偏偏就在这个档口,她的丈夫柳岩山腿上的骨缝里又生了一个大疙瘩,一天一天的愈发严重,慢慢的就不能走路了。想来想去,自己心想偷偷地逃出去,到外地讨饭来养活自己的丈夫,可是,怎么能有个机会走开啊?再说,也不可以把这样拖着个病身子的丈夫丢下吧。
天快晌午了,岩山妻看看菜篮子里边挖的野菜真的够煮几顿饭吃的了,她好歹直了直腰。可就在这一刹那,忽觉得一阵难忍的肚子痛,她小心地揉了揉,越是痛得厉害。
难道是快要临产了吗?自己掐指一算,真的快到临产期了。怎么办呢?她着急的四处寻望,巧了,正好本家的婶子也在离她不远的地方挖野菜。她赶忙硬撑着着急地喊婶子快过来帮帮她。
婶子慌忙地跑过来搀扶着她说:
“看你这孩子,都这个样子了还自己出来挖野菜?”
她苦着脸说:
“婶子,家中没一点儿吃的了,不能干忍着饿啊,自己的男人又是那个样子,俺也得寻条活路吧!”
婶子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看了看她的下身,说:
“赶快回家吧,下边的裤子都湿了,大概是见红了吧?”
岩山妻的个子不大,但是,这时候的她丝毫不敢直着身子。本家的婶子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歹艰难地把她搀扶着回了家。
婶子生起了一堆木柴火,赶快让侄媳妇躺在床上,然后,把旁边的一条破被子拉过来给她盖着,又去针线筐子里找了一把裁剪衣服用的大剪刀,又在木柴火中慢慢地把它烧红消毒,等着孩子出生后好给侄媳妇剪脐带。
柳妻咬着牙一次一次地用劲,本家婶子一次次给她鼓劲。柳岩山也在另一边的地铺上小声地哼着,给老婆助威,说:
“俺起不来了,媳妇,你可得争气啊,坚持用劲,赶快把孩子生下来,让我死后能合上眼啊!”
婶子说:
“山啊,别说不吉利的,孩子生下了,你的病也就被喜气冲好了。”
岩山说:
“俺知道,这腿啊,是个祸殃子,好不了啊!”
婶子气愤地往地上喷了几口:“呸呸呸——”
“哇——”一声啼哭,孩子生下来了,一个丫头。
婶子刚把这个孩子的脐带给剪断,柳妻还在挺着肚子喊叫。怎么了?柳妻还在用劲,她觉着肚子里还有一个,一会儿一个女孩又“哇哇”地坠地了。
婶子一边苦着脸给孩子剪脐带,一边叹了口气说:
“傻侄媳妇啊,这年头,你真行,生一个都够你受的了,你还生了两个,这可怎办啊?”
柳妻说:
“这能怎办?俺愿意吗?”她让婶子把孩子给抱过来,左瞧右看,说,“您看看这两个丫头,生下来就水灵灵的,多叫人喜爱,这年头出生的孩子,也许是属于灾难之中的福星吧,但愿她俩命大福大!”她一把抓住婶子的手,也长叹了口气,又说,“哎,也罢,婶子啊,一头牛也牵,两只羊也放,这两妞即生下了,怎么办呢?一人头上一颗露珠,生下来就是一条命吧,我又不能把她俩掐死;哎,随她去,老天饿不死瞎鹰。”岩山妻不知是想高兴还是想着伤心,而她又一下子想起了早上出去采忍冬叶子的事,又仔细的瞧着怀中的孩子,说:
“你看看这两个丫头,好像要笑了的样子,她爹,你说这孩子啊,还许真是个富贵命,今早我去采那片忍冬的叶子时,就忽然好像有两道金银之光突然钻入我的肚子里,你看啊,此时这两个娃子就出生了,这也许就是这两个孩子的灵气吧!?”
在中国连续三年不平常的自然灾害的年代里,一对孪生姐妹出生了,柳岩山犟笑着爬起来跟妻子说:
“应验了,应验了,可惜这两个孩子真是生不逢时啊,怎么就不是两个小子呢!”他又尴尬地笑着,“灵气灵气,俺就给这两个丫头照着灵气起个好名字吧,别人家的女孩子叫什么‘红’‘绿’的,什么‘桂花’‘美丽’的了,这些名字我觉得俗气,按照俺早就准备好的,也是这灵气给带来的名字,就让她俩,大的叫金花,二的叫银花吧。”
柳妻想笑而又转为唉声叹气,说:
“哎,就是你这讨厌的死鬼,给俺造的孽,一个就难养活,还倒是来了两个,金花啊,银花啊,连饭都吃不上,想得倒美,想什么金啊,银啊的,你俩个可怜的傻妞,怎么就赶上了这个时期啊!?”
本家的婶子赶忙把菜篮子里的野菜拿过来,简单地摘了几棵,放在锅里煮了两碗野菜水给侄媳妇喝,顺便端一碗给躺在铺上的侄子递过去。
侄子端起苦涩的菜汤,望了望可怜的妻子,双眼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