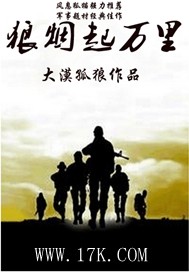彤云不知何时密布在了皇城的上空,“呼呼”的风声无孔不入,带来一阵阵阴冷,就像符坚现在的表情一般。群臣们战战兢兢地跪倒在地,此刻都不敢发出半点声响来。
墨蝶看向慕容冲随即低下头去,她心里十分清楚,穆云枔年少无知犯了此等大逆不道的过错,如果换作别人,此刻早已被拖下去斩了,但他是车师国的世子,秦国虽然强大,也不能随意斩杀属国世子,何况车师国主对符坚还有救父之恩。可是,这帝王的尊严不容亵渎,即便自己和车师国世子什么也没有发生,这符坚也不会那么轻易放过她的。
果然,符坚沉默了片刻,忍住心中的怒火,吩咐道:“来人,将清河公主押下去,杖责二十,禁足三月!”
符坚的声音听在慕容冲耳朵里,仿佛是门外滴漏中的水,才一出口就已成冰。他不敢再言,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番话非但没有给墨蝶解围,反而让符坚恼羞成怒,把怒火都撒在了墨蝶身上,他遮掩住自己不满的情绪,头也不抬的跪着一声不吭。
而那穆云枔听到要杖责墨蝶,他哪里还沉得住气,连忙说道:“一人做事一人担,我之前入宫时迷路了才不小心闯入了清河公主的院落,并非有什么纠葛交集。大王若要惩罚,便请惩罚我穆云枔一人,我愿替清河公主受这二十杖!”
符坚冷笑了一声,脸色却越发难看,说道:“既然世子这么说,那孤治你个擅闯后宫之罪,想必车师国主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将车师国世子一并押下去,杖责二十,以儆效尤!”
“大王,我是替清河公主受过,你不能打她,她是无辜的……”穆云枔不依不饶,但话还没讲完便被一人捂住了嘴拖了出去。
今日朝堂上群臣会聚,王猛和慕容垂当然也身在其中,他们倆都看出了这来自车师国的世子是个不谙世事的少年,当然不愿让他再次触怒符坚。于是王猛把他拖了出去,免得他再招来杀生之祸,还殃及了池鱼。
这一闹,谁也没有心情再继续宴饮下去了,群臣纷纷告退,这原本以示对车师国世子恩宠的宴会反倒成了问罪之宴,符坚努气难消,拂袖而去。
…………
深夜,桐宫,符坚专门为慕容冲这只凤凰新建的宫殿华灯通明,宫娥宦官们忙前忙后地准备接驾。而慕容冲早已沐浴更衣,他斜倚在胡床之上,任由瀑布般的散发泄落在他的肩头,俊秀奇美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他的心如刀一般冰冷,不见了常人的喜怒哀乐。
该来的终究要来,符坚的车驾停在了桐宫之外,片刻后人已经到了内殿。
胡床之上的俊美男子——慕容冲,看着符坚一步一步走到自己的床榻边,他坐了起来,将恨,将怒、将怨都通通深埋在心里。可他还未行礼,符坚的手已经抓住他的领口想要将他身上唯一的这件绸衣扯去。
慕容冲伸出冰凉的手紧紧地握住了符坚的手腕,他抬眸看着他,眼神淡漠疏离,可他这目光背后极力隐忍的不甘、不愿却更加激发了符坚内心的火焰。
符坚大概知道慕容冲内心的想法,他知道慕容冲忘不了亡国之恨,忘不了失身之辱,他也知道慕容冲恨他。但那又如何,他是大秦的天王,大秦的国运如日中天,慕容冲永远无法逃得出他的手心。
符坚收回手,看着慕容冲说道:“这些年,孤对你不薄,孤答应的事也都做到了,她享有着妃子所有的荣耀,孤也没有碰过她一根手指,可你,凤皇,仿佛你是后悔了,孤越来越觉得和你远了,说,你是不是恨透孤了!”他非常想听到慕容冲说出恨意,而不是假装顺从。
慕容冲却不想让他如愿,他漫不经心的理了理自己的衣襟,平静的说道:“蝼蚁尚且偷生,凤皇也不过如此,大王就是大秦的天,没有谁不愿意诚服在大王的羽翼下!”
“是吗?”
符坚冷笑着凑近慕容冲的脸颊,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声音带着怒气:“可孤分明看清你瞧她的眼神,那是孤从未见过的,你要明白孤可以给你们荣耀也会让你们一无所有,包括比性命更重要的东西,孤会做到让你们生不如死,所以,不要让孤失望!”
他一边说一边用力一扯,慕容冲身上的袍服便“刺啦”一声裂了开来。那健硕的肌肉,炫目的光泽让符坚失去了最后的理智,他狠狠地按住了慕容冲的脖颈,将他压在了身下。
慕容冲面颊紧贴着床榻,他没有反抗,只是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屈辱愤怒地泪水却止不住地涌出了眼眶,划过脸颊,无声地滴落在了床榻之上。
桐宫外的巨大梧桐树没有引来凤凰,一声声凄切的凌乱叫声不绝于耳,那是寒鸦们的聚集之所,受惊的寒鸦扑棱棱地飞起,让此时的慕容冲更加烦躁。
他睁开眼侧过脸去,又看见那亮着的琉璃灯心,他根本难以承受如此微弱的光亮,他手指一屈弹出一道风将那灯盏吹吸,内室里顿时一片黑暗。
许久,黑暗终于恢复了平静!符坚起身,将琉璃盏再度点燃后重又坐回胡床。
“你道孤今日只是为了那车师国世子的无礼才如此震怒吗?”符坚背靠着床沿,闭目说道:“孤是因为你,墨蝶生得如此美丽,想必你也是动心了,孤常常在想,孤为何要放过她?”
慕容冲仰头:“所以大王恼怒的原因是误会我为她求情了?”
符坚缓缓睁眼,转身看着床上的慕容冲说道:“你自己想什么你自己最清楚,可不要忘了这是孤的大秦,孤今日只是杖责她,若让孤知道你若对她动了念头,无论是你还是她,孤谁也不会放过!”
慕容冲笑笑,直视符坚的双眼:“大王想得太多了,凤皇此举不过是为了大王好,如今大王已成大势,应受北方各部的臣服,可是今日却唯独不见拓跋代国派使者前来,这是为什么?”
“你想说什么?”符坚被他的话挑起了兴趣:“你说是为了孤?此话怎讲?”
慕容冲轻咳了一声,说道:“那代国国主拓跋什翼犍和车师国本就交好,大王却因为这点小事就处置车师国世子,想必正让拓跋什翼犍有了理由说服车师国国王一起反秦!”
符坚冷笑:“他是自寻死路!孤要聚齐力量一举伐晋,本不愿再对塞外诸胡动刀兵,可你说的这代国真是不知死活,孤意已决,等春暖花开便亲自将代国拿下。”
“大王乃一国之君,大秦人才济济,何需大王御驾亲征?”
慕容冲见符坚终于不再提起墨蝶,继续说道:“凤皇的叔父乃不世出的虎狼之将,丞相王猛更是文武双全、智计高绝,大王随便派他们中的一员皆可成事。”
符坚摇头,叹息一声:“你叔父野心太重,只有孤一人可压得住他!丞相这段时日身体抱恙,也不宜远征!”
话已至此,可慕容冲不想放过这次机会,思虑片刻后说道:“那不如大王命丞相为帅,让叔父领一军听丞相命令,彼此间既可互相照应,也免得我叔父一人独大生出事端。”
符坚再次把目光投向慕容冲,低语道:“若你真是为孤好,此计甚妙,孤会斟酌!夜深了,你睡吧!孤还要去处理些政事!”
符坚说完便要离去,慕容冲起身行礼,待其车马远去,慕容冲匆匆掠出了寝室,随即他修长的身影便没入了黑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