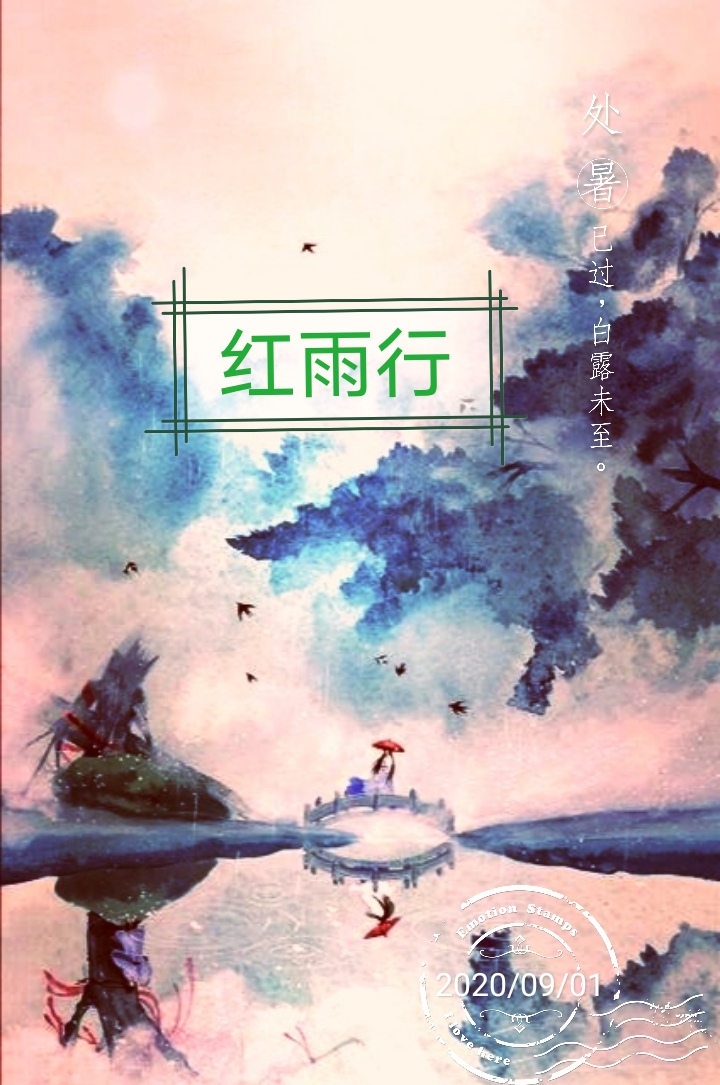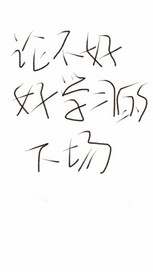楚王重重地倒了下去,倒在南郊辽阔的大荒原上,没了气息。他那一双眼睛依旧圆睁着暴凸而出,失神地凝视着白茫茫的天穹,死状之凄惨令人扼腕叹息。
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以至于长鱼酒和云樗都还来不及回神,楚王就已经没了气息。就连场上扮作东皇太一的桑柔也慌了神。她匆忙地摘下面具,手持冰刃立在祭坛上,神情严肃戒备。
吴起的部下以雷霆之速冲进祭场,吴起一指祭坛,十六名手持长戟的卫兵三步并作两步冲上祭坛,将桑柔护在中间。
就在这时,祭坛下沉默良久的屈宜臼忽然起身,朝着身后的人群高喊一声:“放箭!”
话音刚落,人群中陡然冲出数十名手持弓箭的卫兵。
原来人群中竟然隐伏了这么多弓箭手!
“嗖嗖嗖——”
五支利箭瞬间射出,呼啸着划破空气,直指祭坛上的桑柔而去。
长鱼酒的心脏在这一刻狂跳起来。
“不!不要!”云樗拼命地挣扎着想要挣脱锁链,可锁链却纹丝不动。
桑柔挥起了湛蓝色的冰刃。
“当当当!”
桑柔和吴起的部下奋力抵抗飞扑而来的流矢,桑柔将她那湛蓝色的冰刃舞动如风,锋利的刀尖在半空中带出一道道华丽炫目的光影,将密集如雨的箭矢尽数打落在地。然而箭矢的数目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桑柔连格挡加躲避,才勉强得以在流矢的疯狂夹击之中生存下来。
吴起的眼中划过一道狠戾的阴霾。“噌”地一声,长剑毫不犹豫地拔出,艳红的鲜血喷涌一地,浓重的腥味在空气里弥漫飘荡。阳城君倒了下去,倒在了楚王的血泊之中,鲜血慢慢在他的身下汇聚成河流,和楚王以及牺牲的鲜血混杂在一起,无贵无贱,分不清你我。
霎时间,数百名身着甲胄的卫兵冲上祭场,将吴起团团围住。大荒原上,吴起的部下和屈宜臼的卫兵已经开始了激烈战斗。金属碰撞声不绝于耳,短兵相接刀剑相杀,不断有人倒下,鲜血染红了荒原上的枯草,刀剑的金属声伴随着惊恐尖叫声,一声声刺激着长鱼酒和云樗的心神。场面一时间混乱到了极点。
楚王僵冷的身躯静静躺在一边,仿佛是这场流血狂欢的局外人。
“砰砰!”
长鱼酒奋力地砸着铁窗。
“桑柔有危险,我们必须去救她,可我们现在出不去啊!怎么办?”云樗焦急地问道。
“该死的!让我出去!”长鱼酒咒骂一声,用尽全身力气猛砸铁窗,可牢固的铁栏杆纹丝不动。
“吴起这个蠢货!娘的!”
桑柔命悬一线,他就在离她不远处,却无法脱身赶去救她,这种情况换作谁都会被逼疯。
长鱼酒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他感觉自己的神智正处于一种混沌不清的状态,就好像一张琴上紧绷的琴弦,随时都可能会断裂。
“我明白了!”云樗幡然醒悟般地大喊道,“他早就料到祭典上会来这么一出,才故意把我们锁在这儿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他绝望地大叫道,“我们现在根本就出不去啊!啊,曲生,曲生你怎么了?说话啊!”
长鱼酒的双眸已完全变成了妖艳的血红色,他的气息因为焦灼和恐惧剧烈地起伏着,一双妖异的重瞳陡然暴射出精光。
这一刻,云樗清晰而惊恐地意识到,琴弦断了。那股神秘的宗师之力已完全地、彻底地占据了长鱼酒的心神,他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已被宗师的力量充斥,现在的他,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长鱼酒。
“曲,曲生?”云樗试探性地唤了了一声。
长鱼酒没有反应。
云樗又叫了一声:“俱酒。”
长鱼酒依旧没有反应。
云樗冷不丁地疾退两步。狱中寂静如死,唯有他自己怦怦的心跳声在这座空间回响。
霎时间,只听得“轰”的一声惊天巨响,缠绕在长鱼酒身上的道道锁链出现了裂痕。只见长鱼酒奋袖出臂,怒目圆睁,猛然发力一挣。
“咔擦咔擦!”
束缚在他身上的锁链尽数断裂而去,旋即迅速从他身上剥落,断去的铁链就好像条条死去的小蛇,悄无声息地躺在地上。
“曲生!曲生!”云樗卯足了劲大声叫喊,试图唤醒他的意识。但琴弦已经断了,长鱼酒的意识当然也不可能再被唤回来了。
刹那间,一股狂暴的能量陡然自长鱼酒体内流泻而出,能量之强悍有毁天灭地之势,好似狂风巨浪风卷残云,天地风雨突变,日月星辰无光,狂暴的能量席卷整座空间。
只听得“轰”的一声,坚固的牢房墙面硬生生被冲开一个大窟窿,阴冷的风瞬间灌入,在黑暗中发出“呜呜”幽咽声。大片苍凉旷野和混乱不堪的祭典场面在眼前平铺开来,仿佛一幅华丽激昂的春秋画卷,又似一首热烈悲壮的战国颂歌。
缠绕在云樗身上的铁链被能量余波挣断,云樗揉了揉酸疼的手腕,舒活了一下筋骨,召出香草护身,盘腿坐地调养内息。
长鱼酒虚弱地瘫坐在地上,脸色苍白难看,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大劫,劫后余生,整个人都好似被抽空了一般虚弱。
“轰隆隆——”
在他们身后,关押他们的大牢陡然塌陷下去,砖块瓦砾满天乱飞,乌烟弥漫之中不时传来狱卒和犯人的惊惶叫喊声。
云樗为自己调完内息,又忙将真气灌入长鱼酒体内。长鱼酒接收到源源不断的充盈补给,面色这才稍稍红润了些。他虚弱地倚靠在云樗身上,一双眼睛死死盯着不远处一片混乱的祭场。
“曲生,曲生,你听得见我说话吗?”云樗轻声问道。
长鱼酒没有说话。
云樗的心陡然沉了下去,沉到了深深的谷底。
“你现在很虚弱,千万不要随便动弹!”他明知道长鱼酒不会理会自己,但依然尝试着跟他说一些话。云樗不确定长鱼酒现在是否听得见,或者是否听得进他的话。
长鱼酒似乎真的将云樗的话听进去了。他乖乖地倚靠在云樗身上,剧烈地喘着气,神色疲惫。
云樗意识到自己所处境况的危险程度,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当”地一声,桑柔挥舞冰刃,将袭来的冷箭尽数打落,密密麻麻的流矢铺天盖地射向祭坛,一时间呼啸声破风声不断,地面上插满了箭镞,鲜艳的血珠顺着箭头流淌而下,染红枯草。
弓箭手的攻势太过迅猛,吴起的部下很快支撑不住,一个接一个地中箭倒下,尸身铺满祭坛,鲜血流淌一地。
糟糕!
桑柔心下暗道不妙。气聚而成的冰刃舞动如风,截断一根又一根箭,她咬紧牙关奋力抵抗,且战且退,伺机突围。
“噌!”
吴起的利剑准确而狠戾地刺入卫兵的心脏。他毫不犹豫地拔剑,回身又砍在另一名卫兵肩上。卫兵发出一声凄楚惨叫,捂着血流如注的肩膀倒了下去。
包围圈迅速出现一个缺口,吴起冷哼一声,足尖点地飞身跃起,一手挥剑抵挡漫天流矢,另一手变拳成爪,抓向祭坛上的桑柔。
桑柔已然将舞刀的速度发挥到了极致,尽管她已渐渐体力不支,但神智依旧无比清醒。她一个劲地朝吴起摇头。
不要管我!
她看向吴起的眼神里充满了焦虑和乞求。
吴起淡淡地瞥了她一眼,手上的动作未曾因这眼神有半分动摇。他从来不会为任何人做出改变,以往是这样,现在依旧是这副老样子。
我曾信誓旦旦地答应过他,要保你此次安全无虞。这事端既是由我挑起的,我自然不能放手不管。我既已许下诺言,当然更不能食言。
“快阻止他!”屈宜臼双眼赤红地勒令弓箭手,“快!把她射下来!”
“糟糕!桑柔有危险!”云樗惊叫道。
“曲生,我们现在怎么办……”他明知道长鱼酒已经不会理睬他,但他此刻真的好无助,多么希望有个人能来为他指明道路。
“曲生,曲生?”当云樗转过头时,才发现长鱼酒已经不见了踪影,他原先坐着调养内息的地方,此刻只余荒草一片。
糟糕!云樗心下陡然一惊。
在那一刹那,吴起已经冲开层层箭雨掠上了祭坛。
“拦住他!”
屈宜臼急得暴跳如雷。他一把夺下卫兵手中的弓箭,搭弓上弦,准备亲自射箭,然而有个人动作比他更快。
“呼——”
一袭黑袍乘着风从他头顶划滑过,宽大的黑袍遮天蔽日,俨然一只巨大的蝙蝠张开翅膀飞过。就在那一刹那,申不害手中的弓已张成满月。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转眼间,吴起已经抓住了是桑柔的衣袖。
“嗖——”
锋利的箭矢化作一道流光,闪电般向祭坛暴射而去。箭镞上被申不害灌输了磅礴浩瀚的内力,比起寻常箭矢竟是快上不少。
“小心!”云樗不顾一切地大声喊道。
申不害的嘴角在黑袍下悄悄勾起冷厉的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