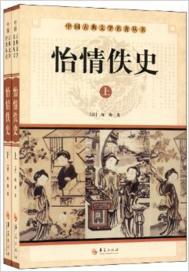胡归一行三人骑马进了一片林子,忽地听到林中隐隐传来叫骂声,登时勒马不前。
柳飞萱道:“这地方阴森森的,左近既无人家,也无行人,怎会有人声?”
胡归打量这林子,绵延十数里,除了眼前这条小道,到处枝蔓横生,荆棘遍布。河南属北方,秋冬时节气候甚是干燥,但这林子却生得葱茏蓊郁,十分的湿润。
胡归心下好奇,说道:“这声音应是从东面林子里传来的,且把马儿拴在这里,过去看看。这一时半会儿应当没有人来。”
胡归与柳飞萱下了马,阿旺不敢进去,不要下马。
胡归说道:“阿旺好好待在这里,胡哥哥与柳姐姐过去瞧瞧就来!”阿旺摇头不许。
柳飞萱骗他道:“阿旺不听话,小鬼就过来捉了你去!”
果然,阿旺听到鬼要捉他,不敢再作声。
胡归吩咐道:“阿旺呆在马上别动!”心想:“便是遇见坏人,以铁象的脚力,一时间也无大碍。”
柳飞萱明白胡归心思,解下辟水寒剑,递给阿旺傍身,笑道:“这便放心了!”说着,向林中走去。
胡归心头一暖,跟了进去,抢在前头,替她拨开荆条。
二人走了一阵,声音越来越响。
只听一人骂道:“他奶奶的,这贼婆娘把咱留在这里,又不送吃的来,想是要活生生地饿死咱们,她自己却不知躲在哪里正大碗喝酒,大口吃肉,逍遥快活。等老子揪住她,定教毒蝎子螫她几口。”
另有一人驳道:“放毒的是老太婆,不是她奶奶,你骂她奶奶,有失偏颇。”
先前一人回道:“我骂的是他奶奶的,又不是当真骂她奶奶!”
后一人说道:“那倒未必,就算你没骂她奶奶,老太婆听见了,也定会觉得你胡老三在骂她奶奶。”
与他辩驳的那胡老三怒道:“胡老三爱骂谁就骂谁,你胡老二再胡搅蛮缠,我连你奶奶也骂…”突然想到胡老二的奶奶也就是自己的奶奶,骂胡老二的奶奶胡老三也跟着吃亏,便住口不骂了。
柳飞萱停下不走,说道:“这些人说话真奇怪!”
胡归已听出说话之人是谁,第一个正是当晚在江边见过的中州三胡的胡说八道胡老三,后一人是胡搅蛮缠胡老二。正欲说话,忽听另一人说道:“小娃娃躲着不出来,我要放蛇了。”说话之人正是胡作非为胡老一。
胡归见已给他们发现,便同柳飞萱拨开树丛,走了出来。
只见许多的毒物正将一棵大榕树围在核心,三胡缩在树上,动也不动。周遭百步以内,没有任何落脚的地方。
胡归看那毒蛇吐信,蟾蜍垂涎,几百只蝎子蜈蚣在地上沙沙蠕动,胸口烦闷,几要呕吐出来。忙将飞萱拉到身后,自己挡住毒物,心想这些毒物当是胡老三口中的那位老太婆所驱使的了。
胡归潜运无极神功,稍作调息,烦闷之感顿消,转头看去,见柳飞萱面不改色,无甚异状,才稍稍放心。
外人面前,胡老一死要面子,装作得意道:“两个小娃娃害怕了吧!”却没认出胡归。
胡归笑道:“三位,那日楼船比赛,是胡老一兄赢了呢?还是胡老二,胡老三兄赢了?”
三人齐声答道:“当然是我赢了!”不再理会胡归,各自争辩起来。
争了一阵,胡老三最先记起胡归,嚷道:“那晚就是你和另外一个小子开走了我们的大船,快赔船来!”
胡老一,胡老二经他提点,顿时都认出胡归来。三人甚爱那三只楼船,当日给胡归盗了去,好不气愤,后来时间长了,才慢慢地忘了。这时记起,停止了吵闹,一致对外,要胡归赔船!
胡老一恐吓道:“敢不赔船,小子,我便叫这些蛇啊,蝎子,蜈蚣什么的,将你先从脚趾头吃起,吃了脚趾头再吃...”
柳飞萱不待胡老一说完,向毒物丛中一踏,走了五六步,那些个毒物竟纷纷避开。柳飞萱说道:“再吃哪里?”
胡归听飞萱说过她幼时服过一枚避毒的药丸,看到群虫躲避,也不奇怪。三胡却惊得张大了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良久,胡老三摸着脑袋说道:“难不成因她是女人便不咬她?”
胡老大点头道:“应是如此,那老太婆不也正是女人。”说着向胡归道:“兀那小子,你也踏一脚试试,看蛇儿咬不咬你!”
胡归暗暗好笑,心道:“三人只管浑说,什么是女人便不咬,专咬男人,天底下又哪有这等奇事。”当下笑道:“自然不咬我,这些毒虫有灵性,专咬有胡子的人。”
三胡你瞧瞧我,我瞧瞧你,但见各人颏下果真有一撮胡须,胡归没有,这姑娘没有,那老太婆自也没有。三人将信将疑,看着胡归。
胡归忍住笑,续道:“这些毒虫既已瞧见了你们的长胡子,即便此刻将它拔去,也是为时晚矣!”
三人点了点头,齐声问道:“那却怎生是好?”
胡归说道:“我倒有一法子,可以救得你们!”
胡老一道:“我们自愿呆在上面,想下去了,自然下去得。”其他二人均点了点头,以示赞同。胡老一续道:“不过我也想听听,天下除了我三兄弟外,谁还有能耐能从这里下去。”
柳飞萱听他三人死要面子,又害怕胡归救下这三人后,惹下麻烦,便道:“胡大哥,既然三位前辈有法子下得来,我们走罢,想来我们留在这里,三位是不会下来的。”
胡归只道她要开三人玩笑,说道:“是。”说着转身便走。
三胡急道:“且慢!”
胡归本就没打算要走,听他叫唤,停了下来,问道:“怎地?”
胡老一摸了摸脑袋,说道:“你且说你的法子,那船,我们不要你赔了。”
胡归说道:“中州三胡,言出如山。说过的话,自不会食言。我若说了法子,三位从此以后便不能找我的麻烦,也不能找我身边人的麻烦!”
三胡被他戴了顶高帽,连连点头,胡老三说道:“那是,我三兄弟说话向来算数!”
胡归见三人已堕彀中,又问道:“三位倘若一不小心,将说过的话忘了呢?”
三人齐道不会。柳飞萱说道:“胡大哥,我看他们三个定是要食言的,你别救他们!”
胡老一怒目而视,气道:“我三兄弟若有食言,那便…那便…”
柳飞萱激道:“那便怎样?”
胡老一道:“那我胡老一便不再是胡老一。”
柳飞萱奇道:“你不是胡老一,遮莫要做胡老二?”
此言一出,胡老二立马抗议道:“他是胡老二,那我是谁?天底下怎能有两个胡老二?不成,不成。”说着,连连摇头。
胡归说道:“如若食言,胡老一仍管叫胡老一,名字无需更改。只不过…”
三胡急道:“那却如何?”
胡归笑了笑,说道:“晚辈胡归,有幸与鼎鼎大名的中州三侠三位前辈同出一源,做了家门。”
三胡给他戴了偌大一顶高帽,连连点头。
胡归续道:“只不过被爹妈晚生得几年,让几位长了一辈去。”
胡老三道:“那也怪你不得,那时你还在你爹妈的肚子里,他们要不让你出来,你也没得法子。”
胡老二一听不对,立马驳道:“胡说八道,你说他在他爹妈肚子里,他爹是大男人,难不成还会生小子?”
胡老三给他一驳,一摸脑袋,说道:“也许是他爹爹和他妈妈各怀一半,生下以后拼成的。谁规定只有女人才能生孩子,再说了,即便是女人,也不一定能生出小子来,就像…”他想了想,朝柳飞萱顺手一指,续道:“像这女娃娃,年纪小了就生不出。”
柳飞萱给他一说,羞得满脸通红,欲待骂来。只听胡老二驳道:“年纪小了生不出,难不成年纪大的就生得出?我看适才那个老贼婆,她就不一定生得出。”
胡老三摇头道:“非也,不一定便是不能肯定,既然不能肯定或许就有可能。待老贼婆回来,你且问问她能不能生小子。”
胡归见他二人越说越离谱,便抢在胡老二的头里说道:“三位是前辈高人,倘若食言,那便连我这后生小子也不如了,是也不是?”
胡老一道:“你也说是倘若,那便是不会的了。”
柳飞萱早已听得不耐,听他们罗唣不休,怒道:“这三个蠢货只管啰唣不休,胡大哥,让他们给蛇吃了便了。”果然这时有几只蜈蚣蝎子顺着树干爬了上去。三胡大急,六掌齐挥,将一干毒物逼了下去。
胡归虽有心戏弄三人,但终究是生死大事,又放心不下阿旺,不敢再延宕,说道:“三位若食言而肥,不如我这后生小子。那我当排在三位前面,这一字前头嘛,当是一个大字。”
这次三胡脑子倒甚为灵光,齐道:“胡老大?”
胡归点了点头。
三胡正犹豫不决,忽地听到林子深处有人骂道:“哪里来的野小子,胆敢来坏老身好事,三条蠢物若被放走一根汗毛,老身立时叫你葬身蛇腹!”
三胡大骂老贼婆,老妖怪,丑八怪,她奶奶的。
胡归听得老妇恫吓,傲气陡升,决意要放走三胡。估模老妪离得尚远,从身旁拾起大段枯木,说道:“待我抛出木头,你们在空中借力跃出。胡老一兄先!”说完,木头已经掷出。
胡归万没料到,这三个怪物此时仍要争个你先我后。居然同时跃起,踩上了那根木头。胡老一,胡老三踩到边上,差点喂蛇。好在三人武功甚高,临危不惧,胡老三和胡老一单脚一搭,分别向左右飞出,两股劲力互抵,木头倒更加稳当了,三人稳稳当当落在地上。木头落地,众毒物一涌而上。
三人刚落地,一个面貌丑陋,又干又瘦的老妪已到了跟前。胡归心想:“丑八怪云云,倒也骂得不错。”
老妪喝道:“哪里来的毛头小子,敢来搅和老太婆的事。”
胡归心中忿怒,但想人家终归是武林前辈,不敢失了礼节,便抱拳道:“晚辈与…与舍妹不小心闯进了林子,正寻出路,听得三位在树上大喊大叫,好奇心起,循声到了这里。不知是前辈所在,多有冒犯!”
柳飞萱听他叫自己妹子,顿时会意,说道:对啊,晚辈与哥哥冒失之处,还请见谅!
老妪冷哼一声,说道:“你们成心放走三个蠢物,当老太婆真的耳聋目昏了吗?”
胡归无话可说。
三胡一脱束缚,立时叫骂起来。胡老一道:“是哪三个蠢物?”
胡老二回道:“她方才说放走三个蠢物。自不是我兄弟了。”
胡老三接道:“是啊,试问天下有谁能困得住我三兄弟,就算困住了,也必然使了阴谋诡计,作不得数。既然困不住,也就没得放走这一说了。”
胡老二故意问道:“既然不是我们三人,老太婆分明说放走三个蠢物,眼下除了咱们却还有何人?”
胡老一看了看胡归三人,掰出三个手指头,数道:“一,二,三,这不是!”
胡归心下既好气又好笑,心想这三人当真无赖到了极点。我若开口,给他们抓住话头,三人蛮不讲理,我可说不过。当下忍住不说。
那老妪气得发抖,恼怒已极,喝道:“三条蠢物气煞人也,老身今日要叫你们葬身蛇腹,尸骨无存!”说着,挥掌向胡老三劈去,脚下的蛇蝎随之涌上。
原来三胡经过树林时,听得林中窸窣声响,三人好奇,便拨开树丛,前去探究,恰巧遇见老妪在训练毒物。老人容貌丑陋,胡老三口无遮拦,嚷嚷道:“这老太婆丑得紧,吓死胡老三了。”祸由此出。
胡老三惧怕她脚下的毒物,闪身避开。老妪一掌劈空,又向胡老二引去,胡老一,胡老二尽皆避开。老妇人身手矫健,但三胡却更为迅捷,左躲右闪,几招下来,连半片衣襟也没被她碰到。老妪业已知道今天奈何不了这三个疯子,但心有不甘,不愿罢手。好在三胡知她毒物厉害,不敢久斗。生怕被毒蛇缠上或被蝎子螫一口,立时便有性命之虞,就是被蟾蜍喷上一点唾沫星子,也是老大一件麻烦事。
胡老二边打边说道:“我三兄弟生平从不和女人打架,今日和你动手,已是大大的不妙。传将出去,于我三人声名不好。”
胡老三接口道:“不光有损三胡威名,便连老太婆的名声也要糟糕透了!”
柳飞萱听他说生平从不和女人打架,已觉好笑,又说还会损及老妪名声,不禁问道:“怎地连老婆婆的名声也要糟糕透了?”
胡老三道:“你们想,我三兄弟只要有一个与她动手,岂有不赢之理?赢了老太婆,老太婆的名声岂不是要糟糕透了?”他一边说话,一边闪身躲避,不让群蛇圈住,动作丝毫不缓。
三胡边打边退,忽地齐声发喊:“好男不和女斗,老胡去也!”话未落音,三人已钻出林子不见了。胡归,柳飞萱相顾一笑。
老妇瞧在眼里,怒火大炙,喝道:“你成心与老身为难,放走他们三个,那就怨不得旁人,只怪自己太多管闲事了!”说话间,窸窣之声大作,群毒迅速向胡归包围过来。
柳飞萱挡在胡归前面,说道:“木头是我扔的,与胡大哥无关,你叫那些畜生来咬我。”胡归知她不惧蛇蝎,也不阻拦。
老妪还不知柳飞萱不惧毒物,冷笑道:“胡大哥,兄妹有这般叫的吗?”柳飞萱一时情急,竟尔忘记了谎称兄妹之事。
老妪又道:“看不出你倒是颗痴情种子,为了他竟不惜自己性命。”
柳飞萱被说得满脸通红。
胡归道:“我与他刚刚认识,什么痴情不痴情的,说得好不难听!”
老妪一愣,念道:“刚刚认识…”忽地朝柳飞萱说道:“刚刚认识你就甘愿为他舍了性命不要?”
柳飞萱点了点头,说道:“一人做事一人当。”说着,一脚踏入蛇丛,叫她再没回旋的余地。只见柳飞萱落脚之处,蝎子,花蛇,蟾蜍纷纷躲避。
胡归看老妇脸色越来越不对,心知不好。果然,只听老妪咬牙问道:“老毒物与你有何干系?胆敢隐瞒,老身立马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柳飞萱想了想,问道:“老毒物是谁?”
老妪怒极反笑,说道:“你不惧我毒物,不是服食过老毒物的百草辟毒丹?”她不笑倒还好,这一笑,更添了几分阴森之气。
柳飞萱身子一颤,说道:“没有,我所以不怕你的毒虫,是因为幼时爹爹给我服过仙药。”
老妪喝道:“你爹爹是谁?”
柳飞萱正待要说,胡归抢道:“我不知道前辈与那老毒物有何仇怨,但柳姑娘适才已经说过与她无关。前辈把一腔怨气发泄在晚辈身上,可冤枉的紧!”
不料老妪连呼三声“我有什么怨气!”接着便向胡归抓来。
胡归展开天外飞星,使出颠倒步,不退反进,从老妪的胁下滑了过去。
老妪惊咦一声,又惊又喜,问道:“好小子,这步法你从何处学来的?”
胡归只道她赞叹自己步法精妙,也不理会,将颠倒步使完,又使了一路倒行逆施,老妪挨他不着。胡归远远地退开。
老妪又问道:“这步子谁教你的?”
胡归心想:“你这么心急知道,我偏不告诉你。”于是说道:“偷学的,没学到家,叫前辈笑话了。”
老妪道:“偷学,这等高深的步法,偷学二字谈何容易?”
胡归道:“所以晚辈说没学到家,只偷到了这两式。”胡归看她好似信了,不禁暗暗好笑。
老妪怒道:“偷学什么不好,偏偏要偷学这天外飞星,本来有心饶你一命,现在别怪老身心狠手辣了。”
胡归暗自戒备。不料老妪一掌拍出后,不再纠缠胡归,径向柳飞萱抓去。事出突然,柳飞萱竟尔忘了格挡。眼见老妪右爪从她肩头抓落。
只听得“喀拉”一声响,老妪连退数步,右手垂在胸前,神情极是痛苦。
胡归挡在柳飞萱身前,歉然道:“得罪了…”话未落音,只觉脚下一阵剧痛,低头一看,却是一只蝎子螫了自己一下。
原来老妪突然发难,胡归离得虽远,但凭着天外飞星,还是抢到了柳飞萱身前,用铁臂格开了老妪的一抓,只是力道拿捏不准,折断了老妪的手骨。胡归分神说话,脚上便给蝎子螫了一下。
胡归当机立断,拉着柳飞萱朝林外奔去。
那老妇也不追赶,冷笑道:“那蝎子喂了我的剧毒,没有解药,半个时辰便会化脓而死…”
胡归和柳飞萱没命价的狂奔,不多时便逃到了小路上。
两人来到原地,却不见了阿旺踪影,连铁象也不见了。胡归急得大叫,登时毒气上涌,昏迷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胡归悠悠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块大石上,有溪水从脚边淌过。
这是一片火红的枫树林,叶子在树上燃烧。金色的夕阳洒在地上,泻在溪流里,几乎耀得胡归睁不开眼睛。柳飞萱安静地伏在石上,似已熟睡。
胡归觉得喉间一股腥膻,一抹嘴,掌上一片殷红。他心念电转,搂起柳飞萱,但见她雪白的肌肤上,右腕一道血痕尤为扎眼,腕上的血液已经凝结。胡归登时明白,自己中了老妇的蝎毒,本已无可救治,是柳飞萱割破腕脉,用药血救了自己。心下感激,将她搂紧了。
胡归心生澎湃,心想自己与柳飞萱认识不久,蒙她在树林里舍身相救,如今又不惜耗费自身精血来活己性命,这番恩情,真不知道要怎生报答。又想自徐伯去世以来,自己先后遇到了花叶,石无德两位前辈,花叶神僧于己有赠佛之德,自己能习得金佛身上的《无极真经》,完全拜他所赐。石无德于己有救命之恩,更是将一套“天外飞星”倾囊相授。尔后遇见王中孚,蒙他多番照顾,两人意气相投,结为了异性兄弟。后来反出军营,又为阿旺的爹爹舍命相救。念及至此,心底生出阵阵暖意,低头看了看柳飞萱。转即想到阿旺,心情又复低落。心中当真五味杂陈,诸般滋味都有。想着想着,自己也睡着了。
在金色的夕阳里,火红的枫叶被秋风吹落,一片一片落在溪流里,随流漂远,还有一些落在了二人身上。
过了许久,柳飞萱只觉身子所依处甚为柔软,有男子气息迎面扑来。睁开眼,却是躺在胡归怀中,不禁一阵娇羞,身子不由地蠕动了下。
胡归惊觉,天已大放曙光,想到眼前的少女在自己怀中躺了一夜,也觉得难为情。看到柳飞萱脸色煞白,气色不佳,显是昨日失血过多。不禁说道:“姑娘不惜损伤自己,以药血活胡归性命,真是...”
柳飞萱点了点头,打断他道:“胡大哥,我没事,你也救过我。”说着,挣扎着要坐起,胡归帮忙搀扶。
柳飞萱看了一眼胡归神色,问道:“胡大哥在担心阿旺?”
胡归点了点头,说道:“阿旺他爹爹临终前把他托付给我,我若不能好好照顾他,怎对得起李大叔的在天之灵。”胡归顿了一顿,说道:“柳姑娘,你身子虚弱,且在这里休息,我寻着了阿旺再来会你!”
柳飞萱笑道:“在家里爹爹管我叫萱儿,此外一干人对我虽好,却只是小姐小姐地叫得腻煞人。胡大哥若不嫌弃,叫我萱儿便了。”
胡归见她情真意切,心下极为感动,轻轻唤了声:“萱儿。”
柳飞萱点头应了,苍白的脸上泛起一阵潮红,说道:“胡大哥无需担心,我那铁象生俱灵性,不管离多远都能寻到主人,萱儿肯定,阿旺过不多久便会和马儿一起回来的。”
胡归叹道:“我所担心的是铁象受了羁绊,难以脱缰。”
柳飞萱神色顿黯,说道:“胡大哥疑心是那三个丑八怪?”
胡归点头道:“正是,除了三胡,我着实想不到是何人所为。铁象若不是被扣住了,阿旺不会引缰,不受他的控制,按理说早已经自行回到你的身边。”
柳飞萱安慰胡归道:“我瞧那三个丑八怪虽然行事古怪,倒也不是奸恶之人,阿旺若真的在他们手里,反倒不碍事。”
胡归心中也是这般想,不然他又怎能在此停留一夜,当下说道:“即便如此,他三人疯疯癫癫,迟则生变,你失血过多,不宜奔波行走,且在这里等着,我找到阿旺便来接你。”
柳飞萱道:“没有萱儿,胡大哥找不到铁象。我的身子不要紧,将息了一夜,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柳飞萱看他犹豫不决,也不说话,往西就走。胡归摇了摇头,快步跟了上去。
二人走不多远,柳飞萱停下脚步道:“胡大哥,你看,这是铁象留下的。”胡归走近观看,只见地上有三四个小坑。
柳飞萱又道:“这是铁象用蹄子刨出来的。”
胡归心想:“铁象马果然名不虚传,居然有这等灵性。”
二人继续往前,隔不多远便会有蹄坑,抑或有被马尿淋焦的枯草,还有马粪。铁象一路留下记号,胡归心下顿时轻松了许多,就是遇上岔道,也无大碍。
渐渐日升中天,已是午时了。
胡归道:“我体内的蝎毒还未完全清去,走了这许久,有些累了。有铁象的指引,迟早能追上他们,不如在此歇歇脚力,再行赶路。”
柳飞萱心下明白:“他是担心我身子虚弱经受不住,借口余毒未清停下休息。”不忍拂胡归心意,便坐在路旁休息。
歇了一阵,二人出了林子,来到官道上。忽听后头有人远远地喊道:“把合着吾…把合着吾…”一声刚落,另一声又起,声势壮大。过不多久,一队镖车缓缓走来,车上插着一杆镖旗,金黄的旗子上绣着一幅虎啸山林图,虎图上头有个“许”字。
镖车来到近前,当先的镖头向胡归二人抱了抱拳,说道:“朋友好走!”
胡归抱拳还礼,也道:“好走!”看镖车向西去得远了。胡归向柳飞萱道:“萱儿,这些倒不像正经押镖的。”
柳飞萱奇道:“怎么了?”
胡归说道:“适才他们打我们面前经过,除了那许姓的镖头,余下的都没注意咱们,只管低头走路。你想,若是押了镖,哪有不细心提防之理。”胡归又指着地上的辙迹道:“那几个大木箱装上东西每一个少说也有三四百斤重,你看地上的车印。”
柳飞萱一看,果然痕迹甚浅,不似装有重物。柳飞萱道:“看样子,他们是打山东过来的,千里迢迢押着几个空箱子,大有蹊跷!”
胡归道:“我倒不想去想有何蹊跷,只是他们的去处让人担心。”
柳飞萱瞧镖车的去处正是铁象马指引的方向,便道:“那我们走快点!”
胡归点了点头,不多久便追过镖车,走在了前头。胡归见柳飞萱气色不好,行一阵子便借口休息。
一路上,断断续续遇到不少人,或独骑,或三两个一起,也有成帮成派的。胡归再也忍不住,向一人打听才知道是赶着去参加九月初九嵩山武林大会的。胡归登时明白,原来那姓许的镖头也是往嵩山去的。
“前面不远有个小镇,大伙儿吃饱了再走!”一队人马打旁边经过,当先的一个汉子叫道。
胡归和柳飞萱正饿得慌,心下均是一喜,加快了脚步。果然行了两三里路便有一个小镇。小镇虽小,客栈、饭店、布庄、赌场、当铺等一应俱全,数量还不少。二人走进一家饭店,找个座位坐了,随意点了些菜,胡归特为柳飞萱要了个补血的冰糖莲藕。
胡归放眼瞧去,在座的几乎都是武林中人。
只听得西首一条汉子说道:“此次少林聚会,听说是要联盟抗金,既要联盟,须得有一位武林盟主才行,也不知这盟主的名头,最后会花落谁家?”
另一人摇头说道:“很难说,除了钱帮主,少林方丈慧空神僧,中州大侠云前辈,十六路镖局总把子王老前辈等人都是很有机会的。”
这人说完,旁边桌上一人笑道:“扬州二怪屁大点见识,那云震与少林寺新结了仇,怎会上嵩山去!”
先前说话的扬州二怪瞧那人商人打扮,桌角放着个铁算盘。大怪葛关长施礼道:“是朱前辈,失礼了。敢问云霞山庄和少林寺怎生结了仇?”
铁算盘朱铁英道:“前阵子我听朋友说,慧空神僧的师叔花叶前辈给云霞山庄害死了。”
众人一片惊咦。胡归听到花叶前辈四字,身子一颤,凝神细听。只听葛关长又问道:“花叶神僧是少林寺老一辈的先宿高人,武功深不可测自不必说,再有少林这个后盾,云霞山庄怎敢加害于他?”
要知道云霞山庄虽然在江湖上声势煊赫,比之少林却大有不如。众人均点头应和,要听朱铁英的下文。
朱铁英道:“我只听说花叶神僧受伤在先,被云震的几个弟子下手在后,具体事节嘛,我也不太清楚。”
朱铁英说完,顿时炸开了锅。
有人道:“云霞山庄此举有违光明磊落,和一些江湖宵小有何分别?”这人说到后面声音越说越小,想来是害怕得罪云霞山庄。
又有人道:“云霞山庄竟不惜和少林结怨,也不知所为何来!”说话的是扬州二怪中的葛关礼。
也有人问道:“打伤花叶神僧的是什么人?”
胡归想道:“花叶前辈临死前说过伤他的是九个和尚,却不知道是什么人?”
有人答道:“多半是江湖传言要大闹少林的九个天竺僧。”
九个番僧要大闹少林,许多人业已听闻,当下纷纷点头,以示同意。
葛关礼怒道:“以多欺少,花叶神僧便有再大的神通,终究抵敌不过。放眼当今天下,除了天下第一大帮丐帮,还真想不到有哪个帮派能和少林一较高下的。九个和尚敢再上少林闹事,那不是自寻死路?”
便在这时,门外几个黑衣汉子拥着一个白衣男子和一个花衣男子走了进来,白衣男子冷笑道:“鼠目寸光,丐帮和少林算又什么东西?也敢拿来大吹法螺,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群雄大是不忿,朝他们怒目而视。见他们衣着打扮与中土不同,不明底细,谁也不欲第一个出头。
来人分两桌坐下。
扬州二怪的葛关礼性子最急,怒道:“哪里来的狂徒,连少林和丐帮也不放在眼里!”
白衣男子不理他,向花衣男子道:“有人眼睛不好,在打听咱们的名头,师弟,你说怎么办?”
花衣男子阴声阴气道:“那得给他治治,叫他睁眼看看清楚!”
葛关礼大怒,骂道:“贼子休要猖狂,且让葛爷来给你们长长见识。”说着,长剑出鞘,向花衣男子削去。花衣男子低头避过,同时长袖拂出。葛关礼待要回削,倏地抛下长剑,滚到在地,捂住了眼睛,有血从指缝里流出来。葛关礼大叫:“是雪山老怪,是雪山老怪…”抖了几下,便不动了。
此语一出,众人无不骇然,纷纷避开。
雪山派是有名的西域毒派。
花衣男子阴恻恻地道:“雪山派从来不说空话,现在你的眼睛治好了,不过还没瞧得清楚,我二人只是老仙的徒弟。”
葛关长折了兄弟,更不打话,长剑已然出手,只是远攻,生怕也遭了二人的毒手。二人被他逼得左躲右闪,极为狼狈,白衣男子手臂中了一剑。葛关长信心大增,心想这二人除了毒功厉害,武功却是平平。手上长剑抖得更快,许多人大声喝彩。
胡归瞧那二人躲避之时,双手仍在不停地挥舞,突然明白过来,朝葛关长喊道:“空气中有毒!”
葛关长经胡归提醒,忙地屏住呼吸,但为时已晚,已经吸入了不少毒粉,只见他脸现黑气,身子一僵,昏倒在地。
胡归喝道:“住手!”身形一晃,掀起一张桌子朝二人砸去,二人躲避不及,给砸个正着。躺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众黑衣弟子手忙脚乱地将他二人扶起。
花衣男子拍拍衣服,望着胡归,见他好端端站着没倒,不禁奇道:“你中了我的毒,怎地还不倒?”
胡归当即明白过来,这二人周身是毒,这张桌子被他们坐过,自也成了一件厉害的毒物。胡归心道:“他二人不知我喝过萱儿的药血,不惧邪毒。我且挤兑几句,杀杀他们的威风。”便说道:“区区微末伎俩,也敢拿来中原炫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花衣男子大怒,一声喝令,七八个人朝胡归一拥而上。胡归施展天外飞星避开。他的拳脚功夫也很平庸,但瞧出这些人的功夫也很一般,自己又不惧毒药,倒不害怕。心想你们使毒害人,贻害不浅,今日碰在我手里,须叫你们吃些苦头。胡归仗着臂膀戴有铁套,便胡乱舞了起来。他步法精妙,汉子们使出浑身解数,也抓不住他,跑又跑不过,一时间,一个个给他打得鼻青脸肿,手断骨折。众人无不喝彩,朱铁英见多识广,见这个少年使出白莲教庞天王的天外飞星,心下更是纳罕。
柳飞萱道:“胡大哥,你还记得放蝎子咬伤你的那个老太婆吗,她好像和雪山老怪有些关系,正好捉个人来问问。”
胡归经她提醒,身子一晃欺到白衣男子身前,揪住了他的衣领,问道:“有个使毒的老太婆与老怪是何关系?”
白衣男子摇了摇头,一连价地说不知道。胡归心想:“我也问得颇没脑子,天下使毒的老太婆何止一二,没名没姓的从何问起?”
胡归担心这干人留在这里,毒气会越聚越多,反生祸害,便喝道:“解药拿来!”
花衣男子掏出一个白色瓷瓶,倒出一粒猩红的药丸。柳飞萱伸手接过,给葛关长服了。葛关长服下解药,脸上的黑气立时褪尽。
胡归把白衣男子往门外重重一丢,喝道:“日后自有找你们报仇之人,去罢!”余下的人将白衣男子扶起,灰溜溜地走了。
众人不敢再留,一一出门去了。临走时朱铁英问道:“小兄弟适才使的步法精妙的很,不知师承是谁?”
胡归见适才扬州二怪对他甚是恭谨,心想此人在武林中地位不低,不敢怠慢,说道:“教晚辈步法的是位前辈高人,至于姓名,个中有诸多不便之处,还请朱前辈见谅。”
朱铁英笑道:“不妨!”便出门去了。
胡归见葛关长仍躺在地上,将他救醒。葛关长纳头便拜,胡归忙将他扶住,说道:“先生既无大碍,在下还有要事在身,先在一步。”
葛关长问道:“恩公此行是要去少林寺?”
胡归答道:“我是来寻一个朋友的,他骑一匹大黑马,恩,对了,旁边应当还有三个矮老头。”
葛关长一拍大腿,说道:“恩公来得晚了,我与舍弟…”看到葛关礼已被害死,不禁一阵伤心,续道:“我与舍弟在这里停留了好一阵,便在不久前,有一匹大黑马驮着一个小童和三个老头打这经过。说也奇怪,那三个老头却是叠罗汉般叠在一起的,叠得很高,进门吃饭时,又不愿下马,说怕给它跑了。结果最上面一人被门框撞了胸口,大声骂道‘胡老二,胡老一你们没长眼睛吗?’下面两人回道‘谁叫你坐上面,自己撞上的,休要赖人。’最上一人道‘要不是让你们先坐了上面,这会儿怎会轮到我胡老三,既然轮不到胡老三,胡老三也就不会撞上。’中间一人道‘适才是谁在上面说风景很好来着?’三人堵在店门口争辩不休。”
柳飞萱抿嘴浅笑,胡归不愿听他唠叨三胡的疯言疯语,问道:“后来呢?”
葛关长道:“后来来了一个贵族打扮的小少年,少年后面跟了一大群人,少年夸黑马是罕见的良马,要买下来。”
他说到这里,柳飞萱道:“他倒识货!”
葛关长接着道:“那少年出到一万两银子,三个老头死活不肯,嘿,一万银子可不是个小数目。少年手底下的人见好买不成,便要硬夺。”胡归和柳飞萱“啊”地一声叫了出来。
葛关长说道:“那三个老头也着实了得,嬉笑怒骂间,一个打十几个。后来一个赤膊汉子射了一箭,被那什么胡老二一手拨开,胡老二却也甩着手掌哇哇大叫,想是那一箭的力道不小。少年见夺马不成,便吆喝手下人撤退。哪知三个老头打得兴起,不愿罢手。胡老二嚷着要赤膊汉子再放一箭,也跟着去了。”
胡归听到这里,问道:“马上的那个小童呢?”
葛关长摇了摇头,说道:“不曾留神,那孩子和马,却不知几时不见了。”
胡归问道:“可是被那少年抓走了?”
葛关长摇头道:“不会,那一干人被三个老头缠得紧,没有空闲去捉人。”
胡归顿时放下心来,柳飞萱亦道:“这下放心了,我们只管在这等,阿旺过不多久便会回来的。”
三人重整杯盘,饮食过后,葛关长要带弟弟回扬州安葬,三人分手道别。
胡归又等了一会,果听见马蹄声响,铁象驮着阿旺回来了。
阿旺一见胡归,便大哭起来,说道:“我听胡哥哥的话,呆在马上不动!”二人好生安慰了一番。
三人九月初八到了登封境内,在一个镇上歇息了。
柳飞萱那日失血过多,又连日奔波劳累,身子有些不适。胡归便也打消了上山看热闹的念头。柳飞萱让他和阿旺去,胡归却是不肯。飞萱便偷偷地教唆阿旺,阿旺吵着要去,胡归没有办法,只得带着阿旺,翌日清早投嵩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