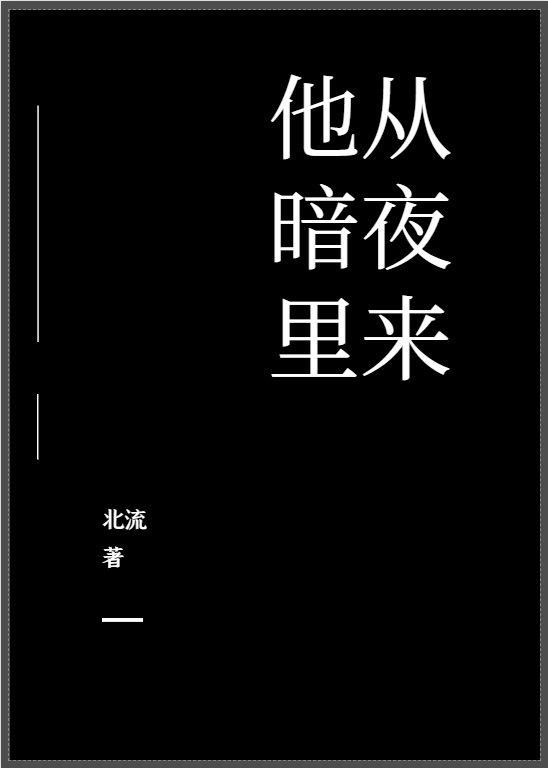脚下是昨天的打斗现场!骇人的念头在脑袋里一闪,禁不住后退几步。
天越来越黑,离最近的住户还有两里路,心桐又气又急又怕。
下午出门时,她忘记换鞋,高跟鞋钉打地面,发出清脆叮咚声,回荡在寂静的湖畔,格外刺耳,也格外疹人。
怕!好怕!
她被自己的脚步声怔住,脱下鞋,想一想,又退下祙子,赤脚小跑。
寒冬腊月,冰冻三尺,刚走几步,她一双柔嫩小脚冻得生痛不说,还被地上零散碎石和砂砾刺得鲜血淋淋。
她找一块干净地方,从口袋里掏出两张餐巾纸,轻轻地擦拭脚上的砂砾和血迹,又重新把鞋祙穿上。
再下地一走,双脚痛得无法落地。
两位大婶找到她,她就那么狼狈不堪地坐在冰凉入骨的石头上,六神无主。
两位大婶像找回了失踪的孩子,惊喜不已。一位大婶姓屈,很胖,块头大,穿棉衣走路,都能感觉身上赘肉一颠一颠,向外张扬。一位大婶姓夏,眼睛大,笑起来亮闪闪,让人忽视了眼角密集的鱼尾纹。
“看到同事了吗?”夏大婶问。
“看到了。”她说,幸好夜幕遮掩住她的沮丧。
“这里阴气重,不能待很晚。”屈大婶说,“心桐,我们回去吃饭。”
善良的屈大婶为心桐准备丰盛的一桌,吃饭时,不停地往她碗里夹菜,饭后,亲切地使唤她做一点家务小事,让女孩子感觉如同回到家里,没有丝毫拘谨。
晚上,屈大婶留她在家过夜。她心情不好,无心清扫家里厚厚的灰尘,便爽快答应。她睡在屈大婶小女儿房间,小女儿跟大婶和叔叔挤在一张床上。
房间宽敞,收拾得干干净净,被子是屈大婶新换的,洁净,散发着淡淡的阳光味。
屈大婶进来,希望心桐在她家里过年。
虽然心桐非常想这样,但没敢答应。
林英婆家在外地,因为工作,五年没有陪老公回去过年,这一次婆婆开口了。不巧,这一年三十小夜班又轮到她,于是心桐自告奋勇地替她值班,为她解决难题。
大夜班她要替汪琪虹上,另外又答应替另一个护士值中班,而白班是她自己的班次,这样从大年三十早晨八时一直到来年正月初一八点的二十四小时,她将在病房里度过。
听完心桐解释,屈大婶说一声傻孩子,不再强留她。
晚上,她翻来覆去,难以入睡。一会儿满脑子水云,一会儿满脑子高明阳,一会儿涌现一片黑沉沉湖水,一会儿又是夕阳乐园后墙阴森森路面和路面上离奇消失的王术宏……理来理去,没有头绪。
担心上班迟到,第二天,她五点半就起床,悄悄地梳冼,准备好一切,去辞行时,发现屈大婶在厨房忙活。看到她,高兴地说饭已经准备好了。
“我知道你早上八点上班,所以起早一点,不然来不及。”大婶说。
心桐感激地望着她,眼睛不自觉地湿润。
冬天的早晨睡得香沉,心桐吃完饭已经六点多,天地还是朦胧一片。
“心桐,东西捡清了吗?”大婶拎起一个大包,问她。
“清了。这是什么?”
“腊肉腊鱼,和一些土产品,带去偿偿。”大婶说。
“大婶——”又吃又带,心桐过意不去,“不带吧,你家人多,我一个人吃不了什么。“
“吃不下,就分给同事吃,过年回家一趟,总不能空手回去,别人知道会笑你。”大婶说,“今年我家腊东西腌得多。”
“谢谢大婶!”她不再推辞。
天渐渐放亮,遍地上霜花如雪,毛茸茸,白花花,覆盖万物。
心桐坚决不让屈大婶送她,两个人争执一会儿,大婶主动放弃,嘱咐一路小心。
外面真冷,呼出去一缕热气,吸进来的却是刺骨的寒风。心桐身躯在冷空气里颤抖,拎包裹的左手冻得生痛,脚尖不停活动,亦感觉不出丝毫暖意。
牛山岭镇车站坐落在风口,心想一会儿站在那里等车,该有多冷?怎么办呢?心桐被寒冷包围,不由自主地为等车苦恼,越走越快,希望能赶上头班车。听屈大婶说,头班车是六时三十分。
“回去吗?”
突然一辆来自同一方向的黑色小车驰过来,稳稳地停在她身边,从车窗里伸出一张俊美的笑脸。
心桐浑身一颤,怔怔地望着对方吃惊。
“冻傻了。”张骋伟又是一笑。
她甩甩头,揉揉眼,再定睛一看,真是那人,不禁一喜。
“不回去!”她赌气,精神却倍增,昂首阔步。
“昨天晚上吓傻了?”他昨天在牛山岭镇待了一天,听周分秋说她回家,便想去找她,结果她竟然上窜下跳的竟然为了高明阳,他便忙自己的事事,吩咐秋分注意她。
周分秋很尽责,昨天一直跟踪心桐,看到她在湖堤上磨蹭,准备上前帮助。两个中年妇女出现,便闪人。回来把情况一一告诉骋伟。
闻言,原准备回市区的骋伟在牛山岭镇又逗留一日,今天大清早地开车堵人。
她回头,斜睨他,揣测他有几分诚意,待他停车,开门,毫不迟疑地上了车。
路过车站,她看到候车广场上三三两两地站着几个裹成大棕子的人影,暗自得意。
一路上,两人均沉默不语。
回到医院,离上班时间还有二十分钟,她懒得回房间,背着大婶装得沉沉的大包,直接来到科室。
大年三十,能出院的病人都让他们出院。能容纳五十八张床位的病房只住着十三个病人,集中放在四个病房里,整个病区显得十分空荡。
心桐心情异常沉重,离开护士站,来到病房。
病人看到心桐,热情地招呼她,问她在哪儿过年。她一一回答,心情稍稍缓解。
后来创伤外科病房里来了一群病人,高速公路附近一辆中巴车不慎翻车,致二十几个乘客受伤,其中四五个重伤。
心桐路过电梯门口时,看见一帮人,匆匆忙忙地拥过来一辆推车,冲出电梯。她赶忙连退几步让路,护送同事歉意地望着她,她摇头示意没有关系。
推床上病人已经昏迷,全身血染,脸上道道血痕流成了红色雨帘,头顶缠绕着白色敷料,严严实实,藏不住凹陷的轮廓,殷殷鲜血染透一大块。
周围是病人闻声赶来的亲人,一个个像霜击的苦瓜,眉头紧皱,蔫头蔫尾。
同事告诉她,他刚从CT室出来,结果很差。
三个小时后,这个病人抢救无效,离开了。他的亲人哭得死去活来,拼命地呼喊死者名字,声声凄婉,让她故意模糊的水云记忆,再度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