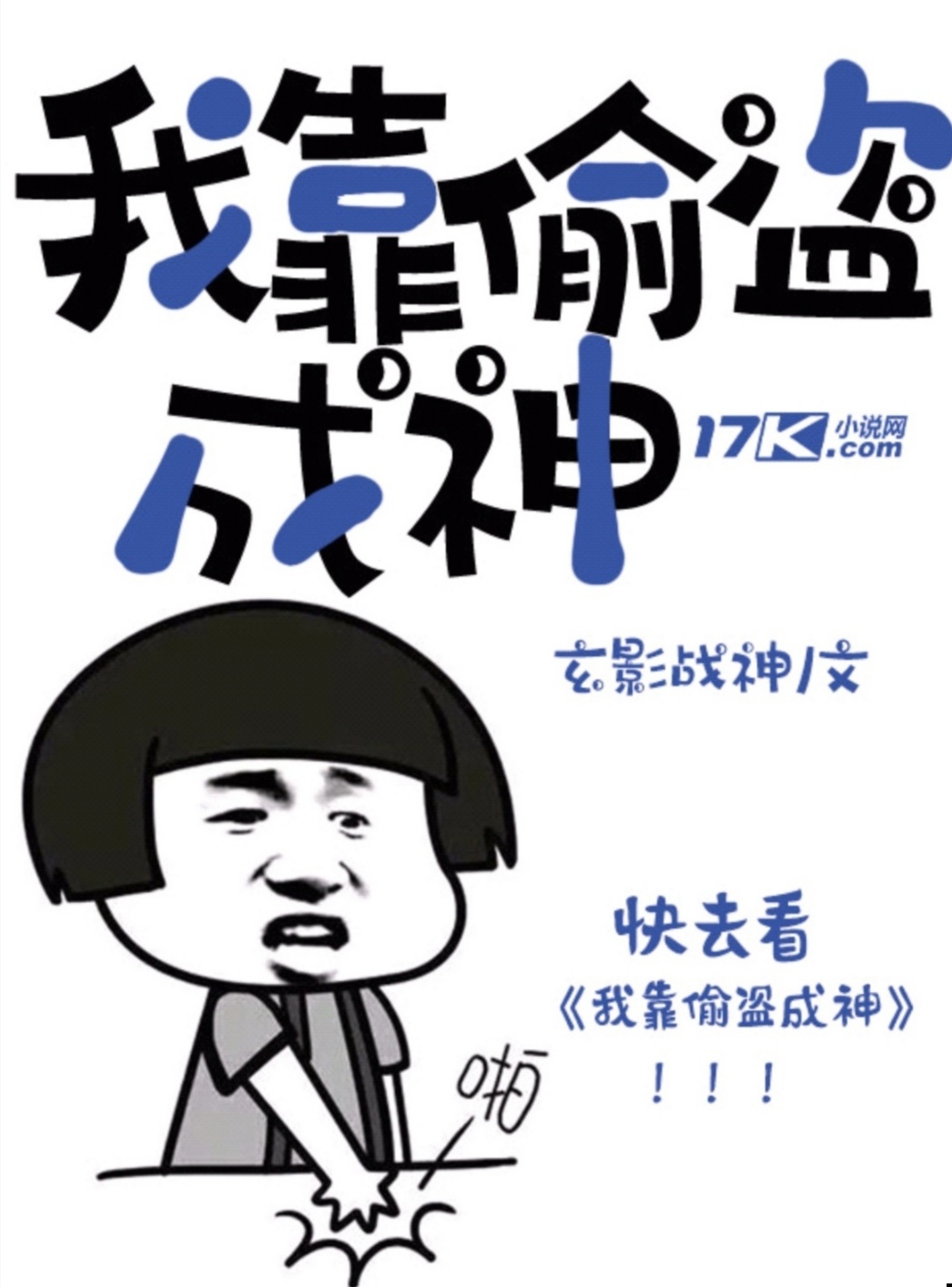大山的颜色,一天之中有很多次变化,黎明,中午,下午和傍晚,各有不同。
早晨空气很干净,大山很近,山上的沟壑也看得清清楚楚。
中午,太阳当顶,它们烟雾弥漫,模模糊糊。
傍晚,西边山坡的颜色美极了,像披着最最华丽的毯子——你从来没有真正看见过的,玫瑰红的大毯子!
那毯子将所有白天的光芒带走,又将黑夜的序幕轻轻打开。
我尝试过,在小镇东边山坡的大理石上,一直待到深夜,看天空、大地,和远山的变化,看得我饥肠辘辘,天旋地转。
我也曾经在深夜梦游,和摇动尾巴的狗儿一道,从家门一直走到街口,仿佛去到群山跟前,好像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魂灵,在半透明的夜里迷了路。那狗儿却什么都知道,所以它带我去我想去的地方,安安静静地陪伴我。
夜和白天的世界,从来都是两副面孔。
夜色中,大山波浪型的剪影,贴在瓷盆一般幽蓝的天边,那么远,遥不可及。
如果月亮很好,正如爷爷教的古诗词里,那种月白风清,或者是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或者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就是那样的时候,夜深人静,你想把《夏洛的网》一口气读完,或者是被尿憋醒……
总之,在万物睡着了的时候,你醒着,倾听夜的呼吸,倾听远方的林涛,在屋里走来走去,蹑手蹑脚.
结果,你看到了月光,从小小的窗户照进来的月光,那么熟悉,好像童年时候的一个梦。
你睡不着,宁愿在黑里,因为那月光,实在太美了,面包,糖果,糯米酒,轻柔的小提琴,没有一样能比得上它的美。
你轻轻开门,走出街口,走到月光里去。
为什么呢?
如果有一个亲人在身边,他就会告诉你,在你还是幼儿的时候,多病的你总在夜里啼哭。
是的,我小时候身体多病,总在夜里啼哭。
奶奶说:“作孽啊,作孽啊,狠心啊!没奶吃的孩子,怎么活啊?”
她不断地诅咒一个人,一个和我生命息息相关的人。
爷爷说:“别唠叨那些没用的。”
于是,她把她平时念的那些佛经,又念了一遍。
奶奶不停地说:“天灵灵,地灵灵……”
爷爷把我抱出去了,走到月光里去。我感觉到丝丝的凉风,从我的小脑门上拂过,很轻,大概它也知道,我只是一个离开母亲怀抱不久的小小的婴儿。
爷爷在月光地里轻轻踱步,给我哼各种各样的音乐。
除了音乐,我还听见一些远远的风声、林涛声,远远地,从山坡上滚过去了。
我不哭了,睁着黑溜溜的眼睛,东张西望,看月亮,看远方的山,那么安静,倾听……
每次都这样。所以,不管你长多大,月明的夜晚,你都会起来,去到月光里,看月亮,到大山跟前。
那样的夜晚,什么都睡了,远处一两只狗儿醒着。它们叫上一两声,好像说:喂,小孩,你看得见我吗?
人们说,夜里,狗儿可以看见鬼魂。
有一本书上说,如果你思念早逝的亲人,想和他们的灵魂相遇,就要在这种夜深人静的时候,踏着月光,去找他们。
我想找爷爷。
我从小砖房的门口,一直走到街口。那是一个无限敞开的地方,连绵群山就在眼前。
我在石头上坐下来,看山。
爷爷,爷爷,你知道我在这里吗?
空气那么干净,人们都睡着了,永远不会醒来。
没有谁能够打扰您,爷爷,您出来吧,从地底,从河湾里,从大山的皱褶中,从乌云一般的树林那边,爷爷,我等你……
大山像影子,好像动起来、飘起来了。
我一动不动,看见它们手拉手,跳起锅庄,旋转起来了……
周末的白天,如果天气不错,我就会到我的瞭望台,看天。
县城那边,那些房子,脏,灰,像乱扔一地的积木。
县城里的人们在做什么,我当然清楚,那都是他们昨天、前天,去年、前年,从他们爷爷的爷爷、奶奶的奶奶就开始做的事情。
他们这些没有土地的人,和附近的农民攀着亲戚,忙忙碌碌,做点小生意,串门聊天,或者打骂小孩。
有些时候,大人比小孩愚蠢多了,他们总做小孩不喜欢的事情。
天空里积了太多灰云,大山灰黄。山上有沟壑,那是夏天的洪水冲刷出来的。
我脚下的小河流,水是灰绿色的,它一直往南,汇入珠江的支流南盘江。
夏天,水边的芦苇越来越茂盛,是捉迷藏的好地方,是我们的乐园,只要不上课,我都会泡在水里,直到我的手掌和脚掌的皮肤,像青蛙的一样,皱巴巴地发白。
直到饿得发晕,我才会上岸。
太阳一整天没有出现,也是我瞌睡的一个原因。
杨老师说,金融风暴,沿海很多人失业了。爸爸为什么不回来呢?
东山口是进出县城的唯一通道,我想,终有一天,爸爸会拄着拐杖,背着包袱,满脸疲惫,在那出现的。
每个周末,我都到瞭望台上,等爸爸。
我想像,他终于看见县城了,却忽然没了力气,膝盖发软,呼吸缓慢。他的脑袋垂下来,就要往厚厚的尘土里扑下去的时候^
我刚好一个跳跃,落在他面前,把他搀住……
我反反复复在脑子里预演这一幕,喉咙一次次打起结来,泪水一阵一阵地涌出眼眶。
3
一个老大爷端着漱口缸子过来,叫我:“小朋友?”我抬起头来,他问:“你没有不舒服吧?”
他的眼睛笑盈盈的,有一点点像我的爷爷,但比我爷爷狡猾多了。他是从卧铺车厢来的,虽然在笑,却有对硬座车厢人的提防。
看我不说话,只盯着人看,就不再理,顾自刷牙去了。那么小心,大概他的牙也日渐腐朽了。
我站起来,走到车厢连接处的窗口,想好好看看风景。那儿的拉手上,有一条黄丝带,是刚过去不久的四川汶川地震周年祭奠留下来的。
我将黄丝带小心地解下,又重新系上。
我再次把它解下来,系到我的书包上,为我的爷爷,为遥远的汶川大地,为爷爷的乡亲们,无数我不熟悉的灵魂。
“打屁股!”爷爷笑呵呵地把我放在他的腿上,在我后面轻拍了两下,说:“记住没有,爷爷的书、报纸,都不能撕的,记住了没有啊?”之后,又把我举起来,转圈。
我们乐得笑个不停。
那时我应该是三岁。
有次在同学家看电视,台湾那个丑丑怪怪的蔡姓画家,说他两岁就觉悟,三岁就立志要做画家。
这事情让我想了很久。
为什么我三岁的时候,没有立下个什么志向?这一定是我到现在——快要当初中生了,还一事无成的原因。
可那时,爷爷也没有叫我立志向啊!他是风谷中学的校长哩,很有名的学校,没谁不知道。
学校敲钟的,也是一个爷爷,很瘦,说我听不懂的北方话,嗓音脆,说得又快,一溜儿一溜儿的,听起来像唱歌。
他偶尔遇见爷爷时,却有些害羞,既热情,又尊敬。
他请爷爷教他说一两句俄语,当爷爷叽里咕噜说完之后,他怎么都学不上。他说他舌头转不了弯,也弹不起来,然后他们一齐哈哈大笑。
我喜欢钟声。
钟声想起来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天地间的一切,原来都不止是那么地沉默、对望着,天空和大地,树木和石头,小草和虫子,溪水和流云,它们其实一直在互相关心,甚至悄悄说一些话,轻轻唱唱歌。它们所说的一切,只是我们人类听不懂罢了。
当钟声响起来的时候,每一棵草木,每一缕空气,都在颤抖,溪水和松涛一样发出各自的欢呼。天空中、山坡和道路上的光芒也发生了变化,一切都那么愉快、和谐,那么激动,就像一个合唱队里的每一张面孔,都在即将开始的歌唱前变得绯红……
每一声钟声都会传得很远很远,送出去,在路上、屋顶上、树林上回荡,前面的还没来得及消失,更响的钟声又推过来了,像波浪。
晨钟几乎和日出同时出现。
那时候,爷爷正在从家里去办公室的路上。他的面孔略有笑意,又将陷入沉思,目光望远处的教室,或者是教室背后,更远更高处山坡上的松树林。
他永远保持着那种笔挺的姿势,和从容不迫的精神。
黄昏的钟声,我到老都不会忘记。
当我在钟声里、小路上蹒跚着往回走时,远远就看见我们住的木房子,各个窗户溢出黄黄的温暖的灯光,爷爷影子浮现在薄薄的窗纸上。
他在备课,或者看书,看报,看杂志。
屋子中间,一盏戴有搪瓷圆盘灯罩的电灯,从屋顶的横梁上垂下来,爷爷,桌椅,都在地上留下影子,就像那些素描画,接上阴影就产生了立体感觉一样。
爷爷头顶的头发掉光了,耳朵上却有,人们说,他太像列宁了。
爸爸在厨房里准备晚饭。
厨房用的是一盏马灯,结了灯花,散出很臭的煤油烟味。锅里的油焌豆腐噗噗响,爸爸添上半瓢水。
那水瓢,是王家寨的一个老木匠,用最好的青冈木刨成,送给爷爷的。我知道,这个老木匠可不是一般的匠人,他的东西也不轻易送人的。
(西篱其他作品:《废墟之痛》http://520yd.com/book/520yd.com;
《十二重天》http://520yd.com/book/520yd.com;
《猫》http://520yd.com/book/520y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