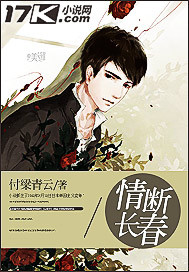我没有忘记我的话题。
我在等待着那个特殊的时刻。我隐隐约约感到,关于妈妈,对爸爸来说是个艰难的话题,对我又何尝不是!
一个人要面对自己生命中的秘密,不能没有勇气。我铁心了,一定要在今夜,知道我想知道的一切。
我把水杯递过去:“爸,喝水。”
爸爸接过水杯的时候,手有些发抖。但是,我已经拽不回自己。等他喝了水,我再次恳求:“告诉我,我妈妈是谁,是什么样的人,她为什么一直没有和我们在一起。”
他又咳了一声。他并不是想拖延。
“关于她,我一点也不了解。”他说。
“为什么?”
“我并没有和她结婚,也不知道她是谁。”
“爸,你没糊涂吧?我太吃惊了。”
“没有。”爸爸说。
我安静下来,耐心等爸爸把他的历史打开。
“十三年前的那个暑假,学校里没有放假,大家都去帮村寨里的农民干活。晚上,就在大操场上放电影,是一部很新的外国片,《人鬼情未了》。我们预先就到几个村寨里去通知了,请乡里乡亲们都来看,结果,来了很多人,大操场都站不下了。电影散场的时候,人都走尽了,就剩放映员在收机器,爷爷陪着他。这时,爷爷听见了婴儿的声音。他在自己的凳子下面发现一个篮子,里面有个小小的婴儿……”
我的声音完全变了:“难道,就是我?”
“包裹里有张小纸条,写着你的出生日期。爷爷用手指拨开包布,你不哭了,含住他的手指不放。爷爷把你抱回家。以后,我天天熬米汤喂你。”
“她什么都没有留下吗?像那些电视剧里一样,玉佩啊,银锁啊什么的,可以证明我的身份的。难道她不想以后找到我吗?”
“有一条围巾,是城里人用的那种,棒针织的海马线围巾,上面绣了一个名字:王小丫。”
我沉默许久,终于,不出声地哭了。
“她扔下你,不等于不爱你。她一定遇到了难处。”
爸爸把我抱住。
“你瞧,她多聪明,把你送给爷爷,爷爷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我依然哭,哭了很久。
我再次变回了那个婴儿,就由爸爸抱住,在炉火边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黑色爱丁堡的那只白鸽子,飞来。我吹着口哨,向它打招呼,同时责备地问:“怎么才到啊?”
它说:“咕咕。”同时把红色的小脚伸给爸爸。
爸爸捏住那张纸条,问:“它带什么给我们呀?”
我不好意思地说:“一首小诗,我写的。”
“你写诗?哦哦,写了什么呀?”
“雪袍子。”
“哦,哦。“
爸爸展开来看,我赶快跑了。
97
第二天早上,我一直睡到十点过才醒来,肚子饿得咕咕叫。
爸爸还在睡。被子里很暖,整夜,爸爸一直把我的双脚抱在怀里。
我轻手轻脚从被子里抽身,起来,穿戴好,去店主的小商店买两碗方便面和几个卤鸡蛋,泡好面,再叫爸爸起床。
吃过早饭,我们把裤脚扎紧,向王家寨奔去。
一路上看不到人影。
冬天的乡下,真的十分荒凉,如果你一个人在这样的季节里走,一定会迷路的。那些光秃秃的梧桐树和槐树的枝桠,伸在灰蒙蒙的天空里,几只乌鸦盲目地飞过,发出饥饿的叫声。天空,大地,找不到一片绿色的树叶。
走了一个多小时,到王家寨了。寨门口的古树上,挂着很多红布条,那是年年岁岁人们的祝福和祈愿。
寨子里,家家关门闭户,连牲畜也躲在它们的圈里,不做声。
整个世界都因为冷而寂静无声,紧缩了。寂寞在寂静中,被成亿倍地放大,大到整个地球都轻起来,在虚无的空气中茫然转动。
多么荒凉!
我庆幸,我是和爸爸在一起的。我们就像是人类最后剩下的两个,已经走到地球的边缘,一个身体虚弱的中年男人,和他收养的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要说,男人和男孩心里有同样的温情,并且,这温情保持着恒定的热度,不会因为他们没有血缘联系而冷却,是什么在给他们的心、给这温情加热?是爱,他们彼此深深地爱着对方。
就在那片刻,我突然理解了爱和生命,和这整个世界的关系。如果没有爱,世界一片荒凉,地球就是一个坚硬然而虚无的存在。
我的妈妈,如果有爱,她一定很美丽。如果她没有,我们要把自己的,给她留着。
我转脸向爸爸,爸爸不看我。但,我知道,他和我心心相印。
他艰难地拖动自己僵硬的腿,他的腿一定又犯风湿痛了。他小心地隐瞒着腿痛,对我微微一笑,说:“找找吧,说不定……”
我们在寨子里转了一圈,那么漫长,好像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没有人影,连牲口和家禽也看不到。这和我童年记忆里的乡村,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很久,终于,我们看见一个戴绒线帽的老人,在茅草房子后面的地里干活。他的手脚因为冷而捏不住锄头,笨拙地,慢慢地把那些土疙瘩一块块敲碎。
我们走上前。我说:“大爷——”
老人直起腰,扭过头来。
“大爷,我是周忻,他是我爸爸。我们来找一个人,女的。”
“女的?叫什么名字?”
“王小丫。”
“小丫?我们这里的女子都叫这个名啊。她长什么样?多大?”
我想了想,说:“她长得像我,年纪嘛,也许和我爸爸差不多大吧。”
“我们寨子里的小丫,没有戴眼镜的。”
“我不是戴着眼镜来到世间的。”
我取了眼镜,请他看我的脸。
他摇摇头,表情疑惑,又陌生。
“大爷——”
他拄着锄头,决然地说:“你们肯定找不着。寨子里的年青人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小孩都比你小,大人都比他老。”他指我爸爸。
“那么,”爸爸说,“快过年了,出去打工的,就要回来了吧?”
“这个,难说。回家可不容易,太远了。要是没挣到钱,更没法回了。”
他说着,呼出一口浓浓的白气。
“你们看天,”老人指指天空,“要下雪了。今年这场雪一定很厉害,打工的都回不来了啊!”
98
下午,我们回到小旅店。天空黑乎乎的,像给棉被捂住了。
吃过晚饭,爸爸就一直站在窗前。
店主过来说:“天气预报,有大降雪。班车已经停开,你们恐怕得多住些天了。”
“哦?”爸爸有些不安。
我从他身后把他抱住:“爸,不怕,我和你在一起的。”
“儿子……”
“爸,我永远都是你的儿子,是你养了我!”
爸爸转身用手臂勾住我的头,他的眼里噙着泪。
他说:“忻,你真的长大了,我很高兴,很放心,真的。”
我想,父亲对每个人来说,意义都是一样的。但是对我,格外不同。
第一朵雪花飘下来了,我伸手去接,没接住。
“爸爸,这么说,我和你都是出生在这里的了。”
“嗯。”
“爷爷出生在风镇?”
“爷爷出生在重庆,在风镇长大。”
“爷爷的爸爸出生在哪里?”
“苏州。”
“再往上,爷爷的爷爷,出生在哪里,你知道吗?”
“再往上,我就不知道了。”
“这么说,我们都不知道,哪里才是真正的故乡。”
“说不清。你想想,以后你的孩子,你的孩子的孩子,也不知道会出生在什么地方呢。”
雪越下越大。它们好像憋得太久,终于可以飞翔了,所以,那么急迫地,挣脱天空的抑制,飘向大地。
我的眼镜蒙上一层湿雾,擦干净后,我发现,远方的景物已经模糊了。世界开始在白色中膨胀和蔓延,雪,将那无边无际的寂寞和荒凉改变。曾经那么低沉、陷落的大地,开始丰满和上升。在雪花的聚会里,在它们花瓣的缝隙里,一定藏有很多很多声音,这些声音会汇集起来,包裹大地,响彻天宇。
“爸爸,我想听你拉小提琴。”
“它早坏了。我吹口琴给你听吧。”
我们的口琴随身带着。
爸爸开始吹出一支曲子,正是我最最喜欢的《银匕首》。
雪下得更快、更密了,它们多么喜欢音乐啊!它们纷纷旋转起来了啊!
爸爸一直给它们伴奏……
“我叫——我不告诉你。”
“嗯,我猜,这是很容易猜到的,”那人得意又狡猾地,斜看着我,说:“嗯,我明白了,你就是那个,周校长家的那个……”
我突然觉得,他有点嘲笑的样子。
我生气了:“我是哪个?你说!”
“斜眼!”他大叫一声,跑了。
我哭了,沿着小路回家去。奶奶看见我,厌恶地喊:“看你一身泥,你又作什么孽啦?”
爷爷把我拉过去,给我擦掉鼻涕:“嗯,乖,忻儿没错,没错,啊?你是好孩子,是世界上最最幸运的孩子,现在是,以后也是,对不对?”
我没错。谁错了,我不知道,也不追究。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们都是一样的,是精子和卵子结合成的生命——我上中学就知道这个了。爷爷先是叫我“幸运”,后来才改叫“小忻”。
“可是,爷爷,他叫我斜眼。”
“没关系,”爷爷说,“斜眼可以看见更多的东西。我们来玩大眼、斜眼的游戏,好不好?”
“好的,爷爷。”
“准备好了啊,大眼,斜眼——该你了!哟,没睁开,哈哈,没睁开!”
“忻,你笑什么?”
爸爸用一块绒布仔细地抹拭着口琴。
“我想起小时候的事情。就是你昨晚玩的那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爸爸,你看,雪好大,那些连起来的山都白了,房子也白了。”
“这雪会一直下下去的。”爸爸有些担忧。
两个小时以后,一尺厚的雪盖住了山头,盖住土地,盖住了整个乡村。鸟儿们不见了,西北风也早早停息,白雪的世界高高耸立,纯净、柔和,无边无际,就像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梦。
“爸爸,爱斯基摩人给雪取了三十多个不同的名字呢。”
“那,你喜欢叫它什么?”
“我想,世界上的雪只有两种。”
“哦?”
“一种是冰冷的,一种是温暖的。”
“嗯。”
“爸爸,你说我妈妈,她是在南方吗?”
“应该是的。”
我对这个回答很满意。
妈妈不会冷的。她喜欢雪吗?一定喜欢的。雪纯洁,温柔。如果没有雪的拥抱,土地怎么能够在春天醒来呢?
如果妈妈正在回家的路上,她一定累了。
如果她是一棵麦苗,就让雪袍子把她盖上。
(全书完。尊敬的读者,请移步“作品相关”,欣赏评说《雪袍子》的各种文章)
作者简介:
西篱,本名周西篱。祖籍重庆,生于贵州。大学中文系学习期间开始文学创作,并以“西篱” 为笔名发表作品。曾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上海文学》、《诗歌报月刊》、《花城》、《作品》、《钟山》、《世界论坛报》(台湾)、《当代诗坛》(香港)等文学报刊杂志发表诗歌、散文、小说作品。历任贵阳市文联《花溪》杂志编辑、广东省文联《广东文艺界》杂志执行副主编等。曾为台湾《育达周刊》撰写散文专栏“心灵的牧场”,为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青年报》及《珠江》杂志等撰写专栏文章。
曾获贵阳市文学艺术成果奖“金筑文艺奖”、伟南文学优秀作品奖、《散文诗》最佳创作奖、首届南方散文诗大赛二等奖、第二届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入围奖(全国唯一音乐剧入围)等各种奖项。
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已出版诗集《谁在窗外》、《西篱的梦歌》、《温柔的沉默》、《一朵玫瑰》、《西篱香》、《西篱短诗选》。
已出版短篇小说集《我一生中最美的回忆》,长篇小说《东方极限主义或皮鞋尖尖》、《夜郎情觞》、《造梦女人》、《雪袍子》(《雪袍子》是中国作家协会重点选题作品,广东文学向建国60年献礼重点出版物)。
已出版散文集《逃惘的女性》、随笔文集《与人同居的猫》。
曾发表电影剧本《苹果园》、《我不是坏小孩》,创作音乐剧《南天雷神》。
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
文学创作一级作家。
现供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
(西篱其他作品地址:《废墟之痛》http://520yd.com/book/520yd.com;
《十二重天》http://520yd.com/book/520yd.com;
《猫》http://520yd.com/book/520yd.com )